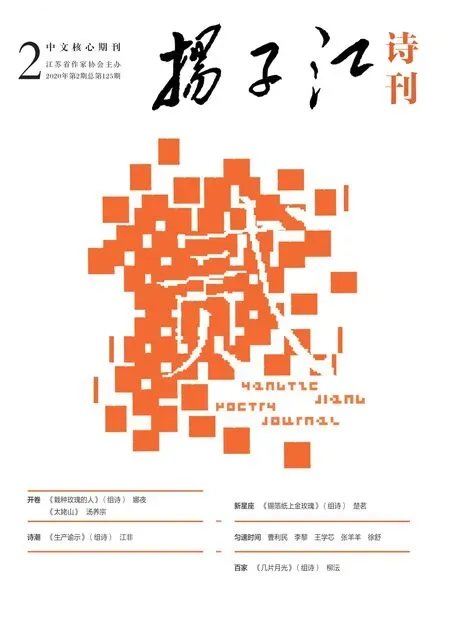[希腊]扬尼斯·里索斯诗选
谢炯 译
月光小夜曲
春夜。老屋中的大房间。女人,一定年纪,身着黑衣,正和一位年轻男子交谈。灯,没有拧开。两扇大玻璃窗,月光如注。我忘了告诉你,女人曾经出版过两三本带宗教色彩的诗集,身着黑衣的她在对年轻男子说: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今夜皓月当空!
仁慈的月啊——掩去了
我的白发。月色,将我的发丝
重新染成金黄。你
不会懂的,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
月亮升起,房屋的影子
更长了,
无形的手拉开了窗帘,
琴键的尘灰上,一根鬼魅的手指写下的
遗忘的字——我不想听见。请不要作声。
让我和你一起去,
走得更远一些,抵达那堵砖墙,
那个道路转弯,城市涌现的地方。
结实而空灵的城市,被月光洗白,
如此无动于衷又如此无足轻重,
如此积极乐观,仿佛形而上学的理论
最终让你相信你的存在和不存在
以及你的从未存在,以及那个极具破坏力的时间
的从未存在。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们将在矮墙上坐一会儿,在山坡上,
四周春风荡漾,
甚至,我们也许还能幻想自己在飞翔
因为我听见,经常听见,特别是现在,自己的衣服
如两张强有力的翅膀打开又合上。
你感到你的喉咙、你的肋骨、你的身体蜷缩;
当你将自己关闭在飞翔的声音中,
你能感到你的喉咙、你的肋骨、你的身体蜷缩在蔚蓝
空气的肌肉之中,
蜷缩在天空强大的神经之中,
你的离开或归来无足轻重,
你的离开,或归来无足轻重,
而我的头发渐渐变白也无足轻重。
(令我悲伤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我的心没能跟着变白)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孤独地走向爱,
走向信仰,走向死亡。
我知道的。我试过了。没有用。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这栋屋子闹鬼,冲着我闹——
我是说,这栋颓朽的老屋,钉子松动了,
墙上的肖像跌入虚无,
石膏无声剥落,
仿佛死人的帽子从黑暗走廊的挂钉上掉下来,
仿佛穿旧的羊毛护套从沉默的膝盖上滑下来,
仿佛月光披落在一张褶皱的旧扶手椅上
它曾经是新的——不是那张一开始就令你怀疑的照片——
我是说那把扶手椅,非常舒服,你可以坐上几小时,闭上眼,做任何梦
——沙滩,光滑,潮湿,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比我每个月送去街角擦鞋店的旧皮鞋更亮,
一条沉落海底的渔船,在自己的呼吸中摇晃,
三角帆对角折起,如手帕,仿佛没有什么需要它关闭或快速撑起的,
也没有理由扬帆告别。我总是对手帕
充满热情,
但不用它来绑任何东西,
也不用它在日落时收集花的种子或洋甘菊,
也不将四角扎起,做成街对面工地上建筑工人戴的帽子,
也不用来擦眼睛—— 我的视力很好,
从来没戴过眼镜。一种无害的怪癖,手帕。
现在我将手帕折成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手指忙碌不休。现在,我想起来
这就是计音的方式。
那时我去音乐学院学琴,蓝色裙子、白色衣领、两条金色辫子
——8、16、 32、64——
我和小朋友手牵手,桃红色,所有的光,采摘的鲜花,
(原谅我这样离题——真是不良习惯)—— 32、64——父母
对我的音乐才华寄予厚望。我却告诉你有关扶手椅——
阴沟里的——生锈的泉水浮现,满溢——
我想把扶手椅送去隔壁的家具店,
但是,时间、金钱和取向——什么先解决?
我想把一张纸盖在上面——倾注了
过多月光的白色布单令我恐惧。人们坐在扶手椅上做着伟大的梦,
就像你和我一样。
现在他们躺在地底下了,雨水或月亮不再困扰他们了。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们将在圣尼古拉斯教堂大理石台阶最上面停留半刻,
然后,你会走下去,我会走回去,
我的左侧,依然留有你的夹克衫传来的不经意的温馨;
还有一些方形的光,来自邻居的小窗户;
还有纯净的白雾,来自月亮,就像一群银色的天鹅——
我并不怕对你坦白,因为无数
其他的春夜,我和
披着朦胧和辉煌月色的神交谈——
很多年轻人,比你还要英俊,我都因为他而抛弃——
白色的火焰,白色的月光,我融化于白色,如此之白,如此难以亲近,
被男人多变的眼神和青春的盲从灼烧,
被精美的古铜色身体包围,
强壮的四肢在游泳池里,用桨;在赛道上,在足球场(我假装没看见),
额头,嘴唇和喉咙;膝盖,手指和眼睛;
胸部和手臂和器具(真的我没看见),
——你知道,有时候,当你沉湎其中,
你会忘记什么令你沉湎,沉湎本身便已足够——
天哪,多么明亮的星星般的眼睛,我被否决之星神化,
困扰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
没有其他路可走,只有向上或向下。 ——不,这些远远不够。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让我去吧,
因为许多年来——许多白昼,夜晚和深红的正午里——我孤独一人,
不屈不挠,孤独,完美无瑕,
甚至在婚床上,我都是孤独而完美无瑕的,
我写下辉煌的诗句,献在神的膝盖下,这些,如同刻进无瑕的大理石,
将在我和你的生命之后永恒。但这些都不够。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这栋屋子已经无法承载我了。
我也无法忍受它。
你必须一再小心谨慎地,
小心翼翼地,
用桌子撑住墙壁,
用椅子撑住桌子,
用双手撑住椅子,
用肩膀撑住房梁。
钢琴,如一具封闭的黑色棺材。你不敢打开。
你必须小心,非常小心,否则它们将倒塌,你将倒下。我无法忍受了。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这栋老屋,尽管里面一切都已死亡,却无意去死。
它坚持和死者一起活着,
靠死者活着,
靠死亡的确定性活着,
为死者保存它的存在,它的腐朽之床和书架。
那么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在这里,当我静静地走过傍晚的薄雾,
穿鞋,或赤脚,
总会听到一些声音:一块玻璃的断裂或一面镜子,
一些脚步声——不是我的。
外面的街上,也许还听不见这些脚步声——
他们说,忏悔者穿着木屐——
如果你看进这面或那面镜子,
在尘埃和裂缝背后,
将看到——变暗的,更加破碎的——你的脸,
而你一生追求的不过是保持这张脸的完美无瑕。
玻璃之唇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仿佛一把圆形剃须刀——我如何将它按上嘴唇?
无论我多么饥渴——我如何又将它举起——你看到了吗?
我已经有了这份愿望——但还是放弃了,
还是告诉自己理智并没有丧失。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夜幕降临,有时我感到,
养熊人正带着他臃肿的老熊在窗外行走,
她的皮毛上满是灼伤和棘痕,
灰尘轻扬,
凄凉的乌云笼罩着黄昏,
孩子们回家吃晚饭去了,不允许他们在户外玩,
即使在墙壁后面,他们神化老熊的路过——
疲惫的老熊在她孤独的智慧中路过,却不知道去哪里,或为什么去——
她变得越来越臃肿了,再也不能用后腿跳舞,
也不再戴蕾丝帽来娱乐孩子、闲人和不肯散去的观众。
她只想躺在地上,任凭
他们踩她的肚子,玩这最后的游戏,显示她消极抵抗的威力。
她不再关心他人的兴趣,唇上的戒环,齿间的禁锢,痛苦,和生活,
死亡的复杂性——哪怕是缓慢的死亡——
对死的漠不关心和对生的连续性的认知,
终于使她超越了一切奴役。
但是,谁又能将这场游戏玩到底呢?
老熊站起来继续前行,
顺从她的绑带、戒环。她露齿
微笑,嘴唇在可爱的毫无戒心的孩子扔给她的硬币上开裂,
(可爱正是因为毫无戒心)
并说谢谢。因为熊已经很老了,
只会说一句:谢谢,谢谢,
让我和你一起去。
这栋屋子令我窒息。特别是厨房,
就像深海。高挂的咖啡壶熠熠闪光,
像不可思议的鱼的滚圆的巨大的眼睛,
盘子如蒙杜莎一样缓慢起伏,
海藻和贝壳抓住我的发丝——我无法将它们拉下——
我无法回到水面——
托盘从我的手中静静地滑落——我沉下去了,
看到我呼出的气泡在上升,上升。
我试图转移目光,
不知道那些在水面看见气泡的人会说什么,
也许会说有人溺水或潜水员正在探险?
事实上,溺水到深处时,我不止一次找到
珊瑚,和珍珠,和沉船中的珍宝,
以及奇迹,过去、现在,还有未来,
一切几乎都是永恒的,
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有一种喘息的机会,一种不朽的微笑,
一种幸福,酣醉,甚至灵感,
珊瑚、珍珠和蓝宝石。
只是我不知道如何给他们——不,我能给他们;
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将如何接受——但我仍然会给他们。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那一刻,我拿着夹克衫。
天气变化无常,我必须小心。
夜晚潮湿,说实话,是不是月亮
加剧了寒冷?
让我扣上你的衬衫——你的前胸多么强壮
——月亮多么强大——扶手椅,我是说——每当我从桌上拿起杯子时,
便留下一圈沉默。我将手掌盖在圈上,
为了不看穿它——我把杯子放回原处。
月亮是世界天灵盖上的一个洞——不要看穿它,
那是吸引你的魔场——不要看,任何人都不要去看,
听我说——你会陷进去。这种眩晕,
美丽,空灵——你会跌进——
月亮的大理石井,
阴影移动,翅膀寂静,神秘的窸窣——你不已听见?
深,陷得越深,
深,升得越高。
空灵的雕像埋在敞开的翅膀中,
深沉,深沉的无情的仁慈的寂静——
对岸颤抖的光,让你在自己的波浪中摇晃,
大海的呼吸。美丽,空灵,
眩晕——小心吧,你会跌倒。别看我,
我就是这摇晃的波浪——这眩晕的眩晕。因此,每晚,
我都有点小头痛,眩晕的咒语。
我经常溜到街对面的药店买几片阿司匹林,
有时候我太累了,只好随它去,
听听水管在墙壁上弄出的空洞声,
或者喝杯咖啡,并像往常一样心不在焉,
我忘记了,做了两杯咖啡——谁会喝那杯?
真好玩,我把那杯放在窗台上冷却,
或者有时喝掉两杯,同时从窗口望着药房明亮的绿色地球,
就像一辆闪着绿灯的寂静的火车,开来将我带走,
带走我的手帕、破旧的鞋子、黑色的钱包,以及诗集。
但是没有行李箱——要那有什么用呢?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哦,你去吗?晚安。不,我不会去。晚安。
晚些,我自己会去。谢谢。因为,最后,我必须
离开这栋破屋。
我必须看到一点城市——不,不是月亮——
是有着老茧之手,日常生活气息的城市,
是用面包和拳头发誓的城市,
是承载着我们所有人的城市,
以及我们的渺小、罪恶和仇恨;
我们的野心、无知和老朽。
我需要听到城市伟大的脚步声,
不是你的脚步声,
或者上帝的脚步声,或者我自己的。晚安。
房间变暗了。云覆盖了月亮。突然,有人在附近的酒吧打开收音机,熟悉的旋律:《月光奏鸣曲》,只是第一乐章,轻柔地演奏着。年轻男人现在将带着讽刺的,也许是同情的微笑走下山坡,他的精致的嘴唇轮廓分明,他感到轻松。在他到达圣尼古拉斯教堂走下大理石台阶之前,他将笑起来——洪亮、无法抑制的笑。月光下,他的笑声将不显得突兀。也许唯一突兀的就是没有任何突兀感。但是不久,他将开始沉默,开始严肃起来,并且说:“一个时代已衰落。” 宁静再度到来,他将再次解开他的衬衫,继续前行。而穿黑衣的女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最终离开了那间老屋。月亮再度照耀。房间的角落里,阴影加深了令人难以忍受的遗憾,几乎可以说是愤怒,而愤怒不是源于生活,而是源于无用的忏悔。你能听见吗?电台正在播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