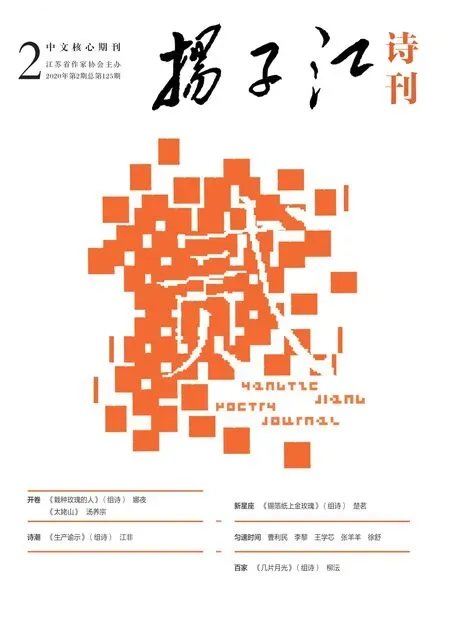[俄]库什涅尔诗选
谷羽 译
人的生命——说是“只有一次!”
“人的生命——说是‘只有一次!’”
这是谁说的?莎士比亚的词句。
洛津斯基为我们翻译了这句话,
翻译家却没有空闲去参加宴席。
宴席短暂。劝你再一次抬起头来
看云彩,看树丛,看那些星座。
或许想说:“一次、两次、三次”——
但愿人生在世能过得更加快乐。
我喜欢的诗人一年到头不写诗
我喜欢的诗人一年到头不写诗。
整整一年——他只写了一首。
那么他在做什么?忙碌什么事?
如何自我安慰寻求生活的意义?
何处掩藏其才华,藏进抽屉?
到年底才想起诗,伸手去抓笔,
拿起草稿本说:“哦,你来啦?”
神秘的缪斯走进门却默默无语。
维苏威火山
哦,我渴望目睹维苏威火山!
见到了,怎么样?山就是山。
用不着激情似火为之癫狂,
它可意识到自己像帐篷一般?
跟它相比卡兹别克的雪峰,
银光闪闪,犹如晶莹的钻石!
有罪的维苏威火山愁眉苦脸,
罗马的历史劫难令人恐惧。
这就是维苏威?无峰无雪,
难道就是它使庞贝城毁灭?
就像我有缘见识一位大人物——
内心的失望之情,难以诉说。
身材没长高,相貌仍怪诞,
早晨冷,多穿衣服注意保暖。
无意间还想要说一说天气:
“今日阴有小雨,不像昨天。”
每棵青草都有几滴露珠儿
每棵青草都有几滴露珠儿,
有的像项链,有的像手镯。
看不见的人守护着它们,
免得这店铺被歹徒抢劫。
露珠儿蒸发,亮光逐渐减弱,
清洗这世界还有细雨迷蒙。
雨是智慧、良心,还是醒悟,
雨是珠宝商,雨又是医生。
艺术可谓是生活的继续
艺术可谓是生活的继续,
但大概是一种美好的状态,
我们不受来客或亲人打扰,
此事无关穿戴只涉及天才。
你能摆脱命运变幻的左右,
不怕死,克制恐惧与烦恼,
只盼望爱神,盼缪斯姊妹,
盼梵·高带来午夜的风暴。
艺术要让森林延续生命,
艺术要让海洋连续翻腾,
艺术中无关乎什么进步,
而是我们心中保存灵性。
音乐教会我们敞开大门,
俯身亲近迎春花与紫罗兰,
这就是热爱生活的理由,
激励我们创作生命的诗篇。
成名时节偏碰上艺术衰落
成名时节偏碰上艺术衰落,
弄不好也许是艺术的毁灭,
因此烦躁忧愁难以排遣,
意大利无聊,法兰西茫然,
屈辱,告别,收场,终结。
哦,博大的散文何等可爱,
诗歌拯救我们脱离苦海,
正面观赏绘画,不必斜视,
音乐中没有威胁与迫害
不让你徒劳无功从头再来。
当忧愁和疲惫相继来袭,
你知道那该有多么悲哀,
那时候你觉得无比可怕,
既没有美,也没有诱惑,
彼此相爱的人已经分开。
公园里站着石刻的雕像,
仿佛来自远古的石器时代,
剧场幽暗像修道的洞穴,
没有情感没有思想和信念,
音韵消失,忘却了欢乐。
不过,可以深深叹口气,
甚至感到惊奇,欣然自得,
我们被选中撰写结束语,
我们受命运与天时捉弄,
变成了悲剧时代的见证者。
未来——就是……——给德·康托夫
未来——就是我们
晚年所要面对的情景,
年轻时它的闪光诱人,
然而注定了十分惊恐。
若能活到那个时候,
疲惫不堪,损失惨重,
你不想再从头开始,
不愿再走进那个门口。
活到未来,我才明白,
才意识到收获了什么,
平静地站立在凉台上,
仿佛刚刚走出电影院:
电影好看,十分惊险,
结局乏味,千篇一律,
像往常一样没有意思,
哪怕影片作者是上帝。
四十岁的时候
四十岁的时候还渴望长生不老,
五十岁的时候还向往永垂不朽。
有何缘由?为的是展现追求——
跟勃洛克会面,跟普鲁斯特握手。
愿你认同:这颇有尊严的借口。
然而活到八十岁,破解自我荒谬,
不朽别有深意:勃洛克仍然年轻,
普鲁斯特掩饰冷笑忽然扭转了头。
他们厌烦不朽这个词:索然寡味,
他们不再写作已经很久很久。
仍然不用敲门走进读者的房间,
或冲着狭小壁龛里的雕像呐喊。
我见过诗歌的荣耀
的确,我见过诗歌的荣耀,
而现在却目睹它的衰落。
似乎神灵都已躺倒睡眠,
我希望他们的梦境短暂。
从另一面来说,没有诗歌,
祖祖辈辈也在大地上生活:
缝衣、织布、塑造神像,
用珍珠玛瑙装饰小木箱。
乌鲁克的陶器令人赞叹,
迈科普的牛犊格外强健。
而诗歌……诗歌正等待,
这是晕厥,短暂的休眠。
小孩子喜欢大地上不仅有人
小孩子喜欢大地上不仅有人,
还有动物——有小猫,有狗,
有鸽子,有乌鸦,随意飞翔。
有一天爸妈带他去逛动物园——
嗬,斑马,跟他想象的一样!
孩子觉得,他是动物的一员,
长尾猴、斑豹、袋鼠、孔雀
大老虎、骆驼、河马、犀牛
孩子把他们当成朋友、亲戚,
不愿它们在笼子里失去自由。
他相信,他和动物天生平等,
所有动物都值得爱,值得尊重,
别欺负它们。看,大象多威武!
狼守在狐狸窝旁边满脸沮丧,
大家都参与奇妙童话剧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