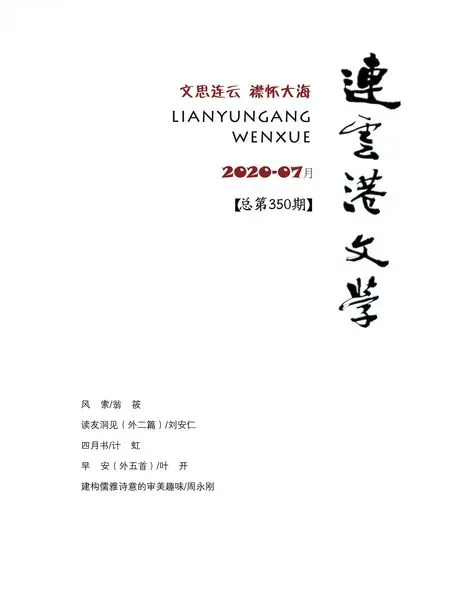早安(外五首)
2020-11-12 04:05:29叶开
连云港文学 2020年4期
叶开
推开窗,就看见了山
一个温顺的故人。他说
早。
风铃就动了一下。
他又说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他的声音安详
我通过鼻息间,嗅到的一缕清香
接受了
他的祝福。
我们所有人
我找不到卡佛了。
卡佛的,
我们所有人。
那本黑色封面的诗集。
他的脸,
像长在石头里。
他可怜的前妻,
从烤箱里
端出
比石头还硬的黑面包。
她一直在生活中
苦苦挣扎。
还有,他总是搬家的母亲。
他惧怕拿起电话。
那些抱怨
会铺天盖地
扑过来。
那个处境不佳,
急需用钱的儿子。
和每日,
靠燕麦粥
糊口的女儿。
他们,
又都来信了。
信并未打开,
挤在一堆乱糟糟的手稿里。
觉 醒
我偶然出现
在这一秒。
这一秒,
来自觉醒。
之前漫长地活着,
那并不是我。
我写的长信
寄往远方。
那个拆开信封的人,
手指上
沾满了暖和诧异。
时间是
火车一定会在这里
停下来。
这是必然的。
火车一定会在这里
为我们
停下来。
你不信不行。
辽阔的华北平原上
你眼睛的深处
溢出一种无法
说清的东西。
古老。
又弥新。
像雨。
又不是。
变形记
我把玻璃杯贴在脸上,透过它看
这世界。
模糊。像变形记还是
它本来面目,
不重要而获得短暂欢愉。
夜空深邃,
而使
我们屏息谁人在凝视:
我体会过那种漫长冬日的和解。
其实这一刻,
我就是
时间。
我就是雨中的那只,黑鸟。
我就是我认为什么
就不是什么的喻体。
玻璃杯沁凉。
这真是一个使人
大笑又停不下来的夜晚,笑是个秘密。
忧 郁
每天我都在天气预报中
找雨。
而我的忧郁,
堪比冰箱里
的一颗冰凉草莓。
白色教堂偏于小城
以北。
通常我会
不发一言
如一尊沉默雕像。
只是安静等待,湖水缓慢地
上涨。
直至它离我的鼻息仅仅
相差一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