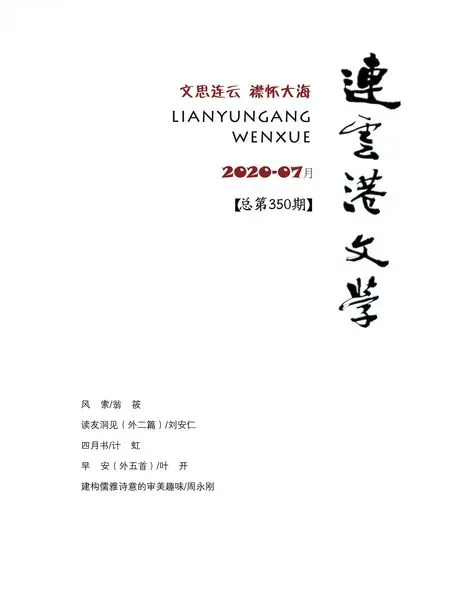建构儒雅诗意的审美趣味
——评马永娟的散文
周永刚
马永娟的散文创作无疑是连云港市近年散文创作的一大亮点。
有目共睹,她的散文越写越好,给我们带来诸多惊喜。她的散文从中国传统散文一路走来,在继承“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乡土叙事优秀传统中,融情入景,以景抒情,情景交融,又融入了现代语境下的思考与创新,使它的这些小情怀的散文反映了人性的温度,社会变迁的速度。
认识马永娟很久了,她的散文写得好,写得真实,写得反映社会人生。她的文笔清新,有诗意,她的散文有意境,她的童话般的笔触,让你感受人间的暖意,那种诗意栖居的求索,使她的散文带给你美的享受,带给你人生与社会诸般考量与回味,她的语言准确的像教科书般,文字功底不俗,经得起推敲,她的行文行云流水,文风纯正,大有可观。本文着重以她出版的三本散文集为例,(《为自己点支烟》《藤花落》《林间物语》)谈一下她的散文艺术风格
一、诗情守望
在心为形役、身为物役的浮躁社会生活中,面对物质的欢悦和精神的流离,她诗情守望,建构现代优雅高贵和诗意的审美趣味。
文学创作就是她的信仰,如同宗教家的殉道,诗人终生殉美。作者对于文学创作一往情深。她的散文创作是她人格和精神的表达,人的高度就是散文的高度。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她是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在散文创作领域笔耕不辍,创作的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成为我市散文创作的领军人物。她的小情怀,恰如我市一位大诗人孔灏所说,纯真的小情怀,恰是比欲望更清晰的大自在。
知人论世。马永娟的文学创作一路走来,并不容易,苦甘自知,用句唱词说就是“集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
她的散文有着极大的张力,在突破自我的精神困顿中昂扬向上的力量,有着强大的正能量,洋溢着世间美的情愫。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都值得她讴歌,她的笔下常常像童话世界,是那么的纯净和美丽。不管现世生活有多少不如意,她从没停止过对人世间美好的追求,她自由而独立的精神探索,身心不二,她的人格是自立的。而这种自立的人格,正是胡适先生所说的产生良善社会的基础。
心有所依,便无畏远方。永远以前行者的状态和直立者姿态向前,不管永远有多远。她追求的人生境界在她的散文里都有很好的体现。
不负韶华,像高晓松妈妈张教授所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她的散文集《给自己点支烟》,那里面记录着她脱胎换骨的人生历练,那是从一个女生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巨大人生转换,其实这种转换倒并不像她文中所说:“女人遇上爱情,就像一支烟遇上火,注定了化为灰烬的结局,点燃,慢慢燃烧,在轻烟散去后的寂寥中消逝。”而是接近于凤凰涅槃,那是女人的一次再生。
家庭是人生幸福的起点,当一个女人走出父母之家,走向婚姻殿堂时,她将重新再造人生的又一次幸福的起航。这种人生的转轨,有时很吊诡。在父母家里像个天使的人,到了婆家有时却像迷途的羔羊。
作者是家中幺妹,不是大富大贵人家的千金小姐,但也算得上小家碧玉,自有人疼,自有人爱。天生丽质,从小到大喜欢的人多了去了。
她生长的山村有一颗大的银杏树,村以树名,叫白果树村。那树的怀里抱着粗可搂怀的、粗可过腿的,粗可过腕的子孙树萦怀,独木成林,自然可观,想来此村至少也有千年以上吧。她生于斯,长于斯,对这山村爱得深沉,爱到彻骨,爱到草木皆我伴侣,爱到沟沟坎坎都伴我共生共长,长成她骨子里、血脉里的基因密码。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像鲁迅之于百草园,像梭罗之于瓦尔登湖,这山村给了她最初的尘世印记,给了她人生美好童年,也给了她一生的追求与回味,那是她心灵的港湾。
我常开玩笑地对她说,说她的散文里透着早春树木绿色的呼吸,她的文章里有富氧厘子,清新脱俗,回味隽永。
长大后嫁为人妇,家在海边,潮来潮往,朝看日出,目送晚霞,又使她的文风多了浪漫,多了胸怀,多了从容与潇洒,多了生气与活力,多了向上的朝气,那是背负青天的鲲鹏之志,那是人之为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白来一趟的理想信仰。
“山川是不卷收的文章,日月为你掌灯伴读。”(简媜《空灵》)日月星辰照耀着她。她如鲸向海,如鸟投林,退无可退,抬头仰望,日月光光,尽管脚下现实生活中的便士也常让她不那么裕如,但她满怀希望,在山海间得大自在。
她一步一步,认真地赏读人生的三部书,无字的书,有字的书,心灵的书。(伤痕文学代表作家卢新华语)边读边悟,边悟边写。她的学问都是点滴自修而来,而且都是千锤百炼,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她的文字极见功力,她的散文从传统一路走来,却是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虽雕虫小技,而不离道也。她的散文反映了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变迁,不仅是人的心态,更主要的是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市民阶层的心理变化,在诗意表达的背后是深沉的忧患,是社会断裂时无助的呐喊,自我成长不屈的探索,中国梦时代大潮中平凡人的人生进取与奋斗,人性之美,人类终极关怀的温暖在她的笔下汩汩流淌。
二、诗意寻觅
她的散文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怀揣理想,相信人间大爱,相信文化的未来,文明的前路光明灿烂。她的散文虽然篇幅都不长,是习以为常的小情怀,但却有着深刻的社会自我认知与文明解读。
在她自我的时空里,我们仍然能找到社会时空的大投影,或者说她的散文本身就是社会大时空在自我空间的投影和折射,因而在她的文字的河流之下,是社会的惊涛骇浪,其实每个人都活得不易。像堂吉诃德,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有时是风车,有时是羊群,有时是一地鸡毛,谁的人生不是在苦斗苦战苦思之中?但她心怀理想,向前进。“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谁把幻光当作幻光,谁便沉入无边的苦海”她诗意寻觅,孜孜不倦,焚膏继晷。“只有用心将心上的雾气淘洗干净,荣光才会照亮最初的梦想。”(《百年孤独》)这一天已经来了吗,这一天即将到来乎?其实这在她都任其自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爱来不来。
她深知有些东西迟早会来,所热爱的一切,有一天会反过来拥抱自己。在破浪之前,她仍需沉淀。前路浩浩荡荡,万物皆可期待。我心光明,身心不二,纵千山万水,也必将抵达。
在她诗意寻觅的世界中,你能看见那一抹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她寻找诗意的栖居,她回答哲学原乡的冲动,有时大气苍茫,亘古如斯,有时时空无限,在永恒与无限中她诗化和升华人生的小我、小情怀,但格局气象依然不俗,可称得上是小写意大自在。
她追求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她笔下的乡村、三月的桃花、十月的红枫、那些美丽的自然生态,那些故乡的原风景,那些无字的书,给她以生存的坚韧和人生的美好。那些有字的传承文明和文化的书,滋养着她的心灵;而那种心灵的书,让她在前行的道路上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她的散文作品里,自然在诗化中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人生启迪开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里有她生命的律动,她真实的点点滴滴,是真性情、真文字、真正去记录自我人生存在的意义,像加缪的散文《重返蒂芭萨》,故乡的原风景,给予他的是人性的坚守和对予苍生的人道主义情怀,那里充满了基督的人间大爱,他的重返,不仅是为了凭吊,更像是回到精神与肉体的故乡,从昔日的神性与荣光里寻求慰藉的力量。在马永娟的笔下,故乡的山川给予她的是精神复活的力量,是美的力量和爱的力量,故乡的一切都是这样美好,哪怕就是贫困的岁月带给她的也是一种亲情守望的力量,哪怕是吃了不该吃的别人送来的礼品,也是让她难以忘怀的童年最深沉的记忆,因为在母亲的责骂中知道了人间道义冷暖,母亲那叹息般不忍的怜爱目光。她的笔下流淌着的浓浓的爱意像月光下流淌着宝石的涓涓细流,那么晶莹透亮。
在对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的转型考量中,作者是通过生花妙笔在桃红李白的映衬中来写的,在自然生态的美好描写中进行比照的。当下单向度太过物欲的追求与感官享受,让社会过于浮躁与喧嚣,在乱花迷眼的无措中彷徨和盲从,让人走上了被奴役之路,产生了社会性的焦虑,作者在诗意栖居的人生寻觅中,以灵心慧手营构生命的本真,进行精神突围。她的作品里留着淡浓相宜的乡愁,这乡愁是她的前生,也是她的今生,也许还寄托着她的未来。
故乡是她永恒的疼痛,也是她永远的精神家园。故乡仿佛凝固成永久的定格,净化成心灵的殿堂,让她不断受洗,那是时空里如明月一般永远纯净的仙天佛国。
家是一种巢穴,是一种生命的亲切,是一种永远飞不出的温存,人生的幸福是从家开始的。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感知感觉真实地以我笔写我家,宇宙山河的浪漫、生活点滴的温暖在她的笔下都是有温度的、有爱意的,不信你去系统细细地读她的散文集,甚至你只要随手翻开她的散文集,试试读上几篇,就会不忍放下,那种乡愁让她引起共鸣,那种美丽自然生态让你流连忘返,那是一个充满了人间爱意的世界。
她的《林间物语》更是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人间美丽的所在,仿佛你不去,今生都会留下遗憾。在那里自然的一切都是那样美好,都有情有义,物我一体,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人世间美以及对美的追求是永远不能变的,那些写下我们文明前行——人间正道的骨子里的东西是永远不能变的。我敢说,在我市的作家中,一以贯之地洋溢着对人世间这种爱的讴歌的作家当中她是独一无二的。
故乡的原风景又在哪里?回家并不意味着抵达,有一天,你发现故乡比你还漂泊,就算我们一道往更早的好时光走,过了天涯都不定居,此成彼,彼成了此,我们还是走不回去。高度物质文明改写了我们城市,更使得乡村失血、乡士失色、乡邻失去了底气。家神庇佑的老宅也在征迁中让位于道路、让位于城市规划,邻家小姐姐的大辫子卷了黄了,就连眼珠子周边也蓝了……原乡已变成一个落后和失败的符号,是欠发达不发达的代名词,像美国的乡村音乐无论多么好听,走向城市的道路毕竟越走越宽了,这是发展中不可逆的现实,故乡即便不让我们生自卑,但也很难再抬高。我们仍然会在“蛐蛐”的秋鸣里听到一种温暖,我们要求的太多,就会走向文明的反面“过剩的欲望,过多的贪婪,蒙蔽了我们的本性。在自然的废墟上,在其他生灵的血泪里怎能建立起人类的天堂。”她说得真好。
墙头摇曳的狗尾巴草,墙根是万籁的低鸣,仿佛一段播不尽的磁带,为你压缩了太多的故事,此刻你才知道你的童年在故乡的某处山阴道上知了般鸣唱,在蜻蜓翅膀上颤动,风在歌唱,歌唱它曾去过的地方。她的笔下,万物有灵,万物有爱,像神灵的絮语,万物都生机盎然。然而现实社会中,我们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是我们的宿命,所以她的作品有挥之不去的惆怅。
三、诗化语言
作者文笔十分优美,那种诗化语言,俯拾皆是,炼字炼词几近炉火纯青,又非一日之功了。她是拙中见巧,让人浑然不觉,几无败笔,让人啧啧称叹。在她的每本文集中都有这样一种诗意隽永的文风,这在我市作家中能达此程度的并不太多。
你知道人可以在与花朵的对视里穷尽一个瞬间。在这无法拂落的凝望里,你忽然明白了来时的急切。你知道,树的心思都在这花里了。四季轮回,树一直在酝酿着这一刻的开放。树用它看风雨晨露,看日升日落,看一群一群的花喜鹊驮着夕阳归巢。轻轻地闭上眼,一任桃花的气息弥漫过来,在微醺中做一个桃花梦。(《独坐涧过看桃花》)
她以文字作画,诗情画意。在《月光不锈》中,她起笔振迅,开头破空而来:“月光,只有老家小村的月光,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月光。”她的望月思月多么温情又温暖,月的情态多么变幻无穷。
“二八月圆之夜,飞镜重磨……遥望东山,等待我心中不染纤尘的月亮。”像闺中密友重逢,等待的心情是美妙的,接着她描述了月亮升起的整个过程,用了多种感知的力量,把月亮的情态、形态表现得如此温馨,她用拟人、比喻、通感、蒙太奇等多种艺术手法,把月亮写得婀娜多姿、顾盼生辉,不同凡响。
初升时,天与山交接处,抬眼可见的“耀眼青白的光”到慢慢地,月亮像个怕羞的少女挖出的小半边脸,接下来过渡为“难耐寂寞的她半遮半掩地露出了圆圆的白玉般的面庞,发出象牙般圣洁的光,再变幻为像柔情的手给人以轻微的抚慰……如一缕春风徐徐落入人怀中……月亮轻移莲步……成了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悬在了暗蓝色的天幕上;周围一块块鱼鳞状的白云恰似两条戏珠的龙。明珠在云缝里缓缓地游着,时隐时现,故意和龙捉着迷藏”这两段写得极具动感,拟人象征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运用纯熟,像电影镜头,这些意象反复叠加,形成了大美的意境,像童话世界那么纯洁美丽。
由“迷藏”自然过渡到儿时捉迷藏的回忆,文章的起承转合妙在随心所欲。我想起我老师常国武教授讲古诗词创作时,讲到那些绝妙好辞时,他会说上“好啊好啊”,真的让你回味无穷。
她以城里月与山村月作比较,并非为了厚此薄彼,而是以此来映衬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带来的巨大反差,时空的无限、美的永恒,不能不让人生哲学上的思考,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现代化之旅不容易,现代化孕育着破坏,这种破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物质享受的当下人们精神披离,心为形役,身为物役,我们太过物质了。人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又无不受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在变与不变中人们有着自己的考量,人对自然美好生态的向往、对文明前行和谐和美好向往是不能变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种美好的情愫是不能变的,如果这些美的东西都不存在了,那人生存在的价值何在呢?
文未又以不结作结,“恍觉夜下生翼,化作了一缕小村的月光”给人留下广大的思考空间。
作者表里俱澄澈,美丽的月光映衬美丽的心情,二美并具的修为,自然让我们和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幸福和自身完美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形成共鸣,而能够反思恰是文明前行的重要支撑力量。无论走多远,都别忘记当初为何出发?
其实她的篇篇锦绣文章,都和她辛勤耕耘分不开的,她在这条路上从儿时、花季、青春,初为人妇、人母,人到中年,到今天。数十年间她一路寻梦而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她的文学梦,像明月挂在中天,摇曳金黄的轻响,梦里的花,被风带到它想去的地方,燕子来时,带来明媚的春光,更带来美好的祝愿:采得百花酿成蜜,苦尽甘来我自知。
文学是她终生的追求,终生写作,要战胜自我的懈怠,又要放下单一的执着,要不断发现向上的阶梯,找准自己的创作风格,主题和内容,一以贯之,在不间断的创作中找到自我更新的途径。“在我看来,艺术并不是一种独自的享乐。它是通过给予最大多数人以关于共同的苦乐的特殊形象,来使之受到感动的一种方式。”(加缪语)近年来作者的创作出现了井喷现象,创作仍然处在上升期,她的创作之路必然会迈向更高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