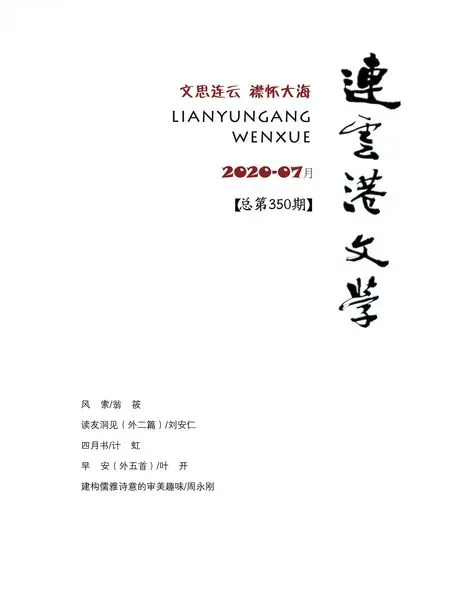乡愁,母亲的情结
浦仲诚
五月底六月初,又正是麦黄菜籽熟的收获季节。又想起母亲生前种过的几分菜地,如今已荒芜多年,而母亲生前劳作的身形,却犹如在眼前。
十八年前,父亲因病离开了我们。那时,剩下母亲一人,仍住在小镇上那座单间小木楼。母亲却始终不肯随我到家生活,她舍不了乡下小镇那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屋,更舍不了她种了大半辈子的那几分菜地。我们几个做子女的,虽然再三地劝,固执的母亲,总是说舍不得老屋空关,舍不得那几分菜地,硬犟着坚持着她的习惯,依然一个人,居住在那座孤零零的、已建了五十多年的简陋小楼。陪伴母亲的,只有依然保持着慈祥脸容的祖母遗像,和依然保持着微笑的父亲遗像。母亲已八十二岁高龄了,到底是什么力量,能让这么大年龄的老人,不肯来儿子家同住,而依然能一个人,早起贪黑地拾掇着那几块加起来足有半亩地的菜地呢?
父亲逝世后十多年来,我和弟妹们始终不忘每周双休日去看望母亲。每次去时,总带上一些母亲喜欢的菜,和她生活必需的日常用品。陪母亲说说话,为她做些家务,偶尔也帮着干些田里的活。
我听了,心中一阵揪紧。心中寻思,我大前天回去,见母亲行动迅捷,身体还挺好的,怎么才过了两天,会这样呢?丽红告诉我说:“老妈怕天会下雨,所以昨天她一个人,去把那几分地油菜籽全部割下来了,会不会是把她累坏了。”
母亲身体硬朗,一生从未生过病,更没住过医院。我分析,母亲现在年龄大了,血管易硬化,很可能她是收割时太用力了导致“小中风”了。这只怪是我们几个儿子的孝心,没有犟过母亲对老屋对田园的情结,才会有如此状况。
我快速联系通知了两个弟弟后,急把母亲送到市医院急症治疗。把所有该做的,和不必要做的检查全部做完成后,妈的病情总算有了说法。医生确诊,母亲是因为脑部毛细血管破裂,导致了“小中风”。医生说,情况还不算严重,但住院治疗是必须的。在医院近半个多月的治疗中,兄妹几人轮流着陪护侍候。经医院精心治疗,十多天后,母亲的神志逐渐恢复了清爽。虚弱的母亲,却依然念念不忘,已经割下十多天,但仍躺在田里没打收回家的几分地油菜籽。
为了让母亲安心养病,我乘着陪护轮空的一天,冒着高温天气,一个人到了乡下母亲的油菜地。我比母亲小二十岁,离开农村三十五年了,烈日下搓菜籽,如此繁重的农活,我尚且累得气喘乎乎,更何况我那年迈八十的老母亲呢,我边干边想。
在田间,我冒着烈日连续干了五个多小时,劳累了大半天,终于把让母亲牵肠挂肚的油菜籽,全部打收回家。回家安放好后,我又把两个半袋子油菜籽拍了照片,发微信给在医院陪护母亲的小妹手机上,叫小妹给妈看一下。小妹在电话中告诉我:“妈看了打下的油菜籽照片,她原来紧锁的眉眼,终于终于露出了放心的微笑。”小妹还在电话中调皮地说:“哈哈,妈叫我对你说,谢谢你。大哥你辛苦了,我也谢谢你。”
母亲在市医院一住,就是半个月。这十多天的治疗,是卓有成效的。这天,照例的病房探查后,母亲的主治大夫跟我们说:“老人家的病情,由于得到及时控制和治疗,现在已经基本康复了,后天可以出院了。但是,老人家的年龄大了,身边千万不能离开家人照顾,加上现在她脑中毛细血管曾破裂过,犯过“小中风”,因此更不能再独处生活了,一旦再犯病,是有生命危险的。”
母亲年迈,双耳失听,我们虽然已经为她配装了一台助听器,但由于母亲双耳失听严重,助听器为她助听的效果并不理想。主治大夫跟我们说的话,母亲没完全听清楚。我大声告诉母亲:“主治大夫同意,您后天可以出院了,但是大夫说,您再不能一个人独住乡下了,如果您一个人再坚持独住乡下,很容易会再犯病的,如再犯病,会有生命危险的。”我还告诉妈:出院后,您今后就别住乡下了,就住到我家去,我们母子应该天天住在一起。
在电气工程建设中,会涉及到大量信息和数据,是重要的参考标准,通过认真分析可以了解实际状况。在缺乏数据参考下,施工活动是盲目的,严重缺乏科学性,所以要自觉遵循,对实际情况有全面了解。另外参数对工程标准评估也发挥着有效作用,一定要符合规定要求,不能出现太大的偏差。参数制定要根据工程而定,体现出合理性,可以指导其他工作顺利开展。由于数据类型多、内容复杂,所以要进行有效管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方案。在参考的时候,数据信息和实际情况要相适应,看是否达到规定要求,便于对出现问题及时发现和纠正。
想不到,母亲听明白了主治大夫的叮嘱和我的话后,又犯起了倔。她说:“我哪能就这么容易犯病呢,你叫我以后住你们家,那乡下的老屋怎么办?那几块自留地怎么办?谁去种?逢年过节时,谁去为你爸、你好婆(祖母)上香祭奠?不行,出院后我还得回乡下去,你们谁也别劝我。”
母亲的身体虽然依旧虚弱,但她说出的话,却斩钉截铁。母亲的倔强,让兄妹几人犯了难。我把弟妹们叫到病房外,商量好了对策。
六月二十一日,终于到了母亲康复出院的这一天。民间俗话说得好“爹亡,长兄为爹。”按照与弟妹们预先商量好的决定,作为大哥,理当由我出面与母亲摊牌。
我对母亲说:“妈,今天为您办出院手续,为了您的健康和安全,也为让我们作为儿女的安心,您出院后,肯定该住到我家去,这是我们兄妹们一起商量的决定,您就别再倔强了。”
母亲却板着脸说:“叫我住到你家去,你家的公寓房,好像鸟笼一般。你们的邻居,我都不认识,我不习惯。再说,我生了三个儿子,又不是只生了你一人,凭啥叫我住到你家去,我可不去。”
我听了对母亲说:“妈,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我来问您,我们兄弟几人是不是您亲生亲养的子女?”母亲疑惑地看着我的脸,肯定地说:“怎么不是,你们兄妹几个,当然是我一把泪一把尿生养大的儿女啊。”我假装生气地说:“妈,既然我们是您亲生亲养大的儿女,那您现在对我们,也太不负责任了。”母亲听了我的话着急了,她惊诧地瞪大双眼看着我问道:“我怎么对你们不负责啦。”我假装严肃地说:“妈,孔夫子说过,对父母而言,子幼而不教,是父母之过。对子女而言,母老而不孝,是子女之罪。再说,自古就有‘百事孝为先’的古训。妈,您现在年迈身体有病,还不肯让我们做儿女的尽一份孝心,我们又没法天天去乡下看您、陪伴您。如果您继续独居乡下,一旦再发生意外,到时候,我们几个作为儿女的,不是要背上不孝的罪名吗,如果真发生了这种意外事情,您不光耽误了自己生命,也会害了我们的名声啊。您说对不对呢。”弟妹们听了我的话,齐声附和说;“妈,大哥讲的对,您虽老了,应该要对我们的名声负责的嘛。”母亲听了我的话,呆呆地沉思了良久。过了好一会,母亲才抬起头看着我们,缓缓地对我说:“我明白,你们都很孝顺。可我养了三个儿子,也不能光住在你一家呀……”
听了母亲的话,我知道母亲已经被我们说动心了。我趁机说:“妈,这个事您放心,您年年住在我家也没问题。您认为要公平对待的话,两个弟弟家也随时准备着您去住,您在我仨兄弟每家住一年,轮着转,你看行不行……”
小妹听了,打断我的话说:“妈,我虽然是您嫁出去的女儿,您也可以住到我家去,我们兄妹四人每年轮着转也行。”现场热烈的氛围,打动和感染了母亲的心,母亲终于勉强同意,首先住到我家去一年。
为母亲办完出院手续,兄妹几人拥着母亲,坐上小车离开医院,一路奔我家而去。从此,侍候母亲刷牙、洗脸,为母亲端饭、倒水、洗衣,侍候母亲服药、睡觉,陪母亲忆往事、拉家常,带母亲去街头逛逛,去石洞景区坐坐喝喝茶,带母亲去荡口古镇等地旅游,还抽空带母亲回乡下老屋看看,细心侍候着母亲的生活,成为我与妻子每天的重要事情。妻子还为母亲买衣服,买补品,一起上街溜达。三个弟妹也轮流着常来探望母亲,他们总为母亲带来一些她喜欢的零食和水果。
在我一家细心的侍候下,起初一个多月,一直坚持帮助母亲服用着医院带回的药,并加服一些滋补类食品,以此巩固着治疗的效果。两个月多后,母亲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状态,她脸色渐渐恢复了红润,她除了依然耳聋以外,食量与我一般,行动挺快捷,说话口齿清晰,记忆率很好,思维正常,人也明显胖了许多。
我才十岁的孙女梦妍暑假放学在家,每天有许多时间陪着太祖母说话、玩耍。哈哈,一老一幼两人挺合得来的。玩耍间,母亲高兴地对玄孙女说:“老太太我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过几天等你开学后,我又可以回葛墅老家去住了。”小孙女把老太太和她说的话,悄悄告诉了我。梦妍告诉我说:“好公、好公,老太太说,等我开学上课后,她就回乡下去住了。”
果然,梦妍开学没几天,母亲便向我提出要回葛墅老家住的要求。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刚侍候母亲洗完澡,与母亲坐一起坐在我书斋中拉家常。母亲吞吞吐吐地对我说:“芳芳(我的乳名),明天六号是礼拜天了,你能不能……能不能送我回乡下老家去住吧。”
我听了母亲的话,没马上回答母亲,母亲怔怔地看着我,等我答复。稍停了一会,我轻声反问母亲道:“妈,您老是说要回家去住,难道儿子这里的家,就不是您老母亲的家吗?我们有啥地方做得不对呀,您尽管讲,我们可以改正的。”
母亲听了我的话,低着头说:“我知道,你当大哥的,尽心孝敬我,你带头带得好……”母亲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虽然说,你的家也就是妈的家。这话虽然是可以这样说,但是这里的一切,毕竟是你自己在外辛苦创下的家业,我和你爹一生虽然辛苦,但仅仅是生养大了你们,没有为你们盖房造屋,没有为你们创造什么,我不能给你们添累赘,添麻烦。再说,乡下老屋没人住不行,那祖坟上几分自留地没人种也不行,还有你好公好婆的墓地也该要有人照……”
听到这里,我知道,母亲的犟劲又上来了。我接过母亲的话头,继续耐心地劝说道:“妈,一切财物都是身外之物。您和爸,在几十年十分困难的岁月中,把我们四个儿女拉扯大,供我们上学、读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是你们给了我们生命,是你们教养我们长大,是你们教会我们怎样做人。如今,我们几个儿女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你们教养培养我们的结果。我们感谢您和爸,对我们在孩童时代的严格教育和管束,所以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我站起身拿来热水瓶,为母亲的玻璃杯中添了一些水后,坐近母亲继续对母亲安慰说:“妈,您也看开些,乡下老屋和自留地,是没人会抢占去的。再说,财物毕竟是身外之物。人一生,不就是一碗饭,一张床吗。您年龄毕竟大了,经不得劳累了,您与儿子我住在一起,我放心,弟妹们也放心,您也安稳。我们可以常常抽时间带您去乡下,看看老屋,走走田头,和老邻居们打打招呼,扯扯家常,这也许还会更显得亲切呢。”
听了我这一席话,母亲缓缓地喘了一口气,说:“唉,我确实天天想起那些老邻居们,几十年了,有感情啊……”母亲顿了一下又说:“唉,你实在不肯让我回乡下住,我也只能这样了哇。”此刻的母亲,眉间露出了红润,双眼显得亮亮的,似有泪水在眼中不停滚动。
听了母亲的回答,瞬间,我的心头虽如释负担,但百感交集。时间过得很快,母亲住到我家已近一年了。在这三百六十多天的时间里,母亲心中的想法,如上述那样,曾向我提过多次。我总是耐心劝慰母亲,或者开车带她回一趟乡下,看一眼那矗立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的老屋和已经荒芜的菜地。
其实我明白,我的家人和我的弟妹们都明白:尽管我们作为子女对她十分关心、万般孝顺。但是,我那八十二岁的老母亲,在她胸怀中那累积一生的乡土情结,却时时在触动着她的心灵。在老母亲的胸怀中,那一份乡愁之情,始终牵系着她那颗在故土上搏动了八十二个春秋岁月的心。母亲的故土情结,成为她思念家乡,不愿离开家乡的精神动力。
三年后的五月,母亲在三弟家生活了快一年。想不到的是,母亲竟得了严重胃疾。虽然特地从上海请来名医为母亲做了手术,在医院医治了四个多月,还是没有挽留住她的生命。母亲在弥留之际,仍然惦念着她乡下的老屋小楼,仍然惦念着祖父母的墓地和她的菜地。
如今,是母亲离开我们第二个年头了。为了母亲的那份乡愁,为了我的那份思念,我经常悄悄地驱车而行,回到小镇故居、回到当年下乡劳动过的碧水小村去看一看。在清明节,到祖父母的墓地添一下土,在父母的墓地上燃一炷香,何尝不是一种深深的乡愁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