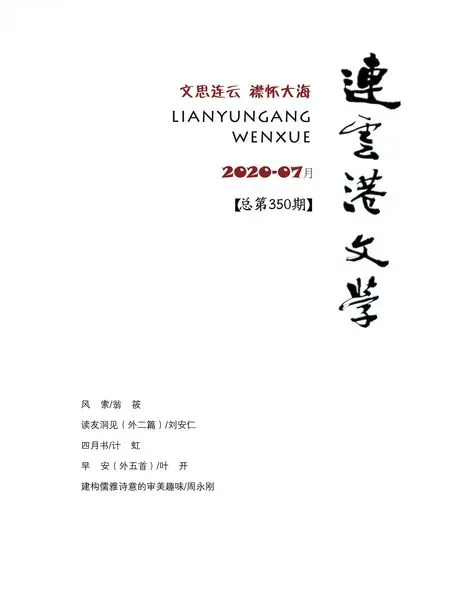清和园
陈武
清和园不是一座园林,也不是文人墨客的馆阁斋榭,而是一家店铺,一家很有文人品相和文化韵味的特色店铺。
在新浦老街上,有许多林林总总的店铺。由于电商的兴起,这种传统的店铺已经日渐式微了,经营也越来越困难。但对于某些特殊的商品,其冲击不但不大,甚至还会显现出实体店的优越来——比如茶叶店。
没错,清和园就是一家茶叶店,店主人就是这篇拙文的主角何洪青先生。
如果在老街上走一走,清和园的招牌一定会引起特别的注意,不仅是名称好,招牌上的字也好——出自已故著名书法家杜庚先生之手。说起清和园和杜老的关系,何洪青还记得当年题字时的情景,那年杜老八十多岁了,已经不太怎么握笔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何洪青和几位文化名人一起茶叙,在座的也有杜老。当何洪青和许厚文、王善同等先生说起茶的不同品类、不同地域特点并且对茶文化引经据典的时候,杜老感慨地说,没想到喝了一辈子的茶,居然还不知道茶有这么多说道,真是受教了。何洪清更是谦虚地请杜老多提携,并透露出还差一块招牌字的时候,杜老会意地一笑,让何洪青取出纸笔,欣然题写了“清和园茶庄”的招牌大字。这真是一块金字招牌啊,何洪清特别珍视,专门请名家刻成匾额。如今,这块招牌,成为老街上的一张名片,也是港城为数不多的杜老亲题的牌匾之一。
我对茶叶的了解不多,可以说是外行,也无心去研究茶文化。但喝了几十年的茶,加上经常和清和园这样的名店接触,对茶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茶叶的经销,一要闻,二要看,三要尝。而这三者,恰恰是电商所办不到的。先说闻,闻当然要得其味了。茶香是一种特别的香,语言无法形容。说香有多种,茶香便是一种。就好比说绿颜色有多种,抹茶绿就是一种绿。你不能说抹茶绿是什么绿,就是抹茶绿。也不能说茶香是什么香,就是茶香。当然,何洪青也从专家的角度说过,茶的香型也可细分,比如苹果香、玫瑰香、板栗香、兰花香等等,这种在茶香味上的讲究,是非专业人士莫办的,一般的茶客大约和我一样,会笼统地说是茶香吧。再说看,亲眼所见才可曰看。网上关于茶叶的照片,包括朋友圈发上来的那些茶叶的照片,都不可信,至少不可全信——美颜都达到乱真的效果了,你还能相信照片吗?最后是尝,尝就更不必多说了,不在现场的尝,不亲自泡一杯,那还叫尝吗?三者之外,还有品。品,可以说是另一个层次的境界了。看过了好茶叶子,闻过了好茶叶子的味儿,再尝一杯好茶,接下来才是品。而品,又和环境有关,和茶友有关,和茶器有关,在人声嘈杂、机器隆隆的地方,或其他气味(比如油烟味儿)浓烈的地方,和在安静的茶室里以及清和园这样的茶店里所品的茶,那可是不一样的。老茶客对于品,可能会更看重一些。品当然也包括闻、看和尝了。但是,怎么品,品出什么味儿来,才可真正分出茶客的高低。所以说,买茶叶,还是实体店的茶叶才让人可信,通过看、闻、尝、品,才能晓知其中的三昧。
清和园的主人何洪青,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茶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一家老字号的国营茶庄“生庆公”工作。单位和海州的百年中药房三和兴毗邻。说到三和兴,那可是新浦老街上响当当的招牌店,其知名度,足可以和整条老街比美了。和三和兴的历史差不多的生庆公,同样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其专业卖茶叶的经验和多年形成的风俗、民俗、习俗,地方历史文化专家彭云先生在《海州乡谭》里写过,在此略过不提。而何洪青经过生庆公的历练,便有了传统茶文化和现代茶知识的交融,也便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关于茶叶的理念。所以清和园在他的经营下,便显现出特别的品格来。他曾解释过“清和园”的来历和意味,大致意思是受三和兴的影响,三和兴的三,是从《道德经》而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是数字当中的特别存在,照《淮南子》的解释,二是“阴阳”,三是“阴阳合和”;和,是和气生财之意;兴,表示兴旺的意思。清和园的招牌也是可以说道说道的,这里的清,有清新、清明之意,清,又最宜茶;和,如此所述,除了和气生财之外,还具备儒家文化的其他特征,有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意;园,就不用多说了,可以简单理解成一处场所,但又不是一般的场所,园有园林,园艺之意,也含有茶园的隐喻。如果叫清和斋、清和馆,那就不搭调了。还有一点,倒可作为趣谈,就是“清和园”的招牌,和主人的名字颇为贴切。何洪青的名字里有和(何),有清(青),园便是自家的小天地。他说当年离职创业之前,彭云先生曾赞赏过他新起的店名,雅而不俗,淡而有味,并赠有一联,云:“清水新茶香飘四野,和风细雨绿染青山。”该联很好地诠释了“清和园”的意趣,并由著名书法家陈枫桐先生书写,再请著名画家王兵画一幅《陆羽煮茶图》。如今,这和谐的一套联画,就悬挂在清和园里,加上橱架上摆放的许多书籍,清和园就不仅是一家茶叶店了,就和文化密切相关了。
不是有人说过嘛,做生意做到一定份上,就是做文化。而清和园又最能和文化搭界了,这不仅是店内的氛围,还有清和园主人本身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没错,他不仅精通茶文化,写过多篇关于茶和茶文化的文章,还有多篇诗文辞章也频频见诸报刊。甚至他还写过一篇关于《镜花缘》和茶文化方面的研究专论,题目叫《镜花水月一碗茶》。众所周知,《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是海州板浦人,《镜花缘》的故事和海州的山水、传说密切相关,李汝珍利用当地的物产铺设故事,结构情节,完全是有可能的。何洪青的这篇专论,副标题叫《有关〈镜花缘〉中茶文化的一点浅见》。他的浅见可不浅,学术水平非常高,在序引里就开门见山地说,花果山早在唐代就盛产茶叶了,有“从陶庵到风门口,十里茶山”的说法。宋代更是茶叶的集散中心,并引刘洪石《东海名郡》中的考证结论,予以佐证。而清代成书的《镜花缘》,“书中很多茶事描写为我们研究和探讨海属地区的茶文化提供了较为有益的材料。”该专论共分十节,分别是《客来敬茶普遍被人们接受》《茶为媒》《〈镜花缘〉是一部渴望男女平等并提倡女权的作品》《体现了海州社会茶饮品的多样性》《茶馆业的兴望景象》《茶的药用》《茶文化的普及》《云雾茶茶名的出现》《〈镜花缘〉中茶文化的局限性》《〈镜花缘〉的解读,对于发展茶园旅游,促进连云港旅游业的发展和提高的一点启示》。从这些小标题中,不难看出,何洪青在这方面研究的全面性,也看出了他所用的功力。
从中国古典小说里汲取的茶文化的精华,让我们知道了许多海州地区和茶相关的典故和传说,还有其他典籍中和海州茶叶及茶文化相关的诗赋辞章,并且对云雾茶的何时出现进行了论证。这篇专论,不仅是对地方文化的贡献,也打通了文学作品和茶文化联姻的通道,十分难得。
何洪青读书庞杂。除了《镜花缘》里的这些茶艺知识,其他古今文学作品里关于茶的描写,也是他平时特别留心的。比如《红楼梦》,该书更是一部生活大百科,许多回目里都有饮茶的描写,最有名的要数第四十一回里的《贾宝玉品茶栊翠庵怡红院劫遇母蝗虫》,有近两千字的篇幅,描写了品茶的全过程,很细腻,很传神,不仅写吃茶,还把人物的一颦一笑、对话中的机锋,都轻盈、准确地描写了出来。比如妙玉捧出的茶盘,是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茶盘里是成窑五彩泥金小盖钟。贾母看了,说:“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道:“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三言两语,就点出了主客都是品茶的行家。茶的品种,还有烹茶用水,陆羽在《茶经》中都有专章论述。而在茶器上,妙玉给贾母使用的是“成窑五彩泥金小盖钟”,众人使用的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还有妙玉拉了宝钗、黛玉吃体己茶时所用的茶器,都是善饮者特别看重的。更为玄机的是,小说写到妙玉给宝钗、黛玉、宝玉所用的茶器时,采用的描写,真是别有用心,难道不是吗?三人的茶器各不相同,宝钗、黛玉的茶器上都镌有名称,还有引申的文字,字体也不一,看似作者随笔点染,实质上都有隐喻,就好比秦可卿卧室里的古董陈设。而宝玉吃茶的茶器却是妙玉平日里用的绿玉斗。这一笔很妙。妙玉如此讲究之人,连刘姥姥用过一次的成窑茶杯都嫌脏不要了,却用自己的杯子给宝玉饮茶,而宝玉又不解其意,发牢骚道:“他两个都用那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的反驳也颇有意味:“我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此种对话,不会仅仅是谈论茶器吧?妙玉借吃茶之机对宝玉的调侃、讥嘲,口气却非比寻常的亲昵,与对待宝钗、黛玉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她笑话宝玉吃了一海,说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饮骡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细细品咂这些话,小儿女的茶浓情长都暗含在这口角之中了,这和对宝、黛二人的态度是天壤之别的,比如黛玉不解风情地随口一问:“这水也是旧年的雨水?”接下来妙玉的话真是精彩之至,她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鬼脸青的花瓷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春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清淳,如何吃得?”妙玉的话也够尖酸的了,这是《红楼梦》里少见的描写。黛玉有多少人宠啊,没有人敢用这样的口气和她说话。而作者也只用“黛玉知道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也不好多坐”来下了台阶。但不得不说,妙玉所论的烹茶用水之论,真是笔酣墨饱,痛快淋漓,道出了《茶经》《茶谱》之类的专书未曾说过的细节。何洪青对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和别的茶艺方面的专家不同,他不仅懂茶,懂文学,更熟知并能真切地体会出文学书中的这些精细的描写。比如他在专论中《茶文化的谱及》一节里所引论的,先通过《镜花缘》第九十回《乘酒意醉诵凄凉句警芳心惊闻惨淡词》里道姑与闺臣的对词,词云:“鞋飞罗袜冷,秤散斧可烂。校射展舒臂,烹茶如心脾。”何洪青由此引出了古代文人墨客的关于茶的诗词多首,可见他对茶文化的了解之广,研究之深。这些都和他平素的阅读、积累分不开的。
我和他互为微信好友,从他发在朋友圈里的文章看,能大约知道他的兴之所在了。除了他自己的文章,文学方面的,茶艺方面的,还有转引的多篇关于茶和茶文化的论述。比如茶叶的标准化方面的,他一口气转了十篇。我猜测,他如此勤快地转引,一来是自己收藏,将来使用方便,更主要的,还是为了传播众人,让茶客们更多地知晓这方面的基本常识和相关知识。有一篇《墨韵茶香——那些有关茶的书法》,是更为典型的一篇,也为我所喜欢。这篇文章的搜集者颇为用心,把历代大书法家书写的关乎茶的法帖,按年代一幅一幅陈列,既可欣赏书法艺术、墨迹源流,也可略知茶艺,更可以揣测这些大名家和茶的关系,从怀素的《苦笋帖》开始,一路下来,有蔡襄的《精茶帖》《思咏帖》,苏轼的《新岁展庆帖》《啜茶帖》《一夜帖》,黄庭坚的《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米芾的《苕溪诗帖》《道林帖》,赵令畤的《赐茶帖》,徐渭的《煎茶七类》,汪士慎的《不知》,金农的《玉川子嗜茶》,郑板桥的《湓江江口是奴家》,最后是吴昌硕的《角茶轩》。细细打量这些法帖,一幅幅眼养的书法艺术,一段段茶艺的诗文章句,是书艺、文艺和茶文化的完美“联姻”,可谓是“天作之合”了。我有时会想,何洪青搜罗这么多茶方面的资料,也否也会仿效古人,编一部自己的《茶经》呢?
在清和园里,常会聚集一些文化名人,彭云、韩世泳就是常客,已故的张传藻、刘兆元、刘洪石诸先生也喜欢到清和园里清谈、品茗。彭云先生有句风趣的话常挂在嘴上,喝茶找小何,买药找吴舟。吴舟是著名的中草药专家,为人低调随和,也是一位乐于助人且性格温润的学者兼作家,出版了多部专著。我只要得便,也喜欢去清和园小坐坐,自然都会讨得一杯好茶了。谈话也便从饮茶开始,慢慢波及文学。何洪青比较清瘦,话风直爽、干脆,臧否人物,评论时事皆能语到意尽,特别是对于那些时尚的伪茶艺家,语气中既有不屑,也有无奈,但又多有宽容之心,认为那也是人家的生存之道和经营策略嘛。
事茶三十多年来,何洪青由20 世纪80年代工作时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一位近乎晒青绿茶般的青涩到陈年普洱的浓醇了,更不满足于每天对着茶杯比较各种茶叶的口感了,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将茶文化与茶科学进行有机的结合。我们茶聚时,他常说,茶学是一门科学,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没有文化的茶学是枯燥乏味的,而没有科学的茶文化,又是愚昧无知的。茶学的科普又必须浅显易懂,对普罗大众讲一些高分子链和大苯环一定不如饮一杯凉白开解渴,空谈茶叶的寒凉、祛湿、养胃则又显得很虚幻。茶叶作为一种健康饮料,主要是茶叶中的内含物质决定的,饮茶有利于健康,但一杯茶绝不是灵丹妙药,用平常心喝茶,既是对身体的保健也是对心灵的抚慰。我是非常赞同何洪青的话的,科学饮茶,喝出健康,喝出优雅,这才是本色。
在清和园坐久了,也常碰到一些茶客来购茶,一些喝了他几十年的老茶客,从不谈价,相信他的公道。也有上了年纪的老茶客,说店主人是专家,何洪青则诙谐地说,你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喝一种茶,真正的专家才是你啊!他向客人推介茶叶,从不推荐那些利润高的高档茶,而是根据客人的经济条件和口感轻重介绍。正如他常说的,适合自己的茶,才是一杯好茶。
这些年,他无论是在电台做嘉宾说茶,还是到学校给年轻的学子讲茶文化,抑或是老年大学给老年朋友们谈饮茶与健康,他都是从科学出发,从文化着手,不盲目,不虚夸。
何洪青还有一颗担当之心,常跟我说起要利用花果山的茶园,搞活茶园经济,集旅游、采摘、示范、品茗于一体,并且准备利用他民主党派、政协委员的身份,写篇提案。并且,在不同的场合,呼吁云雾茶要标准化、规范化。行业管理部门应该指导茶农按照最初设计的工艺流程进行操作,切实做到使云雾茶条索紧结、形似眉状,色泽绿润,香气高洁,滋味浓醇。而现实的情况是,许多制茶人错误地把茶叶的高火香当成了高香茶的标志,云雾茶的炒制出锅前火温过高,以至于色泽干枯晦暗,不够鲜亮。他指出,现代绿茶的加工要求,不论干茶色泽是翠绿、墨绿还是绿润,都必须鲜亮润泽;不论绿茶的香气呈现的是板栗香,还是兰花香,都要求香型优雅,且持久、活泼。
喝酒、品茗、谈论诗文,便是我们之间的日常行状了,特别是听他谈茶时,有意无意间透露的茶知识,都会让我受益匪浅,而他的神情里流露出的对茶的崇敬,对茶艺的顶真,也让我心存感佩。诗人刘毅先生有一次说他有仙风道骨之气。我觉得他是也不是,是,因为已经有了这个迹象,不是,似乎还差点意思。而且“仙风道骨”这个词,何洪青自己也不一定认同。那再继续修炼吧。但如果说他是一介名士,我是没有意见的。我原先对茶和茶文化一窍不通,逐渐能摸到了一点点门径,就是受他的影响。
“君作茶歌如作史,不独品茶兼品士。”我在书房写作或读书,会按照自己的心愿泡一杯茶,在茶香中,便会想到明人杨慎的这句诗,连带的,也会想到何洪青,一算,我们又有好几周没有见面、喝酒了,便拿起手机,打过去,约茶,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