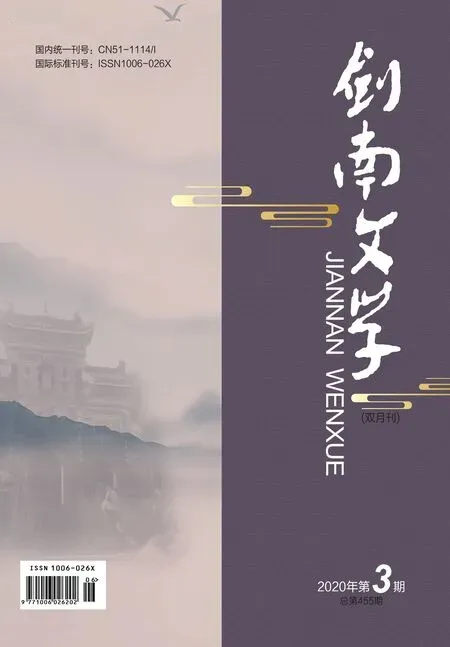浅析《我看日出的地方》中的叙事策略
□童 剑
马平的中篇小说《我看日出的地方》,2019年9月在《人民文学》首发,之后被《小说选刊》11 期选载。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以一棵生长在牛耳湖畔的紫薇树为主线,串联起因树结缘的爱情,寻树过程中产生的人物情感交互,以及在树下生活的几代人的故事。主人公金春早为了救心上人“卖紫薇树”,并不买情的“心上人娄樱子”却投湖自杀;一路随着紫薇树的踪迹到了成都的春早,在新购楼下“巧遇紫薇树”,并通过扦插的方式让“紫薇树再次回到乡村牛耳湖畔”。
从小说的题材看,有理由将其归入乡土文学的范畴。四川历来是一个农业大省,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依旧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许多四川的作家常将目光投注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以及和这一群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广袤土地上,作品常常表现农村人进城后的生活以及对农村生活图景的眷念,这种书写方式在四川乡土文学史的谱系构成中一直都是主流。乡土文学除了因能契合四川的乡土现实这一重要因素外,还在于这种书写能更容易地让作家找到现实与艺术之间的联结点,使作品既能贴近现实和时代脉搏,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反思深度。
在《我看日出的地方》中,马平没有采用惯常的乡土文学“史诗性”的写作方式来表现中国近20年来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场景,而是在创作手法上另辟蹊径,通过将内在的心里世界再造为外化的现实世界,在日常性中抒写时代发展主题。他采用把抒情性融入日常性的叙事策略除了有文学内部因素的考虑,也有外部因素的考虑。因为抒情写作往往重视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容易忽视对外在世界的直接探求;日常性的现实写作又常因偏重对外在世界的表达,有可能忽视文学本身所要求的具体性,对人物的关照也可能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使作品本身缺乏感染力。因此,抒情性与日常性的融合则可能克服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抒情的日常化而言,这一方式能打通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克服文学作品向内转导致的格局太小的问题。现实日常生活的抒情化,则可以对现实日常性写作中常见的问题,起到一种纠偏的作用。马平将抒情性融入日常性中,采用各种手法削弱小说中每个人物的传奇感,重现了近20年来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历程,塑造了不同阶层普通人物的命运。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既有春早、薇子和春美的执着之情,也有青桃的善解人意,还有金家家族的亲情,更有如满文忠这样的农民工。马平通过抒情性的笔调,一一呈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果将他们中每一人物的生活片段提出来加以填补,有可能成为一篇篇动人的短篇小说,可马平只是三言两语带过,让他们成为小说总体叙事中的背景,同时借鉴抒情小说的笔法,深度挖掘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抒情小说兴起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一种小说样式。它们大多在艺术上取胜,以唯美的意境、感伤的情调、与众不同的结构章法和创新的笔法表现人物和故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一种小说样式。其中“自叙传”抒情小说侧重于作家的自我暴露,以及个人私生活和心理的描写,这是接纳日本“私小说” 和其他一些外国小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小说,郁达夫是其中的代表作家。这一时期也有部分抒情小说,不流于纤丽绮靡的个人化抒情,而是将目光投注到当时广阔的现实生活中,具有深厚的文化、社会意蕴,如鲁迅的《伤逝》、老舍的《月牙儿》、艾芜的《南行记》等,这些抒情小说的质量都出奇的高,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不仅是一种文学实践,也是一种生命实践。沈从文曾说过,“文学创作是用人心人事做曲,而自己的作品是用故事抒情做诗。”人类之所以要借助诗、绘画、古琴等方式来“抒情”,是因为文学、艺术、历史和人生,必须“有情”。李泽厚曾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一种乐感文化,缺乏对彼岸世界的信仰,却肯定此生此世的价值,以身心幸福地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作为理想和目的。”而“情本体”又是乐感文化的核心。最终是以“情”,以家国情、亲情、友情、爱情等各种“情”作为人生的最终实现和根本。只有在 “有情”的基础上,生命的意义才能得以确立。
当下一些抒情性的情感都市类小说,往往将人物的主观感受与物质挂钩,如郭敬明《小时代》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其感情往往是可以物化的,使得生命实践维度上的抒情传统面临的困境更加复杂、沉重。正如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的,“抒情的传统主要是偏重书写作家本人或其笔下人物的主观感受和情绪,具有鲜明的个人性和主观主义色彩”。如果一个时代粗鄙盛行,价值和情感都必须兑换成物质才有效,那么这时代的运行逻辑本身就构成了对“情”的质疑,甚至是直接的否定。马平在小说中,通过春早、樱子、薇子、青桃、春美、鲍云龙和鲍云海等年轻人的不同人生片段,呈现农村青年人在近20年来社会发展中不同的情感变化,以抒情的笔法描写他们在生活中的情感世界,赋予他们的是对亲情、爱情和乡愁的不舍、追寻、认同、归属和精神回归,在他们的命运起伏中,向读者呈现出一幅幅城市和乡村生活的新图景。
当下的一些小说读起来总是显得单调,很大的原因是一些作家对物质世界、现实世界越来越没有感觉,缺少日常性。谢有顺曾说,“小说的物质外壳必须由来自俗世的经验、细节和情理所构成,此外,它还要有想象、诗性和抒情性,这样才能获得一个灵魂飞升的空间。诗性产生抒情性,而抒情性的获得和一个作家的叙事耐心有关。”我们常在一些小说中看到,作者往往急于讲故事,而忽略了世界本来的丰富性,在这些小说中是没有声音、色彩、气味的世界。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李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当代生活是没有故事的生活,当代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就是故事的消失。故事实际上是一种传奇,是对奇迹性生活的传说。在漫长的小说史当中,故事就是小说的生命,没有故事就等于死亡。但是现在,因为当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以前被称作奇迹的事件成了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必然改变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以至于作家常常会被淹没在普通人的命运中,以至于许多作家感觉不到那是人的命运,感觉到的往往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日常性往往又会将小说引向一些碎片化的经验,鸡毛蒜皮式的细节,使得小说不再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好的小说作家却常常将写作视角聚焦于社会生活的日常性,不再仅仅通过“故事”书写“总体生活”,而是将故事进行分解,通过某种方式讲出那个无法被总结、提炼与规约的“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奇迹般的有限起因与结果之外,并隐藏着复杂而隐秘的不确定因素。由此,作家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学会观察,从日常性中发现隐藏在生活中的俗世经验、细节和情理。
马平说他曾和朋友在成都郊区看到一片大树,“那些大树并非土生土长,而是十几年前从遥远的乡下收购而来,在此集合待价而沽,却在立正之后一直那样稍息着。我想象不出它们当年呼啸而来的阵势,眼前除了沉寂,就是静穆……我再次把目光投向大树,心里却立即没了底。它们,好像谁都不愿意出头,谁都不愿意往前站,谁都不愿意张扬自己的身世。它们,愿意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吗?”我无法从马平的话中了解树背后的故事,也无法确认从遥远乡下到城郊的大树情系何物,在寂寞后表现出的静穆究竟情归何处;更不知道别的作家在面对这些大树时,是否会感到这种由政治、经济等因素混合而成的否定性力量的强大,从而产生在这个时代对情的书写常常显得无能为力的感觉,甚至让他们感到抒情本身已被异化成为了一种反讽。但在小说中,马平通过紫薇树的离乡、进城和返乡的三个时段的抒情性表达,串联起了小说主人公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在看似没有整体故事性的结构中,引出了20年间次第出场的不同人物。小说既有唯美的意境、感伤的情调,又有与众不同的结构章法,展现了马平通过抒情性的描写展现日常性的高超能力。
第一个时间段是春早和樱子高考落榜后,在牛耳湖畔6年的乡村生活故事。青梅竹马的恋人樱子因家庭原因,被迫嫁给贩卖果树苗发财的鲍云龙,婚后三年身患重病。快破产的鲍云龙想到了春早家的紫薇树,在家务农的春早父子于是决定卖树救樱子;樱子得知卖树消息后选择了投湖自杀,与紫薇树同时离开了牛耳村。第二个时间段,悲伤欲绝的春早,离开牛耳村进城的12年。为见樱子最后一面,春早赶到县城,又为找回紫薇树一路追到成都。在成都的春早干过餐厅服务员、石材销售人员、报纸广告业务员,最后成为策划公司的策划人,目睹了城市的变化和发展,从一个24 岁的青年人变成了36 岁的中年人。他在这期间认识了妻子青桃,见到了离家出走后有了自己事业的薇子,也明白了紫薇树下自己一家人和幺爹的恩恩怨怨,最后在城里新买的楼下找到了紫薇树。第三个时间段,是紫薇树回到牛耳村后的3年。“三年以后,紫薇树上剪下的六根枝条都长成了小树,在牛耳村分三处开花了。我们家那两棵小紫薇树,近距离生长在老紫薇树早已腾出来的地方。白石头也回到那儿,守着他们。”春早的媳妇青桃、堂妹春美、娄薇子也都回到了牛耳村,薇子和春美的“金紫薇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水稻正在抽穗。小说结尾以牛耳村的女人返乡为视角,贯注了作家对乡村振兴的一种期盼。正如马平在谈及小说创作时说的,“乡村的女人们是村庄的眼睛,如果看不到她们,这个村庄的眼睛就是瞎的。我希望在城里能见到她们,在乡下也能见到她们,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太阳照到哪儿,她们就在哪儿。”马平用真挚的文本关照着小说中被迫外出、急于归来、积极发展的农村青年群体,写得优雅、从容、饱满,极具抒情性。
抒情性和日常性的融合还表现在小说中的许多人物的刻画细节上。如春早的父亲常在夜里一个人悄悄出门,天亮前又悄悄回到家里。作为乡村一个单身多年的鳏夫,夜里出门这件事本身就可以给人无限遐想,随着春早父亲的生活片段被一点点接续,读者知道了春早父亲在夜里是去妻子的坟前,将心里话讲给妻子听,仿佛老两口还生活在一起。这里马平就将抒情性写作与日常性的细节做了很好的安排,让读者的心灵受到极大冲击的同时,又将紫薇树下生活的金家人的各种恩怨展示得淋漓尽致。正是春早父亲对情的坚守,让金家父辈之间得以和解。还有青桃的奶奶的去世,青桃告诉春早,“奶奶说,爷爷走后,二十几年前她就想跟去了。她巴不得害那个病呢。她说,那病都是她想出来的,还治它干什么……” 这里没有老人去世后的悲伤,呈现出的是老一辈农村人对爱情的一种感悟。还有一个人物是满文忠。他是春早到成都后合租房的室友,在花市用三轮车送花。小说不仅交代了春早的第一个旧手机是满文忠送的,还多次在春早的生活中出现满文忠蹬着三轮车送花的场景;满文忠最后一次出场,是春早和青桃结婚时,青桃提议送满文忠一部新手机。这些描写表达出的,不仅是春早在社会阶层中的变化,也可以让读者沉浸到春早的生活河流中,在富有共鸣的场景中重温我们的来路;更重要的是,在变动的社会关系中,人物命运展开的诸多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平在日常社会中是如何展开道德想象的,并经由这一想象重申善的信念。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关于伦理和道德的许多定见正在发生松动,但在民间的评价体系中,仁义、善良、讲义气等传统人格修养,仍然是构成民间道德的核心。对于“善”的想象,马平是将其集中在“好人”身上,这种叙事策略是他叙事美学的一种新探索,即让作品回答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好人和如何做好一个好人。
《我看日出的地方》采用唯美的意境、感伤的情调叙写日常生活的细节,通过旁逸斜出的故事结构表现现实生活,表达对中国当下社会发展中人性和人心的思考,不仅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更是对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讴歌。在叙事策略上采用抒情小说的笔法又融合日常性写作,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抒情小说的一种继承,又是小说创作中在叙事美学上的一次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