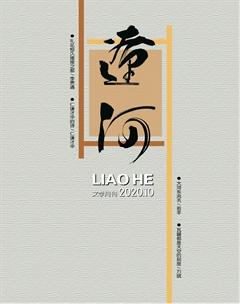瓦罐都是天空的刻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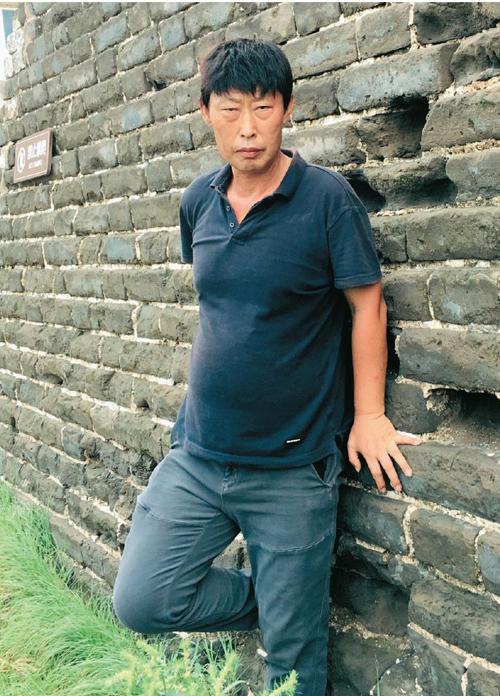
萤火
太阳被我搬动
天空就会震动
包括在地面上的瓦罐
也是我拎着甲壳虫
有些厚的天空
被我在手里捏成纸
但这不等于水面
被我拿到了手中
有些瓦罐出现的瓦片
仍是我的手在白天失手
我只有反复蹲下
才会起落着青蛙
岸上一旦没有了瓦罐
我脸上出现的汗珠
势必会被人们拿走
所以天空在我脸上常空
我们现在见到的白天
是萤火虫为时已晚
如果夜不是太黑
就是我的屁股在闪亮
迟到
有些瓦罐上的虫孔
是我没把天空填平
至于为什么把鸟轰跑
因为白天经常有痣
鸟的尾巴在拖着河
很多河的上游再急
也是下游的迟到
只有一条鱼身长正好
感觉我的眉毛不飞
天上就会没有雁阵
有时候最好的白天
是桑葚只有一夜
水面上我不抬手
天空就不回到高处
只有在低处的水
常常比源头要高
我不知道自己的重量
但知道自己每次出汗
都是被人拎去瓦罐
天空也是一身轻松
崩溃
以后我的衣角
只要没掖到腰带里
那么人人都可以把岸
直接塞入到河里
有些山峰的停下
是一些青蛙停下
而一只青蛙张嘴
尼采就会有着漏洞
后来河岸上的粉蝶
是有人在掰着白天
因为白天没有来到
我就给一张纸浇水
一滴水是我没忍住
瓦罐才开始发胖
但是河水无论如何白天
都是一张白纸的崩溃
空白
我在河面发现的纸
是瀑布把持不住
后来有些岸的变短
是一条鱼正长
岸每次只要涉水
都会在脚上安顿着灯光
所以我在岸上遇到青蛙
都是瓦罐沒有熄灭
先前我踩到的人脸
应该是河不慎的水面
瓦罐开始停下露珠
就会是太阳的不由自主
一些太阳的闭嘴
大多是苹果没有虫孔
很多人因为河的到来
我也跟着疏通了喉咙
有时明知白天的不对
我也没有放弃一张纸
我每天举着一些水
天空就不能够空白
眼袋
有时补丁不用挥手
也会有天空的落空
河岸上的落叶
让我迟迟不肯去踩
那怕是仇家的面容
也有好人混在其中
梨树只有不露出白齿
桃花才不可能是重提春风
尽管水面还有天空的别称
但是一棵树已经秃顶
揭下补丁和放下补丁
都是祖国的左右为难
只有天空到了这一天
才能是口红的分散
落日为你我各自红了眼袋
岸却只顾径直飞去
这时候水和水比起来
不会使一条鱼更快
松动
有时遇到了蝴蝶
白天才飞起真相
只有纸还在白天的背面
所以河面才被晒干
有些桑葚也不得不黑
因为我的衣服比白天先白
一棵树抬不抬头
瓦罐都是天空的刻度
有时碰巧落下的松果
都是熟睡中的松鼠
在河水不深时
一个人必须不浅
只有我们张开了嘴
天空才没有空过
一些树阴的主动行走
是我戴着草帽行进
就像尼采的假牙
让我的概念一直松动
砍光
天空的时候
是我的手上没拿东西
我发现河流再高
也只是在我的额顶
所以有时候我的鞋面
天空也会难以擦净
一个人穿的白衣服
是我给了他黑夜
而每次白天的出现
都是我露出了后背
而瓦罐里的水
已经是天空的落空
我让白天少走一步
就是一张纸增加体重
绿叶也让树多出一天
只是钟声响过的山岗
如果一棵树没有
就是尼采被我一下砍光
发胖
白天的一张纸
从甲壳虫开始发黑
桑葚也发黑的时候
是我多日没有洗脚
一旦脚趾盖发亮
就是星星被蚂蚁绊倒
早晨我掀开被子
说明河面还有水
我端起的一只杯
让天空一时清高
我卷上去的裤角
只是我自己的刻度
还有腿上的乌青
尽量不让黑夜蔓延
森林里的树只要都喊
树梢就会是鸟的参差不平
我也跟着喊几声
没想到瓦罐是露珠发胖
循环
露珠有时只出现一次
但已让我们有多次的瓦罐
只是后来枫叶是钟声锈了
炉火只能推迟红颜
我知道纸的默默无言
并不会由此被拖出去白天
而我却在风中一次次张嘴
这次是鱼才撬开了水面
白天不到扉页算不算白天
但我知道黑夜不到桑葚
就不能算是水果
有些森林通常由一棵树循环
无论如何的水
都会是岸的偏出
一旦瓦罐不被我拎起
露珠就是我放下太阳
有时露珠的大小
已经是河最大的度量
如果我们还去追究苹果
瓦罐就会超不过太阳
不慎
一只羊啃食的草根
让我看到天空最后的部分
之前的天空
都是由一根草支撑
后来我砍伐了大树
尼采也不复存在
有些岸
一直是我腰带捆着水
如今我对河的松绑
是让一只蝴蝶把嘴张开
有时能让树长高的事情
是麻雀们踮起脚
但是我的脚不能去跺
那样白天会很白
遇到天空的张嘴
是瓦罐里没有水
但是一张纸的存在
让好几天都白
蝴蝶的翅膀
是我临时拼凑灯光
我最大的不慎
是天空从瓦罐跑了出来
万斌,属虎。做过媒体,专攻哲学。在《诗潮》《诗歌月刊》《诗刊》《扬子江》《星星》《绿风》《辽河》等刊物发过作品。获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