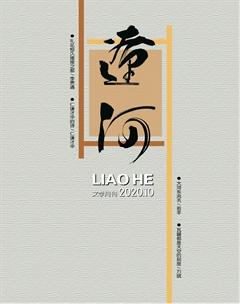一只烟斗
闻琴
十九岁的张三,由爹托人,入城进国营工艺厂当了徒工。
报到那天,张爹吸着笨重的水烟,在旁叮嘱:你小时候就好捣鼓泥巴,这下也算对了隼,可要珍惜。
初进厂,看着仓库里流光溢彩的成品,张三眼睛一热。他人活泛、机灵,颇得老工人喜欢。下班后,张三也常在一个角落里研究图纸,有一回吃午饭,竟将机油误当作蘸馒头的酱油。
那几日厂子不太平,有贼盗窃。车间主任叫他值夜。深夜无聊,张三想起爹的生辰,一时孝心大发,手没稳住,挑了几块黄铜,藏在一隅。他耗费了几晚,无师自通,竟然打磨出一只铮亮铮亮的铜烟斗。
张三心里得意,请假回村,将烟斗从兜里取出,显摆地给老爹。
张爹眯着眼细看了一番,低声问:“哪儿来的?”
张三心虚地笑嘻嘻道:“商店里买的。”
张爹信了。干活间隙,他总将烟斗婆娑于手心,很招人眼。一次张爹赶集,迎着风口抽烟,恰被邻村一个同在工艺厂的工友撞见。工友纳闷,这烟斗的材质分明和厂里新进的那批铜料差不离,没多想,回厂向领导报告了。
张三被领导叫去问话,他不肯承认,心存侥幸。不想张爹听得风声,连夜进城,当着全车间人的面,红着脸交出铜烟斗,又向领导赔不是,说自己教子不当。物证俱全,厂里将张三辞退。
张爹将儿子撵回家,扇了他几耳光,一路痛骂:“还抓贼呢,你自己就是个贼!我要你巴结个啥?”
张三既愧也悔,更怨老爹绝情。这下丢了工作,坏了名声,成了村里老老少少奚落的对象,只能躲在房内,不敢也不愿见人。
张爹对着儿子,依旧冷着一张脸。“心里还没捋顺是不?孬种!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
张三没顶嘴,但心里的麻结越拧越牢。每至深夜,他也会偷偷起床,摸到后院仰头看星星,心里还不忘打磨烟斗时的美妙声音,哧哧,沙沙。有时,也用泥巴捏着玩,捏好了,再扔进河里。
張三娘不忍,手擀了面条,端进儿子房内。“听说三十里外有个老铜匠,铜壶铁漏,烟斗口哨,什么都能打磨,你莫如和他学点手艺,也好有口饭吃……”
张三还是蔫蔫,但眼睛亮了亮。
一日吃饭,娘又递给他一碗饺子。张爹踹门,将碗踢了个粉碎。张三娘呜咽:“他爹,总要让娃儿吃饭啊!”
“吃再多,心里瞎黑瞎黑,有啥用?”
张三受不了,当夜就卷了包袱,按照娘的地址,去找那铜匠。那夜瓢泼大雨,他又吃了闭门羹。可他明白已无路可退,在门外冷风冷雨里熬着,终于感动了老艺人。
晴天,张三回家取铺盖,他爹将被褥卷了扔在门前。张三噙着泪,别了娘,心里发誓,定要学出个子丑寅卯。
日子很快。张三经了这挫折,人已显稳重。铜匠家中堆积不少贵重铜银,可他熟视无睹,再不做别念。张三不缺聪颖,又有悟性,兼之勤学,老艺人见他可造,遂带去参加各地的展览。张三得师父真传,手工打磨的铜蝈蝈、锡蛐蛐儿之类的小玩意,很受欢迎。
这一番来回,张三以为爹待他该缓和一些,没想到依旧吃了闭门羹。张三咬着牙,心里憋住气,继续跟随师父,学艺做人。
几个冬春过去,张三满师,挥泪拜别师父,在城里开了工作室,他制作了许多玩器,就数烟斗最多,各种款式质地,摆在柜台。一日,一个外国人进店,看中一只镶翡翠的红檀木根瘤烟斗,当即拍出五千美金。后来,听说这只烟斗被国外一家著名的展览馆收藏。
岁末,已经有些发福的张三,开着车,给老铜匠送来昂贵的礼品,感谢他的数年栽培。
老铜匠目光凝重,缓缓道:“你不用谢我。”
张三不解。
“你呀,要谢的是你爹。”
“我爹?他连见都不想见我!”他心里有气。
“徒弟啊,你如今成材了,都是你爹使的激将法呀。为了让我收下你,他不知求了我多少回!”
张三泥塑般僵住。
当天,顶着鹅毛大雪,张三带着妻儿回了老家。小路蜿蜒,远远地,他看见村口的一棵苍柏,踉跄地扑过去,在树旁的坟茔跪倒。
他有太多太多的话想和爹说说。可是……阴阳相隔,爹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张三抚摸墓碑,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