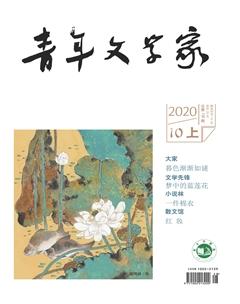母亲的针线活
侯保君
记忆中的母亲是终年闲不住的,每天蒙蒙亮她就起床下地。那时候没有钟表,更别说手机之类的东西,一颗墨蓝色里的启明星,就是母亲早上的时钟;中午,太阳偏歪向西倾斜,便是她歇晌的时刻……这是年轻母亲一惯的时间表。
其实母亲也有闲赋的时候。淡白带着寒气的太阳在天上慢腾腾地走着,迈过一片霜,踱过二片枯叶,趟过三片冻土,踩过四片冰凌,冬天总是望不出个头绪,于是母亲便在冬日难得的闲暇里,做她的针线活。
当然,做得最多的是纳鞋底,做布鞋。那時候没有电,更别说灯,唯一出亮光的,是那盏煤油灯。煤油是从煤里提炼的唯一点亮农村各家各户的液体,而且要凭票限量,只每月供应三四斤,点多了只能摸瞎。母亲只好把油灯做得最小,用父亲教学时写字用完的墨水瓶。
在寂静的冬夜里,如豆的煤油青灯,昏黄的光亮闪闪,托着长长的黑烟,映着母亲黑色的青丝,秀美的脸。此时,母亲正在昏暗的油灯下转着木拨锤打麻绳,这是纳鞋底的第一步。
麻绳是夏天晒干的麻秆,母亲第一天晚上烧些热水,用嘴吸后对着麻秆不断喷洒,之后用塑料纸裹住闷湿,等第二天晚上才解开,扒麻披,几个晚上下来,成捋的麻披让母亲带茧的手指剥下来,成捆成捆的,像她浓密的秀发。
接下来再用水喷洒湿透后,用拨锤转着打麻绳,打麻绳是个技术活儿,既要拎着下面快速旋转的木拨锤续上麻披,还要在快速中掌握速度,不至于续麻绳拧紧中断裂,屋外清冷的月光一缕缕洒进屋里,也被母亲续进飞快旋转的拨锤里……
麻绳一卷卷的被母亲做好,还要拨锤拉直。然后用一片片废布,熬玉米粥一块块粘起、压平、晒干。之后开始做鞋样,鞋帮。母亲手掌虽然满是茧子,但心灵手巧却是左邻右舍比不上的。她用粉笔画线条,布尺子量脚,这样做好的鞋不挤脚合适舒服。其实在从七十年代初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那个吃穿贫乏的年代,我们全家所有穿的,从单衣到棉服,从单鞋到棉鞋,都是母亲一线一针缝制的。
总记得在那些闲赋的冬天,在青灯下忙忙碌碌的母亲穿针引线的情景。她右手拿着厚厚的鞋底,左手拿着银闪闪的大头针,理一下头发,再向厚厚的鞋底穿插,那时候的母亲真的年轻美丽,红彤彤的油灯照着她圆亮的眼睛,青丝下丹红的脸庞,天蓝的粗布衣,丰腴的胸脯,像蓝天,覆盖着我童年所能仰望的天。往往我睡好几觉醒来还看见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身影,她正在做全家五六口人的保暖衣物,而且,一做就是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买得起衣服,母亲才停下手里的针线活。
2015年国庆节后,是母亲绝症在世的最后十八天。十月一日那天,因为医院放假,母亲没有住进医院。那天母亲说刚给我买的短袖衣拆商标的时候破了,她说什么要给我补上。母亲戴上老花镜,穿针引线,仔仔细细地缝起来。一会儿,母亲竟缝出一朵白色的菊花,在十月的秋天静静绽放,那是母亲人生最后一次做她的针线活。
母亲在我的衣领上缝完那朵白色的菊花,十八天后,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可这朵母亲亲手缝织的菊花,却在我的心里一生一世静静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