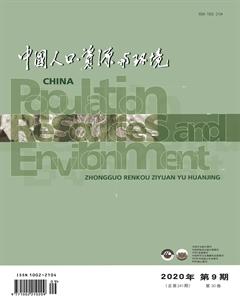环境问责与投诉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史丹 汪崇金 姚学辉



摘要 近年来,自上而下的环境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环境投诉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当前环境治理创新的显著特征。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改善了环境治理的客观绩效,还影响了公众环境满意度,提升了环境治理的主观绩效。文章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和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认知或判断,对其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众对环境问责的认知是否强化了其对环境投诉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发现:①公众认为环境问责越是有力,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认为环境投诉越是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②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还在其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前述中介效应在城乡居民间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满意度更直接依赖于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环境投诉有效性的判断未发挥中介作用,这或许与农村居民环境投诉经验不足有关。文章建议在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加强环境问责力度的同时,还应引进柔性治理技术,推进公众环境参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增强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改善环境治理主观绩效。文章还建议,中国在环境治理、反腐败斗争等领域探索出的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的经验,还可以推广至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 环境问责;环境投诉;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F06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20)09-0021-10DOI:10.12062/cpre.2020042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大气治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已经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之路。一方面广泛宣传“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不仅改变了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也影响着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强化信息公开,拓宽公共参与渠道,在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互动中层层压实环境保护责任。相继修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问责制等,国家监督越来越紧;各级环保监管部门也主动公开环境举报电话和邮箱、开展环境污染“随手拍”等活动,一些环保公益组织还利用新媒体搭建信息平台,方便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投诉举报监督,社会监督日趋活跃。群众的投诉举报等社会监督为国家监督提供了大量的“地方知识”,使得国家监督更为精准有力,进而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增加企业环境违规违法行为成本[1-2],倒逼地方政府和企业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治理绩效。可以说,中国环境治理特别是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功不可没。
中国环境治理实践中自然衍生出一个大命题,即自上而下的国家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及其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否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满意度?现有文献有以个案研究分析环境投诉及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3-4];有以环境统计部门定期公布的环境投诉、信访数据,评估公众环境投诉对地方政府环境投资[5]、环境监管强度[1]、环境治理绩效等的影响;还有基于微博论坛等上的文本内容,构建衡量公众對环境投诉或对环境关注程度的指标,解析它们对于城市环境治理的推动机制[6-7]。
本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如果公众相信政府领导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造成环境恶化将会被上级问责,那么他们对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更满意;如果公众相信政府对涉及环境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会及时给予有效的回应与落实,那么他们也会更加认可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研究还发现,公众越是相信政府领导对环境治理不力而被问责,则会更加相信社会监督渠道畅通有效,对政府环境治理的满意度也会更高。即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在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上述中介效应在城市居民中效果显著,而在农村居民中不显著。探讨人们对环境治理领域的国家监督、社会监督的主观认识如何影响其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环境治理满意度。本文以微观的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人们对环境问责、环境投诉等的个人主观感知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作用机理,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同时,本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认识,拓展了学界对公众参与、环境投诉的研究。
1 制度创新与研究假设
随着公共服务绩效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学术界目前已经形成了两种评估模式。一是重视成本效益分析等客观信息的客观绩效模式;二是强调满意度等公众主观判断的主观绩效模式[8-9]。忽视公众主观绩效,可能会丧失公共价值[9]。本文因此沿着第二种评估模式,基于中国环境治理创新实践,着重回答了人们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感知是如何影响其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满意度的。
1.1 环境问责与环境治理满意度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中国相继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法律法规和行动规划,特别是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环境保护督察条例》《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等党规党纪和部门规章,推动地方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据统计,刚结束的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就问责了1 035人,其中厅级干部218人,处级干部571人。环境问责已成为确保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
学术界常常将环境规制当作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外在动力,认为环境问责有利于改善环境治理客观绩效,但对主观绩效的研究尚欠缺。吴建南等[10]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政府环境考核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认为自上而下的环境考核与监管具有良好的治理效果。Wang和Di[2]基于地区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对中国85个乡镇的研究,发现来自上级政府和辖区公众的压力将促使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并提供更多的环境服务。在主观绩效方面,我们乐见陈卫东和杨若愚[11]利用CGSS(2015)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监管和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环保问责力度还是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都对环境治理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参与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性也会显著地促进环境治理满意度的提升,且后者的显著性高于前者。从满意度模型来看,本文认为这背后的逻辑或许与政府形象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有关。如果政府在治理环境问题方面的行为失范,不能得到及时纠正,显然难以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12]。换言之,如果公众相信在环境治理中失职不力的地方官员会被问责,则更加认可他们的环境治理工作,满意度也会越高。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增加政府形象方面的变量给予佐证。
假设H1:公众越是认为环境问责有力,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
1.2 环境投诉与环境治理满意度
在国家监督这一环保“紧箍咒”越来越紧的同时,来自公众的社会监督也日趋活跃。自下而上的环境投诉为自上而下的环境问责提供了必要的“地方知识”,在监督上的“上下齐动”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新特征。据统计,2018年全国“12369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共接到公众举报710 117件,同比增长14.7%,其中电话举报365 361件,微信举报250 083件,网上举报80 771件[13]。广大群众利用通畅有效的社会监督渠道,为打击环境违规违法行为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使得国家监督精准发力、有的放矢。
已有文献对环境投诉的环境治理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肯定了环境投诉对于推动地区环境治理客观绩效的积极作用。例如Dasgupta等[14]、Warwick等[3]等指出,公众环境投诉、信访能为监管者提供有效信息并降低监管成本,上级政府能够利用民众提供的信息,通过问责机制激励下级政府更好地为当地公众服务。Lu和Tsai[5]发现政府官员担心公众对环境的投诉影响社会稳定,因而增加环境治理支出,改善环境质量。Wang 和Wheeler[1]通过对中国3 000家企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在公众环境投诉越多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排污费征收强度越高。郑思齐等[6]利用中国2004—2009年86个城市的数据,证实了较高的公众环保诉求会推动地方政府通过环境治理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来改善地区环境,并促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提前到来。杨瑞龙等[15]的研究发现,公众环保诉求的增强能显著改善地区环境质量。当然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如此乐观。比如李永友和沈坤荣[17]发现,民众环境投诉并未对更严格的环保执法起到推动作用。
与上述研究视角不同的是,本文尝试分析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是如何影响环境治理工作满意度的。从满意度模型来看,其中的作用机制也离不开信任等主观认识。例如学者们常常用信任、规范、网络等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基于这一基本框架,万建香和梅国平[17]在探究社会资本是否对环境保护有促进作用时,使用群众环境来信来访数衡量公众的环保参与度,并发现公众环保参与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共赢”,从而构建了环境投诉对环境保护的作用路径。另外,一些学者强调公众参与不仅是实现民主和实施“善治”的传统方式,也是环境治理工具的重要补充,与其他政策性工具相得益彰[18]。具体而言,公众参与环境事务还为当事各方提供了一个渠道来表达诉求、交流信息、讨论环境后果,进而减轻社会误解以及误解所带来的损失[19]。这里强调的“善治”或“减轻误解”,很大程度上也是从社会心理的视角定性分析公众参与的深层价值。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的基本假设。
假设H2:公众越是认为环境投诉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
1.3 环境问责、环境投诉与环境治理满意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自然衍生出一个新的命题,即那些认为环境问责力度越大的公众,是不是更相信环境投诉通畅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是不是因此会更高?在中介效应模型语境下,该命题即为公众对环境投诉通畅有效的判断在对环境问责的认知与环境满意度之间具有多大程度的中介效应。学术界尚未有针对性的研究,但也论及此话题。例如陈文斌和王晶[20]指出,政府在环境方面的“自我管制”,能够引导公众的“生态美德”,鼓励社会参与环境协同治理。加强监督以规范权力行使有助于提高行政相对人的满意度,几乎已被当作常识,但王福涛等[21]指出,若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缺乏实质性回应,反而会引起行政相对人更大的不满。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的基本假设,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给予验证。
假设H3a:公众越是认为环境问责有力,越相信环境投诉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
另外,值得关注的两个城乡有别现象。一是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不仅导致城市和农村在经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差异拉大,在生态建设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出现了“城市环境好转,农村环境恶化”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央政府将环境指标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后,重污染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22]。二是就环境污染问题,城乡居民的态度或行为也是不一样的。聂伟[23]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市居民对于环境关心程度远高于农村居民,并且农村居民大多只是关注环境的直接效果,而城市居民掌握更多环境知识,更愿意采取行动解决环境问题。马戎和郭建如[24]的调查还显示,城市受访者会认为自身在环保问题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向政府反映身边环境问题的比例会更高,而农村受访者的比例则偏低。Zhang等[25]还指出,由于农村地区特别是中国西部偏远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等都很低,他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与其他地区居民的差异明显。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的基本假设。
假设H3b: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和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对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始于2003年。该调查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0 000多户家庭,不仅包括诸多个人特征的数据,还包括诸如法律、环保、节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调查数据,现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本文使用2015年CGSS调查数据(简称CGSS(2015))。受访者年龄分布在18~95岁之间。其中60岁以下占比72.46%,60岁以上老年受访者占比27.55%。从受教育水平来看,17.14%的受访者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82.86%的受访者接受过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从居住地来看,受访人群在城市和农村区域的分布较均匀,城市有1 690个样本,农村有1 139个样本。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2.2 变量选取
本文考察的核心变量是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以及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其中,环境治理满意度(Satisfaction)作为被解释变量,该变量对应于CGSS(2015)问题B158,即“您对政府环境治理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对应有“非常满意”“满意”“非常不满意”等五个选支。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简称“环境投诉”,记为“Complaint”)是本文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对应CGSS(2015)问题F9,即“如果在您家附近有一家企业违反规定排放废气或污水,严重损害居民健康。如果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件事,政府会如何处理?”对应有“政府根本就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政府会立即派人来调查处理”等四个选支;公众对政府环境问责力度的认知(简称“环境问责”,记为“Accountability”)是本文另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对应CGSS(2015)问题F253。即“政府领导片面追求产值,对企业排污疏于监管,造成环境恶化是否会被问责?”有“很少”“通常”“总是”等五个选支。
本文还结合顾客满意度模型,并借鉴吴建南等[10]、陈卫东和杨若愚[11]、Zhang等[25]的做法,挑选了一些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以下两类:一是包括受访者的个体特质,如性别、年龄、学历、社会地位、所在区域、个人收入、政治面貌以及健康状况等。二是包括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如受访者所在省份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含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剔除CGSS(2015)中“无法回答”“拒绝回答”等无效样本,最后获得有效样本2 829个。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为更清晰地了解核心变量的关系,本文进行了更细致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按照环境治理满意度来分组,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非常满意”和“满意”的被访者占总样本量的47.33%,而认为“一般”以及“不滿意”的占52.67%。按照政府对环境问题举报的处理情况来分组,认为政府会立即或很快派人来调查处理的占17.28%,相信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但会拖延的占73.39%,而认为政府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的占9.33%。按照政府对环境违法违纪行为的问责处罚来划分,认为政府环境治理失职不力“基本上”或者“通常”会被处罚的占51.01%,认为“很少”或者“有时”会被处罚的占48.99%。
2.3 模型构建
根据前述研究假设,本文首先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和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如何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其中,Xij代表个体控制变量的集合,Dj表示地区污染变量的集合,εi为随机误差项。
同时,为考察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是不是作为中介变量,使得对政府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进而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本文借鉴Baron和Kenny[26]的研究,在模型(2)的基础上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β1表示公众就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总效应;γ1表示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这一中介变量的效应;δ1表示环境投诉中介变量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效应;δ2表示环境问责对公众环境满意度的效应。中介效应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与上述模型(1)和(2)的控制变量相同,εi为随机误差项。
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本文采用逐步检验法进行检验。按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7]提出的检验流程,依次检验系数β1、γ1、δ1及δ2的显著性。当γ1、δ1的系数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时,需要构建Sobel统计量进行检验。本研究所涉及变量为类别变量,适用Ordered-Logit回归,因此本文借鉴Lacobucci[28]的研究,构建Zmediation 统计量:
若Zmediation>1.96 ,则证明中介效应存在。
简而言之,本文通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7]提出的Accountability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环境恶化,是否会被问责总是通常基本上有时很少1145777528795074.0320.4026.5831.0717.92
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和Lacobucci[28]检验多分类变量中介效应的方法,结合李莹和吕光明[29]的研究,使用如下检验流程:①检验系数β1,验证主效应是否存在。若不显著,则停止检验,说明不存在中介效应;若显著,则进入下一步。②检验系数γ1、δ1的显著性。第一种情况是,两者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使用Lacobucci法进行检验,若不显著,则中介效应不存在;若显著,则进入下一步,考察系数δ2的显著性。第二种情况是,γ1、δ1均显著,也将进入下一步。③若δ2显著,则根据γ1、δ1、δ2的正负号,判断是部分中介效应抑或遮掩效应;若δ2不显著,判断为完全中介效应。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根据研究设计并使用Stata14软件,首先依次分析了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和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是如何影响环境治理满意的,其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公众对于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会不会通过影响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进而间接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
3.1 基准回归
首先基于模型(1)、(2)进行基准回归。由于本文研究核心变量为离散的有序变量,变量取值具有固定的顺序和含义,因此相较OLS估计方法,Ordered-Logit回归更适用。基准回归的结果见表3。
第(1)列和第(4)列只是分别检验了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和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其他各列分别又加入了个体特征变量和地区环境污染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Complaint的系数一直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公众越是认为政府会及时调查处理环境投诉,环境治理满意度就会越高。变量Accountability的系数一直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公众越是认为地方领导环境失职将被问责,环境治理满意度也会越高。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来看,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年龄、教育水平以及所在区域的系数始终较为显著。年龄与环境治理满意度呈正相关,表明年龄越大的居民环境满意度越高,这可能是由于年龄大的居民相比年龄小的居民拥有更宽容的心态;教育水平与环境满意度呈负相关,表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对环境更加敏感,环境满意度也越低;受访者所在区域与环境满意度呈负相关,城区往往比农村区域的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因而生活在城市中的受访者也往往更加关心环境的质量,环境治理满意度也会越低。
3.2 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会不会改善公众对环境投诉的判断,进而提升环境治理满意度,按照改进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对模型(2)(3)(4)进行回归,检验系数β1、γ1、δ1及δ2的显著性,考察中介变量效应。回归结果详见表4。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主要变量系数β1=0.132、γ1=0.101、δ1=0.399及δ2=0.113,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按照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可以认为Accountability这一变量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可以通过影响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进而影响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换言之,政府对环境方面违纪违法行为的问责处理,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众对于政府治理行为的认同感,公众会相信参与监督与反馈的途径有效,从而提升了环境治理满意度。
3.3 城乡异质性分析
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城市与乡村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较大差异,使得我们不能对环境满意度的考察一概而论。因而,有必要对城市和乡村两组样本进行分别检验。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与中介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受访者所处区域对于环境治理满意度影响较显著。类似的,基于中介检验模型考察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样本中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以及是否存在差异,详见表5。
从表5对中介模型的分组样本回归来看,在城市组中控制个体特征变量和地区环境污染变量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公众对政府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对举报渠道是否有效的判断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然而,在农村组别中,模型(3)的变量系数不再显著(详见表5列(5)),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当γ1、δ1的系數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时,需要构建Z值统计量。经检验,Zmediation = 0.566 3 < 1.96,即认为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在农村组中没有发挥中介效应。因而公众对政府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判断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是直接的,未通过中介变量发挥作用。
正如Zhang等[25]指出,由于汽车尾气排放和现代工业的集聚,使得城市居民可能更为关注环境污染。类似地,对上述差异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城市和农村在公众参与的途径、方式的便捷度和多样性上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公众越认为环境问题的监督渠道畅通有效,越是能提升他们的环境治理满意度,而农村中监督互动的渠道较为缺乏,公众环境满意度的提升更多依赖于政府直接的环境问责。
3.4 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本研究的可靠性和可信性,通过两种方法进行检验:①首先替换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有研究者认为,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与Ordered-Logit估计方法没有优劣之分,而且OLS解释能力更强,因而本文采用OLS回归方法对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再次检验。②将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判断这一变量替换为CGSS(2015)调查问卷中的问题F9,即“违反党规党纪的问题是否都受到了严肃处理?”(记为Supervise),该变量可认为包含了政府环境监管问责。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和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更换变量还是更换回归方法,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是稳健的,主要变量的系数尽管大小存在差异,但是符号始终一致,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 结论与启示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秉承“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理念,努力打造形成有为政府、成熟社会和现代公民共同治理的格局[30]。在此社会治理框架下,中国未来环境治理模式将包含:政府严格的环境规制、企业绿色的生产发展和公众广泛的环境参与。当前,政府已经行动、企业已在路上,公众参与的自觉性也有所提高。本文紧扣中国环境治理的实践,从环境治理的主观绩效入手,实证检验了当前环境治理创新对公众环境满意度的影响,不仅拓展了人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现实意义的认识,而且为今后推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提供了理论支持。简而言之,公众环境满意度是一种心理活动,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不仅要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改进环境治理客观绩效,同时也要根据公众心理活动特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重视交流互动、信息公开等柔性技术的推广运用,增进公众环境满意度,提升环境治理主观绩效。
第一,进一步通畅公共参与渠道。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公众参与环境事务同环境监测、环保督查、环保问责等其他政策性工具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是环境治理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环境治理、反腐败斗争还是其他领域的治理创新,引入社会监督、借力地方知识,是国家监督能够有的放矢的保障。中国环境治理已从大气污染防治,到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纵深领域推进,也是从显性污染治理向隐性污染治理的迈进,国家监督更是需要社会监督为其提供地方知识。因此需要进一步通畅公共参与渠道,激发和利用人们对于环境破坏行为的举报揭发的政治美德。
第二,进一步加大环境问责力度。本文研究显示,公众对国家监督强度的认知以及对环境管理部门形象的认知,都会影响到他们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满意度。这一判断与公共参与相关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但本文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一的被访对象认为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环境恶化“有时”会被问责,近五分之一的被访对象甚至认为“很少”会被问责。本文就城乡异质性的中介效应分析还显示,农村组的公众对政府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判断未能影响他们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进而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简言之,尽管中国国家监督这一环保“紧箍咒”越来越紧,但尚未获得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同。中国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繁重,很难在短时期内释放长期形成的环境污染压力,但进一步加强环境问责力度,在公众中形成国家监督恰当得力、公务人员廉洁勤政,这都有助于赢得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等工作的支持和认可。本文的中介效应分析还显示,政府对自身加压,还可以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集聚更多环境治理力量。
第三,進一步推广环境治理经验。环境治理只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在环境治理领域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同样可以推及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从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从本质上讲都属于公共品的范畴,由于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征,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政府责无旁贷地成为这些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但从新近的强互惠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人类形成了关心集体、关注他人的亲社会特质,在环境保护领域则表现为环保社会人。政府在提供各类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加强与社会的互动,树立良好政府形象,赢得公众广泛信任,从而更充分调动公众的这种亲社会特质,引导全社会参与到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共建共管进程中来,最终形成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共享的良好局面。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
[1]WANG H, WHEELER D.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endogenous enforcement in Chinas pollution levy system[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5,49(1):174-196.
[2]WANG H, DI W. The determinants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townships[M]. The World Bank, 2002.
[3]WARWICK M, ORTOLANO L. Benefits and costs of Shanghais environmental citizen complaints system[J]. China information, 2007,21(2):237-268.
[4]LI Y, KOPPENJAN J, VERWEIJ S. Governing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in China: under what conditions do local governments compromis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6,94(3):806-822.
[5]LU J, TSAI P. Signal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environmental petitions in China[J].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2017,18(4):391-418.
[6]郑思齐, 万广华, 孙伟增, 等. 公众诉求与城市环境治理[J]. 管理世界, 2013(6):72-84.
[7]KAY S, ZHAO B, SUI D. Can social media clear the air? a case study of the air pollution problem in Chinese cities[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15,67(3):351-363.
[8]倪星, 李佳源. 政府绩效的公众主观评价模式:有效,抑或无效?——关于公众主观评价效度争议的述评[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24(4):108-116.
[9]范柏乃, 金洁. 公共服务供给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机理——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与公众参与的调节效应[J]. 管理世界, 2016(10):50-61.
[10]吴建南, 徐萌萌, 马艺源. 环保考核、公众参与和治理效果:来自31个省级行政区的证据[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9):75-81.
[11]陈卫东, 杨若愚. 政府监管、公众参与和环境治理满意度——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J]. 软科学, 2018,32(11):49-53.
[12]刘细良, 刘秀秀. 基于政府公信力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对策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13(S1):153-158.
[13]肖琪. 国家战略不容一省一地自作主张[N/OL].中国环境报. 2019-08-23. http://www.qstheory.cn/zoology/2019-08/23/c_1124911181.htm.
[14]DASGUPTA S, WHEELER D. Citizen complaints as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evidence from China[M]. The World Bank, 1997.
[15]杨瑞龙, 章泉, 周业安. 财政分权, 公众偏好和环境污染——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2007.
[16]李永友, 沈坤荣. 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08(7):7-17.
[17]万建香, 梅国平. 社会资本可否激励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29(7):61-75.
[18]MORGAN R K.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he state of the art[J]. Impact assessment & project appraisal, 2012,30(1):5-14.
[19]VOSS H, BUCKLEY P J, CROSS A R. The impact of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firms[J].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0, 18(3):25-48.
[20]陳文斌, 王晶. 多元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公众有效互动研究[J]. 理论探讨, 2018(5):154-160.
[21]王福涛, 黄怡茵, 潘振赛. 行政许可监督与服务满意度关系研究——基于广东省J市行政许可绩效评价[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8):95-101.
[22]杨健燕. 公众诉求提升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制度改进[J]. 中州学刊, 2015(10):83-87.
[23]聂伟. 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与分解[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4(1):62-70.
[24]马戎, 郭建如. 中国居民在环境意识与环保态度方面的城乡差异[J]. 社会科学战线, 2000(1):201-210.
[25]ZHANG J, CHENG M, WEI X, et al. Internet use and the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212:1025-1035.
[26]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51(6):1173.
[27]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22(5):731-745.
[28]LACOBUCCI D. Mediation analysis and categorical variables: the final frontier[J].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12,22(4):582-594.
[29]李莹, 吕光明. 收入公平感、流动性预期与再分配偏好——来自CGSS 2013的经验证据[J]. 财贸经济, 2019,40(4):35-49.
[30]王岩, 魏崇辉. 协商治理的中国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7):2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