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凹访谈:榆柳夹桃花,日光漏叶莹
韩寒
作家贾平凹新作《暂坐》于2020年5月在《当代》杂志上发表。文章讲述了一个关于西安城里十二个女子的故事。如作家所言,新作“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正如一段古文所写:“墙东一隙地,可二亩许,诛茅夷险,缭以垣,垣内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这是她们的生存状态,亦是精神状态”“而菟丝女萝蔓延横生,日光漏叶莹如琉璃,叙述以气流布,凝聚为精则是结构之处”。作家认为,这一次的写作仍是日子的泼烦琐碎,只是藉那众姊妹之口,写众生之相,“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亦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
智与慧
问:周汝昌先生曾说,古代作品,下焉者把妇女只当作一种作践的对象,上焉者把妇女也不过看成“高级观赏品”,悦一己之心目,供大家之谈资而已,都没有真正把她们当“人”来对待,更不要说体贴、慰藉、同情、痛惜……自有雪芹《红楼梦》之书,妇女才以真正的活着的人的体貌心灵,来出现于人间世界。
您此前的作品或聚焦社会政治、城乡衍变,或寻根传统文化,为何这次,“没有大的视野”(据《暂坐》后记自谦语),以一群女子的日常生活作为主要书写对象?
答:初学写作时大概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越是写作,越明白了自己的无知和渺小。越写越有了一种敬畏,敬畏大自然,敬畏社会,敬畏文字,作品常常是在这种敬畏中完成的,只想把自己体悟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不是仅仅用一个传奇故事或一些华丽句子取悦读者。小说并不是仅仅写写故事,也不是只有批判的元素,而应有生活的智和慧。
而且,到了这般年纪,写作可以是随心所欲的,写自己长久以来想写又没有写的东西,像一条水流着,流到哪儿是哪儿,因越往下流的地势不同,流量不同,呈现的状态、颜色、声响越不同而已。到了这把年纪,对于名利已无早年的冲动。写作《暂坐》的动意,我在后记里已经说了,因为书中那个茶庄,十多年来我差不多每日都去喝茶闲聊,所写庄主和她的一帮朋友,又都是我的朋友,太熟悉了。只要某一日有了想写她们的念头,提笔去写就是了。
问:您认为,您塑造了一个怎样的女子群像?她们与传统观念中的女子,有哪些不一样?
答:《暂坐》里塑造了一群个性独特的女子,经济独立,自由时尚,潇洒率性,有文艺范儿,却多为未婚或离婚的单身。她们身上有着这个时代特有的东西。
问:《暂坐》以俄罗斯女子伊娃的视角为线索,进入了“西京十玉”的世界,后遭际从乡下来的女子辛起,成为“西京十二玉”。“西京十二玉”与“金陵十二钗”,是否有耦合之处?如夏自花与秦可卿的早夭,冯迎与元春的意外之亡,曹雪芹通过贾府操办丧事来写王熙凤,您通过“十玉”操办丧事写海若。
答:也许有耦合,这十几个女子的命运都不好,像十二钗。但是她们与十二钗毕竟不同,也努力摆脱命运的摆布,在起名的时候也说过,“咱姊妹么,我觉得叫十钗不好,这是套用金陵十二钗,本来就俗了,何况那十二钗还都命不好。”她们活力充满,享受时尚,不愿羁绊,永远自我。简直是,你有多高的山,她们就有多深的沟,你有云,云中有多少鸟,她们就有水,水中就有多少鱼。她们是一个新世界。
问:《暂坐》与红楼梦,是否有耦合之处?如都是盛极而衰。再如贾府衰败乃是因为政治巨变,茶庄遭难是因为查肃腐败。您怎样看待这种耦合?
答:毕竟是不同的两部作品,如果有耦合,也是时代与社会有共同的规律。现实中的好多事情是做了不说,说了不做的,小说也可能有不要说破的地方。《暂坐》里大量的笔墨是在写雾霾和市井的,那就是我要渲染和弥漫的,是一种象征。
问:《暂坐》里的“羿光”,体贴、慰藉、同情、痛惜茶庄的女子,身上有宝玉的影子。同时他又是一位作家、书法家,写字画画,身上也有您自身的影子。他不时通过诗文和自己的观察,表现一些哲思,如“天地一遽庐,生死尤旦挽”“此身非我有,易晞等朝露”,等等。您如何看待和安排“羿光”這一角色?
答:羿光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身上有复杂的矛盾。比方他要经常面对自我与物欲的选择,面对不同的女性和情感,他身上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这个人物是丰富复杂的,他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问:羿光与海若之间的关系,体现现代男女之间的关系,有了怎样的变化?
答:他们是现代男女关系中的一个类型,不是情人,却充满了感情,说明时代在进步,两人是真正平等的精神上的交往和沟通。
命与运
问:茶庄女子在盛宴之后也逐渐凋零四散,正如红楼梦里“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您为何会为《暂作》安排一个不太圆满的结局?您意在通过《暂坐》达成怎样的文学理想?
答:每一个作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在写作里并没有依附其他作品在写。我总有一种印象,在这个年代,没有大的视野,没有现代主义的意识,小说已难以写下去。这道理每个作家都懂,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在让自己由土变洋,变得更现实主义。可越是了解现实主义就越了解超现实主义,越是了解超现实主义也越是了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的长河,在这条长河上有上游中游下游,以及湾、滩、潭、峡谷和渡口。超现实主义是生活迷茫、怀疑、叛逆、挣脱的文学表现,这种迷茫、怀疑、叛逆、挣脱是身处时代的社会的环境的原因,更是生命青春阶段的原因。处理这些说话,总是平稳、笨着、憨着、涩着,拿捏得住,我觉得更显得肯定和有力量,也更能保持它长久的味道。尽力地去汲取一切超现实主义的元素,丰富自己,来从事适合国情和自况的写作。视野决定器量,器量大了怎么着都从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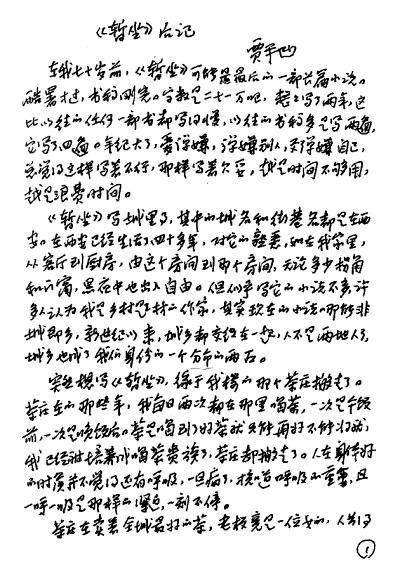
问:《暂坐》的人物,似可以分成几层——前景是“十玉”、羿光、伊娃和辛起;中景是小唐、小甄、高文来、夏自花的妈妈和儿子、范伯生等人;背景是市委、纪委、汗蒸的领导、城墙上唱秦腔的伶人、停车场收费的老头。《暂坐》后记里说,“众生之相即是文学”。这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了一幅怎样的众生相?
答:在《暂坐》里,以一个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正如一段古文所写:“墙东一隙地,可二亩许,诛茅夷险,缭以垣,垣内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这是她们的生存状态,亦是精神状态。
在小说中,社会上的种种事情,连同笼罩城市的雾霾,以及所有的市井现象,都成为那些女子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背景。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众生相,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人也不是,就像生活在沼泽地里一边扑腾着,一边沉沦着。所有人和事,都是复杂、纠缠而丰富的。
善与哲
问:文章有义理,是埋藏在其中的“善”与“哲”。不难看出,通過希立水和海若对辛起为人处世的劝诫,通过应丽后让章怀停止追讨债务的诉求,您表达了对“善”的追求。通过羿光多次对古文、对当下不经意的讲述,您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您认为,《暂坐》想传递的理念是什么?暗含着怎样的哲思?
答:《暂坐》的写作,就是听茶馆里的女人在说自己的事,说别人的事,说社会上的事,说别人在说她们的事,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在这些叙说中,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地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也明白了有众生始有宇宙,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亦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
人生就是一场“暂坐”,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暂坐”。小说要表现的是社会,是人活着的意义,这群女子又是如何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她们在经济独立后,怎样追求自在、潇洒、时尚和文艺范儿,又怎样的艰辛、迷惘、无奈甚至堕落。也是每一个人的状态。
问:您在后记里陈述,以往观念认为您是一个乡土作家。这次《暂坐》的背景设置在了西安城,并通过“汉唐的苍蝇”“墙上的秦腔”“夜里的曲池”“照片墙上的西京百年”,通过高档小区、职工家属院、城中村,通过羊肉泡馍、甑糕……将西安城的“声”与“色”描绘了出来。您希望您笔下的西安城,体现的是怎样的精神与气质?西安作为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说,不了解农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我大多数作品都是写乡土的,写近百年中国的历史演变。许多人认为,我是乡村题材的作家,其实现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新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分布的两面。西安既古老又现代,和这个时代的中国其他城市有共同的东西,但是因为它历史深厚,又形成自己不同的习惯和气息。
我熟悉西安,所以将这里作为故事的发生点。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对它的熟悉,如在我家里,从客厅到厨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写它的小说不多,写西安,就是写我熟悉的城。
(文章原载于《光明日报》2020年7月25日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