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创新尺度 探索实用之路
段盼盼 王辉
2019年中秋節晚上,田野正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突然电话铃声响起,一个好消息从电话那头传来:他的科研成果被材料学领域顶级期刊Nature Materials接收。这个消息犹如一个从天而降的节日礼物,让田野感到有些激动。这是他从事DNA纳米技术研究以来第二次如此高兴,第一次是他做出第一个成果的那天。
从提出想法到做出成果,再到文章发表,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年。在这期间,这项研究一直被认为是很难完成的工作,一路走来有着外人所不能理解的辛苦和辛酸,但是这依旧没有阻挡他探索的脚步。也许在外人看来,田野的行为过于执拗,不达目的不罢休,但是也正是这种“执拗”的精神让他取得了科研上的“小胜利”。如今,立足于前期取得的成绩,田野正向着DNA纳米技术研究更深、更广的领域前进。
聚焦DNA纳米技术发展前沿
DNA纳米技术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主要利用DNA(脱氧核糖核酸)尺寸为纳米级别、刚性结构、编码性强的特点来构造各种纳米结构,可以应用于生物医学、化学、材料等领域。为了更清楚地解释DNA纳米技术这门研究,田野从它的起源开始讲起。
D N A纳米技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它的创始人是纽约大学的教授Ned Seeman。1982年,Ned Seeman还是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他当时主要从事蛋白质结晶领域的研究工作。所谓蛋白质结晶和解析技术就是通过X射线衍射法研究蛋白质分子结构的技术,但是很多蛋白质结构都无法结晶,所以都无法用这种技术进行解析。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Ned Seeman。
有一天,Ned Seeman正在美国纽约州首府的一家酒吧里喝酒,突然,一幅荷兰艺术大师M.C.Escher的木刻雕版画映入了他的眼帘。这幅画描绘了一群高高跃出水面的飞鱼,所有鱼的头尾、左右、上下姿势全都一样。由此,Ned Seeman敏锐地想到这些飞鱼其实就是一个个人工构建的六分支DNA分子,可以将这些六分支DNA分子规则地排布成一个三维的中央镂空的立方晶格。如果可以将蛋白质分子插入到这种立方晶格,就能够让这些蛋白质分子全都按照一个方向排列整齐形成晶体。换句话说,Ned Seeman发现了一种能够解析任何蛋白质结构的工具。
这一想法提出以后,很多人都认为Ned Seeman是异想天开。此后的20多年里,Ned Seeman和他的学生们一直在这一方向深挖。终于,2009年,Ned Seeman与合作者将许多个三角形DNA结构拼装成了一个硬质的三维水晶晶格,其间嵌有菱形的空隙。不过,由于中间的空隙太小,蛋白质又较大,所以蛋白质不易“塞”进三维晶格中。而田野的一部分研究工作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致力于将DNA折纸术引入其中以实现大型DNA结构的搭建。
DNA折纸术是当下科学研究的热点,它的诞生为制备大型D N A结构(10?100nm)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田野介绍说:“通俗点讲,DNA折纸术就是将细菌内部的DNA取出来然后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其实是想对一些纳米尺度颗粒排列的形状进行精准控制。”
2019年,田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DNA晶体结构的纳米材料三维有序组装体”。在这之前,他已经率领团队利用DNA折纸术设计出了一种具有三维空间结构的正八面体DNA基底来构建三维的纳米粒子团簇,纳米粒子排放的位点以及纳米粒子的种类具有很高的自由选择性。团队还利用冷冻电镜-单粒子分析技术对三维DNA框架进行重构,发现利用DNA折纸术设计的DNA三维结构具有较强的刚性,能够在溶液中保持其三维形貌,这在软物质材料组装中是很少见的,也因此激发了田野对项目中构建DNA晶体结构的思考。
田野还发现,基于DNA三维框架结构上的功能化位点来进一步组装的三维纳米粒子团簇中纳米粒子的空间位置具有很高的精准性,通过三维重构的方法能得到具有很高分辨率的三维团簇结构。这些结果都证明,这些组装在DNA框架模板上的纳米粒子在溶液中的三维空间位置是比较固定的,这为项目中设计不同结构的DNA框架以及进一步组装纳米材料提供了充分的研究积累。
更进一步的,团队利用DNA折纸术设计了DNA多面体框架结构组装纳米粒子,形成大面积的有序三维超晶格体系,并证明了不同的多面体结构能够根据其几何构型控制生成的三维超晶格的种类。这是领域内第一次通过“设计”的主动模式来制备不同三维结构的纳米超晶格体系。该成果对于项目中研究构建DNA晶体结构、DNA/无机纳米材料、DNA/蛋白质等多元有序复杂体系的构建有着指导性的作用。此外,该成果还能够为深入理解和研究具有特殊形状的组装体在溶液中的组装行为、团聚行为以及结晶行为的机理提供一种新的手段。
在“基于DNA晶体结构的纳米材料三维有序组装体”项目研究中,田野团队拟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利用DNA折纸术设计体积更大、“客体”分子携带性更强的DNA结构,研究如何利用这些DNA结构之间的组装制备出DNA晶体结构,从而抛开金属纳米粒子的引导连接作用,避免高密度的金属纳米颗粒遮盖DNA结构信息的问题。根据Ned Seeman团队之前通过简单三角形结构制备DNA单晶的经验,项目团队将利用 DNA折纸术选取和设计结构相对比较刚性的多面体框架结构作为DNA晶体结构的组装单元。
除了该项目,田野也承担和参与了其他一些项目研究来拓展DNA纳米技术的应用,尤其在生物医药和精准医疗方面,DNA纳米技术的应用有着很大的需求。他说道:“化学走向精准化是近年提出的重要理念。要说精准化的话,DNA折纸术是很好的一门技术。我们也希望未来在医疗领域,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艰难中坚持自己的方向
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读硕士时,田野师从刘鸣华研究员,主要从事超分子组装研究。之后,他前往美国继续深造,跟随Oleg Gang教授学习纳米颗粒的自组装技术。2013年,在机缘巧合之下,田野认识了哈佛大学的William Shih教授和正在博士后时期的柯勇刚教授,他跟随两位老师学习了DNA折纸术。
田野坦言:“最初学习D N A折纸术的目的是,想将这门技术与无机纳米颗粒相结合,做一些有序的结构搭建研究。”不过,在学习过程中,田野对纳米粒子的精准装配方面的研究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随着DNA纳米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通过DNA的引导实现了纳米粒子的三维有序组装,然而在结构更为任意、尺寸更小的团簇装配方面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尽管通过一定的化学修饰手段可以获得表面结合能力各向异性的“补丁”粒子,但受限于过小的粒径,简单的化学修饰往往难以在纳米粒子表面所需的特定位置安插“补丁”位点,难以控制的“补丁”数目和张角,也为随后的多级次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针对这些问题,田野及其团队在配位化合物结合模式的启发下,开发了一种基于DNA折纸框架的纳米粒子“补丁”编码策略,有助于实现胶体纳米粒子团簇的多级次、多尺度精准装配。借助DNA折纸框架外壳赋予纳米粒子的不同“价态”,即利用核酸框架为纳米粒子安插“补丁”,模拟配位化合物的结合模式进一步操纵纳米粒子在空间中完成精准定位。
在这项工作当中,田野团队开发了一种由DNA自组装形成的八面体折纸框架。这种利用DNA自身折叠而成的几何体框架结构在设计上具有独特的可编辑性,八面体的顶点和内腔都可以通过特定的设计延伸出具有连接能力的DNA链段,只需同样使用DNA链段对胶体纳米粒子进行简单的化学修饰,就可以轻松地将纳米粒子装载到八面体框架当中。
团队还借鉴配位化合物的形成方式,通过进一步调控八面体外壳顶点延伸出的DNA单链的数目和空间位置,对内部的纳米粒子完成了表面“价态”的编码。这种编码机制可以方便地对纳米粒子进行“价键”个数和位置的更改,即可以对表面的“补丁”位置和数目进行调整,且八面体外壳顶点之间的互相连接可以操纵这种经过特殊编译的纳米粒子最终实现特定图案和结构的精准装配。
最初田野提出这些想法时,周围的人几乎都不支持这项研究工作。很多人劝告他,这项工作的研究难度太大,是做不出来的,不要去浪费时间。然而,面对四面涌来的质疑,田野心中那名为“斗志”的火苗却越烧越旺,他想,“我就是要做出一些别人认为做不出来的工作”。尽管每每汇报研究想法时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但田野一直没有放弃。终于,2016年,他率领团队取得了第一个研究成果。
该项目研究是在田野回国时正式完成的。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维度上的多种团簇结构均能够按照预期形成,同时展现出可观的装配精准性和产率。田野团队在透射电镜和扫描电镜下不仅观察到了不同结构的组装产物,更论证了该编码策略的可靠性。在表征过程当中,田野还与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以及南京大学亚原子分辨中心的相关专家展开合作,借助X-射线小角散射、冷冻电镜以及三维重构等多种技术手段多角度展现了胶体纳米粒子在不同结构中的排列方式和真实状态。
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在面向结构的精准构建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装配效果,同时可以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机制在应用层面为多种功能性客体物质的精确组装提供可靠的平台,并有望在纳米光学元器件和纳米诊疗等领域展现出更大的应用前景。项目成果取得以后,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等待,直到2020年年初,相关文章才正式发表。
对于最初的那些怀疑的声音,田野也曾问过这些人:“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做不出来?”他得到的答案各式各样,但田野却觉得那些答案都不能成为他停下脚步的理由。他说道:“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才是投身其中的那个人,我知道研究能不能行,什么程度能行,所以别人说的那些不行的原因,我觉得都不是原因,都是可以克服的”。
祖国是出发点也是归宿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中国历史上,很多科学家远渡海外就是为了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如今,这一点在新时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身上仍有體现,这其中也包括田野。他决定回国时,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尤其是他的爷爷最为开心。
其实早在田野出国时,爷爷就叮嘱过他,“你出国的目的就是去学习好技术,然后回来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这是不用怀疑也不能动摇的”。老一辈的爱国情怀自然而然地传承到了新一代的田野身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虽然说报效祖国听起来有点太大,但是这确实是我最初的初心,也是我最终的归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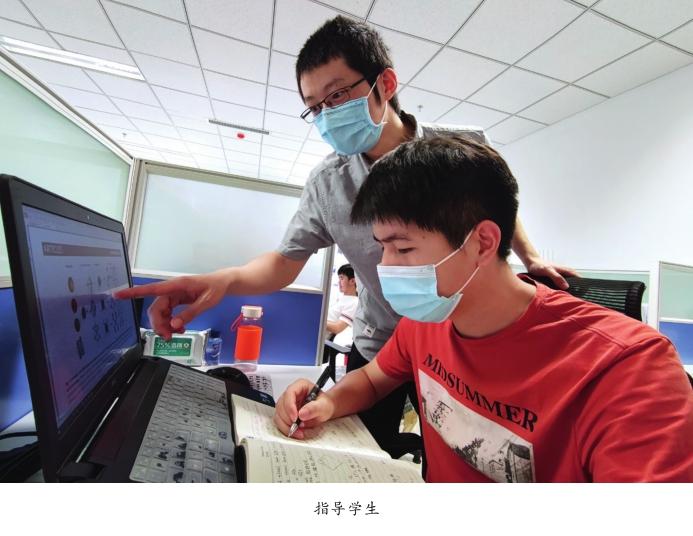
2016年,田野已经在考虑回国的事情,偶然之下,他又见到了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前任院长陆延青教授和现任院长吴迪教授。一番交谈之下,田野对于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有了初步的认识,他认为该学院虽然年轻人居多,但是学院充满朝气,而且该学院在整个南京大学里面是少数以应用方向为主的学院,这些都十分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回国之际,只投了一份简历给南京大学。
选择南京大学作为落脚点,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理由,那就是,田野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这一选择的背后其实还包含着对母校的情感。回国后,田野致力于DNA纳米技术在光学、催化、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应用拓展,其主要研究方向大体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期望通过材料的有序自组装制备相关的电子学、光学材料与器件;第二部分是期望在有机晶体和生物大分子晶体的制备上有所突破。至今,田野已经在这两个研究方向上做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成果。成果已发表于Nature Materials、Nature Nanotechnology、Nature Chemistry、Nano Letters、ACS Nano等领域内的国际顶级杂志。
在谈话中,田野还透露道,虽然现在使用DNA纳米技术的学者很多,但是在其核心上开枝散叶的研究者却不多。不过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优势,那就是在该领域的一些顶尖专家喜欢招收中国学生,而且其中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他表示,这些学者无论是不是在国内其实都在推动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
可尽管如此,田野仍非常希望身在国外的中国学者能回国效力。尤其是2020年年初暴发“新冠肺炎”以来,他的感触更加深刻,他说道:“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自立自强。中国虽然正在日益强大,但它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实现腾飞,科研工作者们责无旁贷。我个人看来,学成归来为祖国做贡献比什么都重要。”
人才培养立足于寓教于乐
1985年出生的田野无论是在科研领域,还是在三尺讲台上,都是“年轻”的代表。如果不认识他,看他与学生们走在一起,是很难分辨出他其实是一位老师的。这不仅因为他年轻的面貌,还因为他没有架子。他像一个朋友一样,和学生一起打打篮球,开一些玩笑,谈一些心事,用一种“陪伴”的方式融入学生当中。
在国外求学时,田野的导师会召集大家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下进行头脑风暴和知识输出。受这种教育模式的影响,田野在自己培养学生时,也十分注重兴趣的培养。他总跟学生们强调,想要做好一件事就要學着享受做这件事的过程,只有你享受这项工作,你才能有动力一直坚持下去。
“科研工作是一件极需要主动性的工作,它需要你主动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甚至主动与他人进行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做出好的成果。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建立在兴趣的基础上。”田野并不是一位“严师”,他会尽力为学生们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在学业上也不会责骂学生。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对学生的“包容”没有底线,他表示:“如果规定9点要来实验室的话,他们晃荡到10点半才来,这可不被允许。在研究工作的一些方面我可以不设限,但是该有的规矩还是要有的。”
在交流过程中,田野还提到了他带领的第一位学生,语气里满是骄傲和欣慰。回国第一年,田野并没有学生指标,然而巧合的是,他通过“捡漏”获得了自己教师生涯的第一位学生。目前,这位学生已经成长为团队内研究能力和科研成绩最为出色的成员之一。除此之外,田野还与其他老师联合培养了多位优秀的学生。
交谈至尾声时谈及未来的规划,田野表示其工作重点仍会放在DNA纳米技术的应用拓展上。不过,他也坦言,DNA纳米技术要真正实现落地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虽然现在他和团队已经在为技术转化做准备,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
专家简介
田野,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双创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者;曾先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就职于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南京大学化学与生物医药创新研究院双聘PI;同时担任南京大学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江苏省功能材料设计原理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DNA折纸术的可控组装与应用;基于DNA核酸材料的新型光学,电子学材料与器件;形貌与组分微观可控的光催化,电催化,光电催化体系;基于核酸体系的体内体外疾病诊断与肿瘤靶向治疗;基于物理或化学沉积法的功能材料制备及相关电学/电池性能研究;基于DNA折纸术的原子制造,特定力学/光学/磁学/电子学等功能材料的定制等。迄今为止,共发表SCI论文20余篇,论文发表在Nature Materials,Nature Nanotechnology,Nature Chemistry,Nano Letters,ACS Nano等国际顶级杂志,在领域内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相关研究被国内外科学媒体撰文报道或采访多达30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