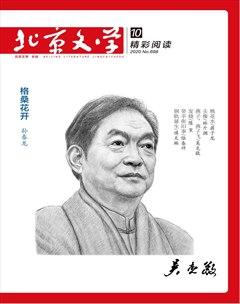想吃

李晓晨
新人自白
近些年有些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离生命的结束如此之近。亲人们不可避免地逐渐老去,认识的人猝不及防倒在地上,朋友的朋友从高楼上一跃而下,每天都微信聊几十条的人得了重病,这让我对生命和生存本身不由自主地充满怀疑,无从解释,只能更加对生命满怀敬意。
这世界啊,变是常态,对于我这么一个渴望掌控全局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糟糕的消息,无从知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时候这种态势常会让我抓狂。我意识到,生命最后的存在有着何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濒死时候的欲望、挣扎、遗憾、愤怒……都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无论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多么强大,都终将陷入一种无法评判是非的境地,而这大概也是人生必需的经验之道吧。于是,我想在一个故事里呈现人之“将老”和“将逝”的某些侧面,也愿意有更多人注意到生命的火烛行将熄灭的最后时光,欲望和念想返璞归真,走到了确实的本源状态。并非什么悲剧,就像人走着走着一定会遇到的最后的那个路标罢了。
跟朋友聊诗人鲁米写的那首诗:“日落有时候不是很像太阳初升吗?/你可知道忠诚的爱是怎样的?/你在哭泣。你说你把自己耗尽了。/然而你想象一下,有谁不是/同样被烟雾笼罩着的呢?”这大概是首写爱情的诗歌,但其实不管生的坚韧还是死的挣扎,大概率也是这个道理——日落有时候的确像极了太阳的初升。尽管遭遇病痛、厄运、灾难……人类的生命依然那么生生不息,就像几千年前祖先们留在石刻和壁画上的图腾符号所寓意的一样。
真正动笔写时才发现之前把这事情想象得太轻易了,创作对一个人的要求实在不算太低,虚构更是一道需要费尽心思才可能逾越的沟壑,当然过程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最后的成品。
没想到的是,写作居然让我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看待周围的眼光,像戴了一副高清模式的眼镜,曾经视若无睹的花草树木、人鸟走兽,在人的视野里丰满立体地浮现出来,甚至,连仲春时节紫藤叶上的脉络都清晰可见。这大概也是创作的乐趣之一种——重新发现和认识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奶奶病了有些日子了。初春的时候,她还能从家里溜达出来,穿过狭窄悠长的胡同,一直逛到大槐树下的过街天桥那头,但到了初冬,就只能走到家门口几十米远的菜摊子了。她走上几步就开始气喘吁吁,只能随手捡起一块不知哪来的白泡沫板子垫在屁股底下,仔细打量着那些红的辣椒绿的菠菜黄的生姜,有时忍不住一个个顺着边儿摩挲过去,“多好啊,要是再便宜点就好了。”她心下暗暗想着,一口浓痰卡到了嗓子眼儿,就顧不得那些蔬菜和鸡蛋是不是新鲜便宜了。她不得不死命地咳上几大口,地上就多了几口浓得化不开的痰,她以为,是同样浓得化不开的雾霾害得她咳嗽个不停。
其实,不是的。
她得了癌,是肺癌。大夫说到了这把年纪就不用化疗什么的瞎折腾了,活多长都够本儿了。也是的,我奶奶已经八十九了,她享尽了很多人间的富贵荣华,和比她大十来岁的老伴儿相伴一生,生了好几个孩子。不过就算这样,她也是不满足的,人总是希望可以长命百岁,要不然当年秦始皇怎么会派那么多人奔瀛洲寻仙丹去呢?我奶奶也无非是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太太,她在那时候只有两个诉求,一个是从医院搬回家住,另一个就是盼着老天爷救救她。当然,这两个愿望最后都没能实现。
那会儿的我奶奶已经完全没有以前的英姿了,以前她完全李铁梅啊——我说一你不能二,我说往东你敢往西?我奶奶,炒土豆丝还是扁豆丝都由她决定;闺女头晚上敢和她吵架,第二天直接堵在门口不让上班。洗个公共澡堂子走了都得回来看看,生怕我们让给别人,就好像谁还能在热水龙头底下冲一辈子似的。但最后几年也还是低头了,人在屋檐下,老太太聪明了一辈子,是明白的。她和我爷爷在几个孩子家住了六年,不雇保姆成了我奶奶最后的倔强:钱么,有的。脾气,有的。雇人,不行!这口气赌到最后,伤人一百自损八十,谁也不痛快、谁也占不着便宜。
“想吃”,是我们那地方的一种说法,“吃”这个字是轻声,意思是说人挑三拣四,口味古怪,我想这个词应该是在食物不充足的年代才有的,因为也只有在吃不饱的时候人才会把“想吃”当回事儿——都吃不饱呢,还想三想四?
我奶奶也受到了这样的指责,当然是暗戳戳的,谁也不敢当着她的面说什么,被牵连的还有一顿能吃一个肉夹馍一大碗燕麦粥三只大对虾的我爷爷。我奶奶吃得不比他少,甚至还更有几分挑剔。她像个骄傲的公主,就算落了难也还带着几分矜持和尊严,不像我打过仗的爷爷特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老觉得孩子们舍不得给他们吃好的,老了老了,看在眼里的竟是几片牛肉一袋牛奶,还有那锅紫菜蛋花汤里到底放了几个海参。若早饭是鸡汤挂面加个荷包蛋,中午那顿一定得切上几片肥厚的酱牛肉再配上一盘青菜,吃过晚饭还得来上斤奶,要是连着两天只有白菜萝卜炖豆腐、红烧带鱼之类的,第三天就一定得去买一只德州扒鸡或是酱肘子给切了放到桌上,要不然老太太一早一定会坐在楼下云淡风轻地跟一群老头老太太说,她这几天没吃饱都没力气绕着小花园散步了。第二天,这样的传说就会蔓延开来,就连那个只有每天天不亮才下来锻炼的美国老太太也大概知道了个所以然。
我奶奶很满意这样的效果,可能比男女关系在传播效应上稍微差点儿意思的就是儿女不孝了。以我的经验来判断,好像每家都不缺这样的故事,但大家就是怎么都听不够,必须得从别人家的狗厮猫咬里咂摸出点儿甘甜来。
晌午的阳光明晃晃刺下来,毒辣得有些让人眼晕,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蹲在树底下正等着蚂蚁爬出来,汗珠子一滴一滴地砸下来,我奶奶坐在白色泡沫上看着这个胖孩子,心里突然有些难过。她的孩子们也都是从这么大长起来,然后风生水起,就算最不济也衣食很是无忧,不用给政府添任何救济的麻烦。他们明明有钱啊,怎么就不舍得买点好的吃?我奶奶越想越愤慨,她看着胖孩子手里那根圆而大的彩虹棒棒糖,不由得慢慢走上去劈手夺下。“奶奶,你饿了?”胖孩子倒是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奶奶,你吃吧。我家还有。”我奶奶于是很满足地拿着那根棒棒糖,一口接一口地吃到只剩下一根光溜溜的塑料棍儿。天空青碧如洗,几朵飘来的云都似乎现出了棒棒糖的样子,我奶奶吃着、望着,满足的笑堆满了脸上的每一道皱纹。胖孩子不一会儿就走了,跑回家拿更多棒棒糖去了。
然而,我奶奶是有糖尿病的。我姑姑赶紧把她送到医院一阵打针忙活。“我就是吃个糖嘛”,她念叨着。
我姑姑暴跳如雷,她亲妈可是连口米饭都不肯吃的,这会儿居然吃了根棒棒糖。
“妈,你疯了吗?”
“你们不让我吃饱。”
“我们怎么不让你吃饱了?”
“你们不让我吃饱。”
“早上不还吃了两片面包一个炸鸡蛋和一碗热牛奶吗?”
“我没吃!”
“你吃了。”
……
我奶奶翻来覆去地絮叨着抱怨着,她时时刻刻都在憧憬着接下来吃些什么,在每个正常的一日三餐的饭桌上,她和我爷爷几乎能吃下三个成年人的食物,就算有时略有挑剔那吞吞咽咽也是分外努力和真诚的。我隐隐觉得,他们所有的热烈和安顿就都来源于这食物了,所以一切看起来只关乎吃食,但似乎又不是。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雇人吧。”我的姑姑伯伯们很是无奈,妈是亲妈,养老院总是传说里地狱一样的存在,可谁又全顾得了呢?这老两口,七老八十,能吃能睡,还隔几天一出戏。
“我想吃饺子。”
“这么长时间都不炖排骨了?”
“昨天的饭还给端上来啊。”
“这汤里有沙子。”
“这个窝窝头蒸的,豆面太多了。”
……
我奶奶和我爷爷把所剩无几的精力全用在吃上了,就像每天必须要攻下的三座堡垒。他们面前放着一格一格的塑料餐盘,上面笑嘻嘻地蹦跶着两个hello kitty,一个粉色的,一个是黄色的。我奶奶细嚼慢咽偶尔嫌弃挑剔几句,我爷爷呢一般不怎么吭气儿,吃完就去床上沙发上躺着。
“那黄瓜鸡蛋汤你也喝,我都不稀罕。”有次,我听见她这么说。“就得吃饱,我管他呢,吃慢了他们就端走了。”我爷爷聋得厉害的耳朵那会儿也灵了。听他们说这些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好笑,老两口到了这把年纪竟然倒着活回去,像孩子一样只惦记着吃到嘴里的那一口,但也是可憐,我打过抗日战争的爷爷和我那挥斥方遒的奶奶,最后也不过是这样。
那场最激烈的战役还是爆发了。到我奶奶死后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凌晨一点多,他们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完全听不清是谁。
“能不能好好说?”
“妈没了。”
我第一反应就是拍醒在另一个屋刚睡下的我爸,此时离我们从医院回来不过几个小时。我眼前全是她的脸,笑的、哭的、誓不罢休的、歇斯底里的,各种各样的脸不停地颠来倒去,像川剧里技艺高超的变脸表演。后来我有几次梦见过她,但都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听不见她到底在说些什么。只记得有次影影绰绰的,她费劲地移动着肥胖的身子走到我跟前,在我旁边的沙发上蹭来蹭去,就像一只在衣柜里待腻歪了来找人解闷儿的大猫。
大表姐呆呆地瘫倒在沙发上,老太太没了,她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觉,松了口气后却又涌上来一股很深很重的难过。这像是一场特殊的仪式,我麻利地穿好衣服,还套上了一件从来不穿的难看的羽绒背心,十二月的北方温度低得让人痛不欲生,和过去一样,倘若有大事发生,我的大脑就会莫名其妙清晰起来,一反平日中度痴呆昏昏沉沉的常态。
出租车在夜里前行,路上空荡荡的,凄清白冷的光把两旁的梧桐树照得肃杀静默,像灾难发生的前一刻。这是灾难吗?我也不太清楚。回来的这个礼拜,我每天都去医院看她,但不知道她认不认得我。她本能地握着别人的手,手指就像快要死去的植物的藤蔓,一捋直又马上弹回去,它们强烈地盼着另一只手的触碰和抚摸,就像预感到要掉进水库里的孩子,我这才知道原来一个老太太的手有这么顽强的意志。
车开得很快,这个时候往医院赶的基本上没什么好事。司机听得我们的只言片语也大概明白了几分,他用尽量快的速度在20分钟后就开到了医院。一辆黑色的中巴车停在住院楼的大厅门口,周围静得瘆人。我奶奶的三个孩子立在走廊里有些魂不守舍,一个一直守在病房,另外两个刚从家里赶来。病房里的白炽灯亮得直刺人眼睛,惨白的灯光里是一间放了四张床的肿瘤科病房,我那当医生的姑父说,进来这里的从来就没见有几个活着出去的。
我奶奶躺的那张床的四周挂着直垂到地面的浅蓝色布帘,被请来穿老衣裳的人正满头大汗地忙活着,他大概不到一米七,五官长得很开,显得一张脸没什么重点,但手脚却是分外麻利,甚至比女人的手还白嫩细长,点到哪儿都是一片锦绣。手边的那套衣裳颜色质地很是讲究,红色缎面做底,上面绣着一对张开翅膀的仙鹤和一丛茂密的松柏,簇新的棉花打得均匀饱满。在我的老家,人不管是哪个季节走的,一定要穿上一套棉衣裳,这样到了另一个世界才能不被饥寒所迫。另三张病床上的人睡得很沉,连翻身和喘气声都听不见。蓦地,对面那个一直没人照顾的老太太突然坐起来了,貌似还轻声细语地打问了句什么,但我一句也没听清,眼前依旧是一片明晃晃的红色。我大姑说,她妈一辈子也没正儿八经穿过红色,就连结婚的时候也没穿上,所以最后一定得从里到外红彤彤地走。
躺在那儿的真是她?我有点儿不大敢认,下午不是还胖乎乎的很活泛嘛,清醒的手指不停地抓我,现在怎么穿衣服都这么费劲?她那么讲究吃喝,真的吃饱了穿合适了?
穿衣服的人很是熟练,人家挣的就是这个钱。戴好帽子,穿好鞋子,最后还很有仪式感地在她嘴里放了一个小小的金色元宝,然后郑重其事地嘱咐,“一会儿到了要记住,小心,用力托一下下巴这里,老太太就能闭上嘴安心去另一个世界了。” 我大伯点了点头。小个子男人又看了他一眼,确认他真的听懂了,然后四处打量了一下,短促有力地说,“抬吧!”我奶奶就这样躺在不锈钢的板子上,下面套着金黄得直刺眼睛的布袋。她似乎比平时重了好几十斤,四个男人抬起来都有点儿吃力。“千万不能落地上。”那人又嘱咐了一句,几个人就更加卖力和仔细着了。
清晨两点是一天里最冷的时候,殡仪馆跟肉联厂的冰柜差不多冻得人哆哆嗦嗦。楼梯上响起一阵拖沓的脚步,一个一米八多的小伙子走下来,眼都还没睁开。他按程序看过证件,登记资料,然后懒洋洋地冲着楼上喊了一声——“别睡了,来活儿了啊!”又几分钟过去,另一个小伙子慢吞吞下来了。是的,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接下来他要完成的一系列工作包括:登记,带家属抬尸体,打开冷藏柜,放进去,关上冷藏柜,锁门,再回去睡觉。这地方几年前我来过一回,考察民政局推广的新型殡葬服务,那个穿着制服的长相清秀的女人带着我们四处参观,走到一个工厂车间一样的地方告诉我们,这里是死者最后火化的地方,可以从屏幕上看到整个过程,就完全实现了可视化人性化服务,绝对不会烧错了。听到这儿我哇地就吐了,中午吃的殡仪馆工作餐喷了一地,有人把我扶到外面的空地上坐下,晴日里的太阳很毒,就跟等我奶奶出来那天一模一样。
我奶奶是在她死后的第二天火化的。那会儿我爷爷还活着,没法让她按我们那儿的风俗在自己家停满三天再走。那天的日头一副要把人烤焦的劲儿,可不知怎的我还是觉得冷。旁人递过来一把黑色的大伞撑开,骨灰是不能直接晒太阳的。蓝天白云,绿树成阴,这里就像现代工厂的流水线,一切井然有序。
我爷爷在我奶奶走后不到俩月也离开了,用老话说是“老死了”。他活到九十多,耳聋眼花,但身子骨硬朗结实,心脏一分钟跳四十几下,符合所有传说中的长寿指标。走前的几个月,他脾气暴躁了很多,扔碗摔盘子,拐杖杵得地板咣咣响,后来还学会了不吃不喝不吱声地示威。他想去医院看我奶奶,家里人拗不过,还是推着他的轮椅带去看了一次,我奶奶烦躁地摆手让他回家,我爷爷一下子就了,坐在轮椅上嘱咐,“听大夫的话,我跟他们说了,不做手术,咱慢慢养。”离开医院的时候他高兴极了,谈天说地,纵横四海。
五天后,我奶奶走了。
我爷爷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些,我们还讨论过要不要告诉他,说和不说,to be or not to be。据说最后的那几个晚上他一直迷迷糊糊地咋呼,弄得一整层楼的病人大夫都睡不着,每天都在梦里稀里糊涂地念叨,“没时间了,你妈喊我呢。”最后那天,孩子们给他穿上了一身干净整齐的西装,戴了一顶羊毛呢子的灰色帽子,据说是我奶奶快不行的时候嘱咐的,“老头子一辈子没穿过西装,最后得穿西装。”唉,我爷爷最后也还是得听我奶奶的。
关于那场有些说不出口的战役,我也是七拼八凑听别人讲的,唯一的证据就是我奶奶在一张拇指宽的格子纸条上留下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他们没给我荠菜饺子!!!
这句话的最后重重地画了三个蓝色的感叹号,歪歪扭扭,深深浅浅,她大概是在生命快完结的时候用尽全身的力气,和当年参加识字班的绝学才写下了这么一句,而且这东西竟然成了她留给我们的遗嘱。谁也不知道,当初我奶奶到底受了什么刺激。
我爸依稀记得,有一天他陪我奶奶坐在沙发上聊天,我奶奶在一顿东拉西扯中突然抓住他的袖子,一字一顿地说,“你前天是不是带了荠菜饺子馅儿来?”我爸想了想,我妈好像说过那荠菜弄起来多么费劲,花了好几个小时,就点了点头。我奶奶的脸色马上阴沉得能拧出水来,说她就吃了白菜饺子都没闻着荠菜味儿。她狠狠地朝着半敞开的落地窗外吐了口吐沫,这时有几片云吞吞吐吐地飘了过来,丝瓜藤下的几只苍蝇也不甘寂寞地飞来凑热闹,在我奶奶眼里这云和苍蝇大概都是来给她鸣不平的吧。
我爸只是没心没肺地笑了笑,继续看着当天报纸里的社会新闻,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她继续念叨。说实在的,荠菜这东西在我们那儿不算稀罕也不是什么贵东西,每年春天都有卖的,但就是收拾起来麻烦得很,要把根掐了再把黄叶子剔干净,有些手巧能干的主妇,每年春天都会到菜市场买一堆处理干净冻到冰箱里,这样来年一整年就都有荠菜吃了。我爸拿的那包应该就是春天我妈买了洗好择净,分小包冻到冰箱里头的存货,包饺子的时候,拿出来等冻得硬邦邦的冰碴儿化了,同猪肉香油酱油葱末姜末搅和到一块儿,就算齐活儿了。我奶奶也好这一口,尤其是后来。
这话当时就是这么一听,可写在纸上就变得意义重大起来了。他们是谁?我爸开始琢磨,但却没敢吱声,这已经到了事关亲妈生死存亡的份儿上了,一家之言那就相当于胡说八道,而且我爸一贯很,得天马行空不问世事,他也只能在心眼儿里翻来覆去地掂量,想等着万一有谁提供线索再把自己听到的供出去。
他们是谁?
字条上没写时间。我奶奶毕竟不是真的在写遗嘱,所以就不可能像遗嘱似的那么严谨讲究。我奶奶的最后是住在我二姑家的,字条也是在我奶奶从老二家送到医院时穿的衣服口袋里找见的,于是怀疑开始剑拔弩张地指向老二。我爸也依稀记得那包荠菜馅儿是带去二妹妹家的,但又不怎么确定,而且就算这时间地点准确无误,又怎么能保证我奶奶写的就是那回呢?我爹不敢言语什么,只是暗暗埋怨几句,老太太到底是没吃上这口心心念念的荠菜饺子,他有些遗憾又有些释然,还好馅儿是他带去的,没给吃到嘴里总是别人的过错。
然而总有人是不怕事儿的,指责和谩骂声一浪高过一浪。老大一口咬定就是老二舍不得给爹妈吃好喝好,“咱妈说过,在你们家老吃不饱!”两只眼睛通红通红的像极了谁家养的兔子,那顿饺子在这个时候真的已经人命关天了。
“大哥这话可怎么说的,我天天海参鲍鱼的做着,怎么就吃不饱了?话不能剜着舌头说啊!”老二也是不甘示弱的,她一个职业律師,平时打官司都不会让人半分,更何况这点小场面。才不怕呢!
“谁亏心谁心里知道,还海参鲍鱼,连个荠菜饺子都舍不得。”
“我们反正问心无愧,你要孝顺,最后我说赶紧送医院去,你怎么说别往嫂子医院送呢?”
“你说这话我就得给你说说了,咱爸妈开始轮流在各家住这些年,给我念叨了多少你对他们不好。你那良心都让狗吃了。”
“是啊,咱爸妈把钱都给你了,孩子也送出国去了,你倒好,最后多一天也不伺候,不怕遭报应吗?”
“你怎么说话呢,再这么说你信不信我撕烂了你的嘴!”
……
我爸看着另外几个兄弟姊妹惊天地泣鬼神地吵成一团,只能呆呆地立在地上手足无措,他像看电视上的家庭矛盾调解节目似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觉得很恍惚又很诡异。他不大相信老二会那么刻薄地虐待亲爹亲妈,但亲妈没吃上那口饺子他是亲耳听着的。老三跟着老两口过了大半辈子,光没少沾但人家也陪了许多年。老大嘛总是习惯性地发号施令,他们都听他的,好像也没出什么纰漏。他也不知道该信谁,觉得谁都不至于,谁都又有些嫌疑,但总归自己是没有日日照顾在爹妈身边的,也就没什么底气了。只是他又是困惑的,几个兄弟姊妹不是很团结亲近么,怎么这会儿胡言乱语地打成一团?他本能地缩在一个角落的椅子上,只能暗暗祈祷他们不会注意到他,永远都记不起还有这么个儿子。
对我奶奶来说,那顿荠菜馅儿饺子终究没吃进嘴里。
“百日”那天我们一块儿送她走,在她堂堂正正的三室一厅的家里。八仙桌上悠悠地燃着三根香,白檀的味道在一片乌漆麻黑的老旧物件里透着股沁人心脾的清净和明朗。偶有几丝风吹过,几缕青烟一哆嗦,打几个弯又向上去了。这样的日子要摆很多供品,于是那张乌木做的八仙桌上便层层叠叠地摆了许多个碟子、盘子和碗,香蕉、火龙果、猕猴桃、老婆饼、长寿酥、烧鸡、佛手、雏菊……这些新鲜的水果甜美的点心,最后都会落到我们肚子里。据说吃了供品的人一定会得到祖宗的庇佑,对活着的人来说,纵是谁都不会嫌弃这份好运的。
我的伯伯姑姑们也不再吵闹了,只是看上去都带着几分鄙夷和轻蔑,也许还增添了些厌弃。他们喝茶抽烟,有的没的聊着最近的时政新闻社会热点,每一个都特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人再说起那场战争,屋子里安宁祥和得一如往常,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但那道微小的裂痕始终是晒在日光下了,即便再怎么热闹的寒暄,也无法整饬得完好如初。
“奶奶,我饿了,我想吃饺子。”墙上的挂钟已经越过了十二点的坐标,我5岁的小外甥第一个扛不住了,他扯着我二姑的衣袖,率先发出了一声稚嫩的也是最本能的呐喊。
空气一下子凝滞了。
那条微小的细痕陡然晾在了白檀香和斜射进来的午后阳光里,一群洋洋洒洒的灰尘在这细痕里翩翩起舞,不肯罢休。那张满满当当的八仙桌在这灰尘里显得空落落的,即便是刚才热络的天南海北的我的姑姑伯伯们,也都在这灰尘里有些怅然若失,在瞬间停下了手里的活计。
“要不,中午包饺子?”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所有人都仿佛得了最高统帅的命令一般,迅速而有序地行动起来。厨房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老三在厨房里翻腾了十几分钟,终于发现了一个写着“饺子粉”的白面口袋,她小心翼翼地解开上头扎着的半截细麻绳子,好像捧着阿拉丁神灯一样。和面的事儿自然要交给男人了,我爸头一回勤快地主动承包了这活儿,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和心血搅拌着那盆面粉,手腕一转砸出一个窝来,一下又一下,见不得一个面疙瘩从那面团,上冒出来,直到揉出了一个光洁圆滑饱满的面团剥了壳的鸡蛋似的安安静静地窝在搪瓷盆里。我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额头上的皱纹也松下来了,整个人都不再咬牙切齿。
不知道什么时候,老二早就悄悄下楼去了趟菜市场,面和好的时候她已经买来了荠菜小葱和七分瘦三分肥的猪肉馅。春天来了,荠菜又下来了。一捆水灵灵的荠菜扎着细细的黄色草绳,青葱碧绿地躺在地板上,棵棵都透着春天的气息。在一道道复杂的工序以后,它们就会和红殷殷的五花肉馅躺在一起,带着所有的希望和遗憾盛在一个光亮如新的碗里。它早就该变成饺子的,只是生生错过了机会。
已经很多年没这么多人一起包饺子了。对北方人来说,无论什么盛大的节日好像都只能吃饺子,似乎只有饺子才配得上节日的郑重其事。我其实不怎么待见饺子的,就算花样种类再丰富多彩也总觉得乏味无聊得紧,谁又愿意那些重大的日子堆满一盘又一盘的饺子呢?但这会儿,我突然很想尝尝这饺子的味道。
包饺子是老二老三擅长的,擀皮儿,调馅儿,全都不在话下。她们把饺子皮牢牢地放在手掌里, [汇]上小半勺荠菜猪肉馅进去折成半圆,然后手指就顺着一边捏过去,一个白胖白胖的饺子就立在那儿了。饺子皮在她们手里飞快地旋转,被捏成一个个带着花纹的、骄傲地挺着大肚子的饺子,我姑姑说这种元宝形状的饺子是我奶奶教给她的,叫“元宝饺”。她们捏得煞是好看灵巧,手指在白色的面粉绿色褐色的馅儿里上下翻飞,像极了春天高高飞在天空里的风筝,不管你长成金鱼样还是蜈蚣样,总有一刻是要落到地上来的,即便落得迟了一些。
锅里的水早就滚了好几滚很有些不耐烦了,煮饺子的往锅里撒了小半勺盐,说这样煮出来的饺子才不容易破。在我看来,各家的主妇们都很有些生活的诀窍,懂得许多不知从哪里得到的偏方,一个一个就像握着无数通往密室的钥匙。她们很有几分隆重,小心翼翼不煮破半只,饺子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煮得好的,倘若破了,那就浪费了之前所有工序的心血和花费,特别在老辈人那里是犯大忌讳的,这顿饺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煮破的。
没过多久,那包好的饺子就在沸腾的汤里打着转儿地雀跃起来了,再添上两回冷水至沸腾,它们就都雾气腾腾地浮上来了。一盘盘煮熟的饺子端上来了,晶莹剔透却依旧掩不住内里灼人眼球的青碧。我的小外甥的饥饿已经变成忍不住的哭号了,刚才塞进他嘴里的熊仔饼全都没逃掉被嚼碎了吐在地上的命运,我的把他宠上天的姑姑这回倒是对哭声镇定自若,这要搁以前,她早就嚷嚷着先下一盘给他填饱肚子了。
这次,她没有。
第一锅饺子开始冒白汽的时候,她悄无声息地去卧室里四处寻那只瓷碗去了。那只瓷碗是我奶奶八十五岁生日时自己挑的,说不上多么昂贵,无非是商场里打着景德镇名头促销的款式罢了,只是摆在显眼的柜台上冠了不中不洋的四个字的名头,又沾了租金高人力贵的光,所以身价自然比地摊上贵了不知多少倍。那是我奶奶这辈子差不多最后一次去逛商场,她从骨子里致命地热爱着那些星级饭店高档商场进口超市和一切华而不实的热闹高贵,从一而终,无可救药。她在一堆绣金描银的花色里一眼看中了那只瓷碗,白底上游着几条青蓝色戏水的小鱼,瓷质均匀,釉色鲜亮,鱼儿活灵活现,打眼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卖碗的人一個劲儿地忽悠她,这是出口转内销的紧俏货,一个八十两个一百五,我奶奶就拿在手里怎么也舍不得放下了。后来,我奶奶还给这对碗配了两双暗黄色的鸡翅木的筷子,她看重吃到嘴里的东西,也就连带着看重吃饭的家伙事儿。
那只碗竟然锁在床头柜上层的小抽屉里,乱七八糟堆着的针头线脑和七零八碎,丝毫不能掩饰它的光芒,它在杂乱无章里显得分外妖娆,急不可耐地跳脱出来很有些英雄久无用武之地的意思。
我姑姑把那只碗里里外外擦洗得干净清爽,几条鱼活泼泼地游在沾着水珠的碗边儿上,一股久违的生气冒了出来。她就从那热气腾腾的锅里盛了白莹莹冒尖的一碗放在八仙桌的正中央,于是,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每个毛孔的紧张都随着初春时的阵风一股脑地吹散了。再看上去,那本来隆重地在供桌上的鲜花水果,在一碗饺子面前竟好像全都隐身了一般,反倒是那元宝样的形状越发突兀和鲜明了,它们威而不骄,只在香烟和火烛间现出了更加丰满和可爱的样子。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