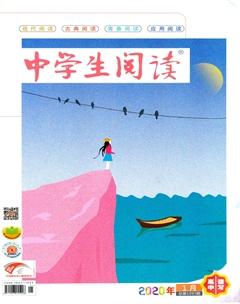君子报仇
唐小兵
每次读到有关校园霸凌现象的报道和讨论时,我就会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经历的那些往事,就会庆幸自己从那段屈辱和难堪的时光里走了出来,实现了与自我的和解。
作为一个不嗜辣、不喝酒、不霸蛮的非典型湖南入,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迷恋武侠,经常舞刀弄枪,自我壮胆,就像走夜路吹口哨一样。一些童年的伙伴每每相聚回首过去,也常常提到一个细节:我在一闾卧室的门背后,曾经用黑色笔写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每每放学归来,或上学之前,个头矮小的自己都会凝视这八个字,找时间练习“花拳绣腿”,希望终有一天能够一改文弱书生的样貌,不再受人欺辱。
幼年阶段我身体发育迟缓,长相呆萌,看上去笨头笨脑的,父母担心我接受不了学校的功课,一直到八岁才让我入读小学。没想到从第一学期期末开始,我就长期占据了班级第一名的位置,班主任和各科老师对我也青眼有加,委以班长的重任。不过,我这个班长基本上是一个消极角色,从不在老师委派的任务之外主动加码,也没有“五道杠少年”的优越感。可不知怎的,班上有好几个男生就是跟我过不去,总是想尽方法欺负我:比如将我小学时总爱戴着的黄军帽取下来,戴在女生头上;比如放学途中,总是在一条黄土大道土肆意地侮辱我,给我取各种羞辱性的外号,充满了挑衅的神态和动作。这种情形之下,我大都是忍气吞声或者忍辱负重。人们常说,只有你在乎的人才会伤害到你。可这些我并不在乎的人,貌似也对我构成了某种心灵的伤害。只是如今追忆起来,我很诧异当年的那个傻头傻脑的少年,怎么就从没有想到向老师反映一下这种情况呢?
好不容易盼到了小学毕业,初中的美好生活在向我招手。因为我知道那几个男生大都不会再接着念书,即使读书,也未必会跟我同班。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乡中学后,没过多久全体同学需要排座位,确定同桌。按照高矮顺序,我恰巧排在了两个从另一所小学来的男生的中间,而他们两人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同桌,就跟我私底下商量,希望我能够往前或往后挪一个位置,玉成其事。那时候的我有一份湖南人的蛮劲,就是不肯顺从,要严格按照老师制定的规则来坐。结果我就跟其中一个个性较倔强的男生成了同桌。
那时候的乡村中学已经配置了可以翻开半边盖子存人书籍、文具的书桌,中午我们就趴在书桌上午睡。我的愤愤不平的同桌在书桌内存放了一根又长又粗的铁钉,午睡时间总是在里面玩弄、比画,其实是含有某种威慑我的意味。开学没多久,发下来各科教科书,没过几天,我发现自己的语文书的一角居然从封面到封底整体地被切掉了。凭直觉我就认定是那个男生所为,可惜那时候的乡村中学没有摄像头,我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质问他,他自然一口否认,作一脸无辜状。我只能徒叹奈何,内心里自然忧愤到了极点。
后来院子里一个老人过世,按那时候的风俗习惯,都要连着几天放露天电影。这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乡村公共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同村刚结婚没多久的五舅过来看电影,顺道来我家闲聊。我记得那正好是一个周末,我也可以娱乐放松一下。我跟着舅舅一起看电影,就轻描淡写地讲了在初中受欺负的事情。五舅长得很壮实,个头虽然不是很高,但力气很大,在当地江湖上也算是一个角色。他听了之后也没说什么,我就把这个当作吐槽式的自我心理治疗,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到了紧接着的周一下午,我们正在教学楼的三楼某一间教室里上英文课,我突然瞥见窗外晃过一个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原来是彪悍的五舅正大步流星地穿过走廊,向教室后面班主任周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走过去。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静止了,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估计我都能敏锐地察觉。我特别担心那时候有点“好勇斗狠”的五舅冲进教室,拎起我的同桌摔到教室之外或一顿暴打(尽管我曾多次在睡梦中梦见这一幕)。好些同学都是认识我这个五舅的,齐刷刷地转身或转脸看着我。只听见五舅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大声说道:“我外甥要是在这个学校被人欺负了,我就找你这个班主任负责。”听到这话,我难为情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可对于五舅来说,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记得周老师很耐心地对他说:“你放心,小兵成绩好,又懂事,很快就会获得同学的信任,不会被欺负的。”五舅获得这个承诺之后,从办公室走出来,向着我那曾经不可一世如今瑟瑟发抖的同桌狠狠地瞪了一眼,就扬长而去了。
确实,如周老师所言,由于五舅的“积极介入”和同学们的信任,我较快地在这个新的集体里建立了某种类似于“威信”的东西,也当了班长。而同桌知道我背后有个这么厉害的亲戚,再也没对我做过小动作。初中三年总算平安无事地度过了。
很多年后,我在一次寒假回乡过春节,与父亲赶集回来走在乡村的那条直行大道上,偶遇了小学时曾经欺负过我的一个男生,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态。彼此面貌都变化很大,他一直在广州、深圳等地做生意,而我这些年客居沪上。其实他的父亲还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就跟父亲谈了一点小学时受霸凌的尘封往事。父亲很惊讶,他不知道那个每学期期末从学校捧回奖状的儿子其实同时还有一段在阴影之中的人生,问我为什么没有及时告诉他。无论是作为村支书、家长还是那个男生父亲的好友,他都是可以很轻易地解决这一问题的。而我在漫长的岁月里居然选择了沉默,只是用门板上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来自我砥砺,作为“弱者的武器”来自我调节。
我感到庆幸的是,这种委屈与怨愤并没有长久地牵缠我,以至于成为一种难以解开的心结,甚至影响人格和心智的正常发育。我将屈辱转化为学习动力,将遭受霸凌变成自强不息的动力。这或许得归功于我天性里那一种对外界反应迟钝的憨傻和“谨慎的乐观”吧。
(选自2019年9月28日《文汇报》,有删改)
阅读点击
作者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叙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