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与珍妮:乌云密布,只待雷鸣
毛旭
一、青涩
1821年6月初,珍妮·威尔士家里来了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她小时候的家庭教师爱德华·欧文:他时年29岁,英俊潇洒,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他自信大方。暗恋欧文的珍妮和他聊起了往事。他带来的那个陌生人没有加入到对话中,而是和珍妮的母亲攀谈起来。这惹得珍妮不时拿余光打量他: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并不帅气,但好在有一双湛蓝的眼睛;他身材高瘦但不匀称,穿得土里土气,举止之间显得笨手笨脚。
托马斯·卡莱尔对珍妮一见钟情。彼时,26岁的他正处于迷茫阶段,欧文带他出来散散心。卡莱尔被眼前的姑娘迷住了:她身高一米六五,秀丽苗条,黑眼睛长头发,沉静时显得温柔,开口时满嘴学问。卡莱尔之所以不跟她交流,倒不是欲擒故纵,而是因为他被女士拒绝过,被吓破了胆。
卡莱尔1795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个泥瓦匠,母亲给人当女佣,两人虽不大识字,但都是个性极强之人。他们信奉加尔文主义,当所属的教堂纪律不够严酷时,他们独立出来,成立了更严酷的分离教派。他们崇拜工作,不苟言笑,对灵魂的不朽和地狱的永火深信不疑。在卡莱尔看来,父母是上天给他的最好馈赠,他说他的父母比国王还高贵,他说他的使命就是把父母教给他的道理传给世人。当有人问他如何培养出如此雄壮的语言风格,他说他父母就这样说话。这种崇拜是双向的,在父母的鼓励下,卡莱尔从来没怀疑过自己是天才。至于贫穷和出身低贱,卡莱尔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十分自豪。这种莫名其妙、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使卡莱尔保持独立并最大程度地培养意志力,但在人群中却是处处碰钉子。在学校里,卡莱尔与老师同学不和,因为他大多数时候沉默不语,开口时却居高临下。
尽管卡莱尔相信自己来这世上肩负着使命,但他在择业时彷徨许久,甚至焦虑得患上了困扰他一生的消化不良。他一开始应父母之命准备当牧师,但当他痛苦地发现自己并不相信基督教时,便改行教学,当了数学老师。然而卡莱尔也并不适合教学:他虽不体罚孩子,但他的“笨蛋”“蠢货”“脑残”和轻蔑的哼气声让孩子们更加恐惧。直到他自学德语并研究了浪漫派哲学之后,才摆脱困惑,决心成为作家,并且有了自己的信仰:在不坚持基督教具体信条的情况下,也可以相信神的存在。
珍妮·威尔士比卡莱尔小6岁。她出身中上层家庭,父亲是医生,有大片的田产,母亲是地主的女儿。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她几乎被父亲宠坏了。父亲把她当儿子培养,送她去学校学习拉丁语和数学。她跟男同学打架,一拳捣出人家的鼻血;她上树爬墙,飞檐走壁,甚至曾赤手掐住一只来袭击她的大鹅。长大之后,她热爱文学,既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又幻想像《新爱洛依丝》中的主人公那样,和自己的老师相恋。18岁时,她的父亲因病去世,她一直没走出阴影。卡莱尔第一次见她时,她还着一身黑色丧服,直到出嫁那天才脱下来。

珍妮有成群的追求者,她在给闺蜜的信中无情地嘲笑他们,卡莱尔也在其列。不过,她确实看出卡莱尔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追求珍妮的方法很特别,不靠耍帅也不靠礼物,而是主动提出教她德语。他热情地寄给珍妮一本《论德国》,并附信:“我们必须尽快见一面,不然我就发疯了。如果我正式来拜访珍妮,珍妮觉得怎么样?她的朋友们会不会嚼舌头根子?”珍妮对他的请求避而不答,只把书寄回来,里面夹了张卡片,上面连他的名字都写错:“卡斯莱尔先生,威尔士小姐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感谢。”
其实,珍妮对卡莱尔是有好感的,他说话时使用的无尽隐喻证明了他的才华。但是卡莱尔举止粗鲁,满嘴方言粗话,不思悔改还引以为傲:他把珍妮家的壁炉架给挠坏了,地毯也被他踩脏了。珍妮说要给他准备一副手铐:“除了舌头,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全都笨拙不堪。”
卡莱尔多次“威胁”要去她家检查她的德语是否进步,被珍妮的母亲阻拦。在经历了最初的挫折后,卡莱尔不再一厢情愿地假装珍妮爱自己。他仍旧与珍妮保持联系:一来他确实喜欢她;二来他感到孤独;三来他打心底里知道,珍妮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孩子。她喜欢写信,擅长叙事,“能将一把笤帚的故事讲出花儿来”。他鼓励她学习哲学,鼓励她成为作家。这极大地迎合了珍妮的志向和虚荣心,久而久之便对他产生了情感的依赖。尽管她说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有且只有父亲,尽管她说“我爱你,但没有爱上你”,但当卡莱尔宣布退兵的一刹那,珍妮却献城投降了:“我怎么能够离开唯一那个理解我的人呢?我宁可明天就嫁给你,也不让你离我而去!”
二、裁缝
尽管珍妮的母亲极力反对,但珍妮毕竟任性惯了,這桩婚事还是随了她的心愿。1826年,31岁的卡莱尔和25岁的珍妮成婚,搬进了在爱丁堡租的小房子。后世传言两人的婚姻有名无实。不管怎样,有两点是确定的:第一,卡莱尔是个属灵而非属肉体的人,他一生都表现出对欲望的冷淡;第二,当有人说“卡莱尔属于那种不应该结婚的男人”时,就算指的不是他的身体状况,那也适应于他的心理状况。
他们在爱丁堡住了两年,但卡莱尔的收入太少,不足以支撑生活,而且他嫌总有人来做客,便和珍妮搬到了她祖上留下来的农庄。
两人在农庄上的安排是:由卡莱尔的二弟负责种地,卡莱尔写作,珍妮照看家务。卡莱尔作息很规律:因为经常失眠,所以起床时间不定,但不晚于7点。散步回来,8点吃早饭,抽烟,然后开始工作。中午在办公桌上喝点茶或咖啡,吃点布丁。下午2点骑马锻炼,6点左右吃晚饭,然后小睡,再之后阅读。后来搬到伦敦后,晚上的部分时间也用来见客。
珍妮的生活则显得有些空虚,因为家里雇了一个女佣,所以留给她的家务不多,她顶多是写写信,学学意大利语,白天捡拾鸡蛋,晚上缝缝裤子——她结婚后才学会的。刚开始的时候,卡莱尔还能在白天陪她骑马、散步,晚上一起学西班牙语,但随着写作压力的增大,卡莱尔便顾不上她了。
事实上,卡莱尔几乎受不了和别人一起做任何事。他属于那种有“思维洁癖”的人:他思考的时候,不能有人在身边,哪怕对方安安静静待着也不行。久而久之,夫妻二人散步也不在一起,而是像倒班一样轮流出行。有时就连吃饭也只是珍妮一个人,餐具的碰撞声格外刺耳。珍妮的孤独和无聊可想而知。尤其到了大雪封门的时候,一连几个星期都见不到人,连邮递员都不来。珍妮开玩笑说,要是断炊,他们连易子而食的机会都没有——既没邻居也没儿子。对卡莱尔来说,这是天堂;对珍妮来讲,这就是地狱。卡莱尔晚年时常说农庄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丈夫日夜辛劳,妻子默默忍受,1831年,36岁的卡莱尔终于生出了“第一个孩子”——《拼凑的裁缝》。这是一部非常另类的哲学作品,卡莱尔假借一名专门研究“衣裳哲学”的教授,发表了对社会的看法。为了推销它,他和珍妮去到伦敦小住,但没人愿意出版这本书,最后只得在《弗雷泽杂志》上连载。卡莱尔穷困至极,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度日。但珍妮毫无怨言,坚信丈夫的价值:“如果他们不出版,你就把‘裁缝带回家,我会照顾他、阅读他、欣赏他,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有钱自己出版。”几个月后,他们回到苏格兰的农庄。此次伦敦之行,不能说是空手而归,因为他们都坚定了一个信念:必须搬到伦敦去。对卡莱尔而言,那里是机遇;对珍妮而言,那里有社交圈。
三、革命
1834年,卡莱尔夫妇搬到了伦敦。卡莱尔从此开始了他和公鸡、小鸟、狗、小贩、手风琴乐手等噪声制造者的斗争。“夫学须静也”,他需要集中精神才能工作,结果神经越来越敏感,甚至能听到体内细胞分裂的声音。珍妮作为妻子的任务就是保证周围的邻居不能养鸟和公鸡,但花园里的野鸟也让他烦躁不已,后来他干脆在屋顶上加盖了一层隔音房。
珍妮在伦敦如鱼得水,过起了“座上客常满,杯中茶不空”的生活。她那机智的聊天和大方的性格吸引了很多作家,约翰·穆勒也成了他们家的常客。穆勒在报纸上读过卡莱尔的文章,对他十分钦佩:“卡莱尔是个诗人,我不是;他富有直觉,我没有;因此,他能在我之前洞悉事物,而我只能在他指给我之后,经过一番推理论证才看到或者仍然看不到。”有出版社向穆勒邀稿,请他写一部法国大革命史,穆勒将这一任务推给了卡莱尔,由此便有了历史上一桩著名的焚稿案。卡莱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写完第一卷,允许穆勒将手稿拿回家先睹为快。第二天,当穆勒满脸沮丧地出现在卡莱尔家门口时,珍妮以为他要和情妇私奔。没想到穆勒说:稿子不小心被烧掉了。看到穆勒那痛苦的样子,卡莱尔和珍妮来不及伤悲,先极力安慰了穆勒3个小时。卡莱尔没有细细盘问事情的经过,穆勒似乎有难言之隐:手稿很有可能不是在他家,而是在其情妇哈莉特家被女仆当成引火物烧掉的,但这涉及桃色新闻,自然难以启齿。送走穆勒之后,卡莱尔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是一阵阵钻心的痛。他给母亲写信说:上帝就像他的小学老师一样,大概觉得他的作文写得不好,所以假人之手把它撕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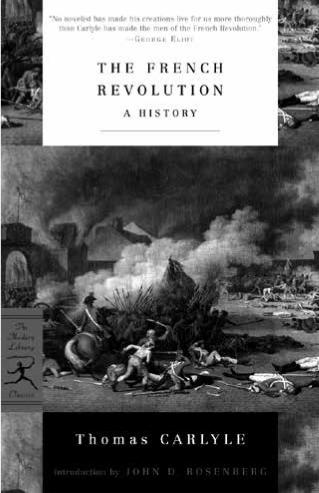
重写的过程既痛苦又漫长。1837年,三卷本的《法国大革命》终于面世了。在其中,卡莱尔把散文写出了史诗的气魄。桂冠诗人骚赛说自己读了六遍,说它在英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狄更斯把它当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并受其启发写出了《双城记》;王尔德甚至能记诵全书,他发挥想象力说:烧掉《法国大革命》的手稿不是哪个仆人,而是哈莉特,因为她觉得写得太好了,担心卡莱尔会以之将穆勒比下去。
《法国大革命》是卡莱尔的成名作,但它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卡莱尔的思想。卡莱尔的思想,简单说来就是:一方面推崇用革命推翻旧秩序,另一方面找到英雄实行独裁统治。《法国大革命》是只有群众、没有英雄的史诗,所以广为自由派所接受。然而自那之后,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就越来越“反动”了。
四、英雄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使卡莱尔夫妇摆脱贫困的局面,而公开演讲做到了。1840—1847年间,卡莱尔做了四场讲座,其中包括后来整理成书、鼎鼎大名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靠着演讲,他和珍妮才摆脱了缺钱的困境。
卡莱尔非常恐惧演讲,视演讲为炼狱,但另一方面,他又坚决不打草稿,因为他相信即兴演讲才是真诚的,才能表达出内心的想法。他开讲时几乎从不抬头,总是不停地用手指抠桌子 ……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渐入佳境,收放自如。
卡莱尔的笨拙反而是他真诚的明证,他奋力挤出的词句,被听众视为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演讲大受欢迎。卡莱尔成了文坛的领军人,被视为一个预言家。最令人意外的是,他受到他所批判的贵族社会的欢迎。是他们,而不是穷苦的白丁,能够欣赏他。他试想:或许英國的未来可以寄托在贵族身上?
并不能说卡莱尔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只能说他原先的想法更加明确。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本来就有极为保守的一面,而这一面现在越来越明显,在《过去与现在》《末世手册》中达到极致。在卡莱尔看来,英雄有权独裁,非英雄有权接受统治——这就是自由的真正定义。卡莱尔关于黑人的观点,使穆勒等自由派朋友弃他而去。他认为黑人骨子里就懒惰,被人逼迫着才肯工作:“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坐在路边无所事事,把脸埋进南瓜里,吸食甜美的果肉和果汁,弄得满嘴、满耳朵都是;他们浑身上下只有臼齿和门牙随时准备工作……周围的甘蔗都烂在了地里,他们也懒得割。”听上去刺耳,但不应该脱离背景来理解:卡莱尔说这话时,英国的很多慈善机构正在宣传奴隶解放,却对眼皮子底下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视而不见。卡莱尔认为这是伪善:对工人进行定时的剥削,和对黑人进行终生的奴役并无二致。
五、贵族
卡莱尔逐渐发展出“新贵族”的概念,他希望改造现有的贵族,让他们摆脱无所事事的悠闲状态。他向贵族靠拢,有两个想法:或者,他自己从政,摆脱文人的空谈和不作为状态;或者,他可以作为导师或先知,指引贵族走上正轨。卡莱尔的确做了很多实事,比如,伦敦图书馆就是在他的倡导和活动下成立的。
但珍妮并不理解卡莱尔的想法,她看到卡莱尔如此频繁地出入上流社会,便吃起醋来。她尤其嫉妒艾什伯顿夫人。艾什伯顿夫人是社交场上的名媛,喜欢网罗名人作家。其实她长相平平,而且偏胖,但几乎没有哪个作家能抵挡她的魅力,因为她聪明机智、擅长聊天,而且“礼贤下士”,总是放下身段去追求名人。珍妮知道卡莱尔对男女之事不热心,但他和其他女人的友谊还是让她感到痛苦。卡莱尔和艾什伯顿夫人交往的10多年间,是夫妻二人关系冷淡的时期。珍妮在客人面前对卡莱尔冷嘲热讽,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大扬家丑,抱怨卡莱尔漠视她的疾病。这些年来,因为疾病的缘故,珍妮的性格变化了不少。她未出阁时,就犯有奇怪的头疼和神经衰弱。结婚之后愈加严重,还受到卡莱尔的传染,胸闷、便秘、失眠已是常态。她因担心卡莱尔失眠而失眠,两人早上问候的第一句话多是“你昨晚睡了几个小时”。她大量地服用鸦片、吗啡、汞丸、蓖麻油……多年的疾病、孤独和无聊让她迅速衰老,脸形瘦削,两腮凹陷。好在在卡莱尔的眼中,她还是那个小姑娘,尤其当她写信时,语调始终是年轻、活泼甚至调皮的。除了写信之外,她沉迷于搜集残忍的刑事案件的剪报,还养了越来越多的宠物:狗,猫,刺猬甚至水蛭。
卡莱尔知道珍妮不快乐,对她心中有愧,所以一再忍让。预言家本是容不得别人辩驳的,他总是滔滔不绝,每当有人试图反驳他的观点时,他总是提高音量把对方打压下去。卡莱尔只容忍一个人的反驳,那就是珍妮。当他和客人聊天时,珍妮就坐在角落里,如果她对卡莱尔的观点不满意,就会皱着眉头对他发出“啧”的声音,卡莱尔就会沉默下来。珍妮经常当着客人的面讲述他的窘事,卡莱尔总是乐呵呵地听着,或许他觉得这是欠她的,客人却感到尴尬。珍妮也只准自己欺负卡莱尔。卡莱尔曾经和客人就爱尔兰的独立问题进行争辩,当双方的嗓音越来越大时,珍妮碰碰客人的脚:“小声点。”客人大怒:“你怎么不让你男人小声点!”
六、蜜月
1857年,艾什伯顿夫人因病突然去世,打碎了卡莱尔从政的梦想。而卡莱尔夫妇的关系也没有立刻回暖,因为介于两人中间的第三者,并非另一个女人,而是卡莱尔的工作——那本怎么也写不完的《腓特烈大帝传》。这本六卷的传记一共写了13年。13年间,他在故纸堆里头也不抬,要不是珍妮摔了一跤,他还以为她有金刚不坏之身呢。
1863年,62岁的珍妮在马路牙子上摔伤了大腿。回到家后,她不敢打断卡莱尔的工作,让女仆去向邻居求助。卡莱尔在听到动静后走下楼来。珍妮摔得很重,再加上之前胳膊的神经炎以及胸痛,她几乎每天都在死亡的边缘痛苦挣扎。卡莱尔这时才意识到珍妮病得有多重。他对珍妮加倍温存,两人好像是在度蜜月。即便如此,卡莱尔也抽不出太多时间陪她,只能让弟弟陪她到外地养病。珍妮依旧保持她那帶刺的幽默:说两位给她看病的医生彼此嫉妒,“巴恩斯医生认为我的腿是他的病人,我的胳膊是奎恩医生的病人”。有时候,她疼得实在受不了,在给卡莱尔的信中,对尘世也愈加留恋了:“吾爱,吾爱,我还能逗你开心吗?我们缘尽于此了吗?我真的好想活下去,这次是为你而活;但我怕,我怕!”
在苏格兰修养一段时间后,珍妮奇迹般地康复了。等她回家时,卡莱尔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一见她便激动得泪流不已,把她抱上了楼。卡莱尔给她买了一套马车,让她每天出去散心。珍妮对卡莱尔也很满意:“我没法向你形容卡莱尔先生对我多么温柔!他还在忙他的写作,但现在特别关注我的舒适和安宁。”所以,当周围有人再养公鸡时,卡莱尔没有像以前那样,怒气冲冲地冲下楼,而是第一次选择了忍耐。珍妮那生动的长信值得剪摘:
邻居家的花园里突然住进了9只母鸡和1只公鸡!多少年来,正因为我英勇地消灭一切噪声,才使得那个花园一向安静。但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维持治安了。当漆黑的凌晨突然响起一阵嘹亮的鸡叫声,声音之大就好像从我床底下发出的,你能够想象我是多么惊恐,多么绝望……我的心脏跳到了嘴里,一边听着公鸡时不时地叫唤,一边等待着卡先生像往常那样在楼上跺脚。但奇怪的是,这次他好像没有听见他的宿敌的叫阵,大概他现在把敌意转移到火车的汽笛声上了……这些日子我一直期待着决战的到来,每一声鸡叫都让我心惊胆寒。我在夜里数着它打鸣的次数——2点一次!3点一次!4点一次!……啊,7点是最可怕的(因为最可能吵醒卡莱尔)!……(受不了的珍妮找邻居交涉)我们达成协议:公鸡必须关在他家的地下室里,从下午3点关到转天上午10点;作为交换,我每天早上教他家的小孩儿读书——那孩子太好动,没有学校敢要。
1865年,卡莱尔终于完成了《腓特烈大帝传》。
1866年,爱丁堡大学决定授予他名誉院长的职位——这可是顶级的荣誉。起初,他予以拒绝,因为听说在就职时必须做演讲。在珍妮的鼓励下,他才答应。尽管没有写草稿、没有睡好,卡莱尔的演讲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卡莱尔的“工作哲学”让年轻的学生们留下了激动的泪水。暮年的卡莱尔终于摆脱争议,成为权威和英雄。远在伦敦的珍妮听到了胜利的消息,激动得差点晕过去。她再次吹嘘自己年轻时的眼力。她给卡莱尔写信,充满幽默和温情:“我在一家旧家具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张腓特烈大帝的照片复本,有点粗糙,不过制作得很像……我下了马车问:‘那个东西(怎么卖)?老板虔敬地说:‘那个,夫人,是彼得大帝。‘我知道!我是问多少钱?‘七块六。我还价五块,他只肯降到六块。你想要的话,我回头把它买下来,挂到我那屋的墙上。”滞留在苏格兰的卡莱尔没有收到妻子的来信。4月26日那天,他做噩梦梦见珍妮,惊醒过来,第二天早上收到电报:珍妮突发心脏病去世。
对卡莱尔而言,这无异于天塌地陷。赶回伦敦之后,他对前来探视的朋友回忆往事,一连几次泣不成声。他看到了珍妮的最后一封信,像遵守圣旨一样赶紧去把照片买了下来。他充满了悔恨:“要是她能再活过来,哪怕只活5分钟,我就能告诉她,我一直都深爱着她!但她从来都不知道,她从来都不知道。”
按照珍妮的遗愿,她和父亲合葬在了一起。自那之后,卡莱尔只是假装活着罢了。他写回忆珍妮的文章:“脾气火暴,没错;很少有比她脾气更暴的,她一点就炸。但伴随着雷电而来的,是温情、希望、天真和善良——我真心怀疑还有比她更高尚的灵魂,她陪伴了我40年。”他把珍妮的信件搜集起来,尽管里面净是对他的抹黑,但他还是决定出版这些信件。正是卡莱尔的大度,使得后世得以见证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书信作家的诞生。
在卡莱尔的晚年,外甥女成了他的秘书兼全职保姆。他的手哆嗦得不能写字,便尝试口述。但其他作家能做到的事,他却适应不了:他受不了工作的时候有人在边上。所以口述失败了。他便基本停止了写作。但给他的荣誉一个接一个。1869年,英国女王召见国内的名人,74岁的卡莱尔在列。轮到他觐见时,女王恭维他说,苏格兰人是非常聪明的民族。卡莱尔回答说苏格兰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无所谓聪明不聪明。一阵尴尬的沉默后,卡莱尔突然说:“要是陛下给老朽赐座,咱们会聊得更开心。”说完拖了一把椅子,在女王对面坐了下来。这在英国觐见史上是第一次,让当场所有人极为震惊,而且女王起身时,才发现卡莱尔的椅子腿压住了她的裙裾。
1881年2月5日,86岁的卡莱尔去世,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原来这就是死亡。好吧。”
七、结语
在当代,尤其在中国,卡莱尔的英雄主义思想一直被视为唯心主义的反面教材——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受过卡莱尔的启发。摘掉标签和帽子,任何一個阅读其原文的人,都会为他的风格所折服,总有一种想要立刻行动、提升自己的冲动。
卡莱尔把工作变成了一种宗教。他和弗洛伊德一样,相信只有工作才能使人身心健康。但他痛苦、别扭的一生却证明了这个命题只是工作狂们的一厢情愿罢了。他那些雷霆万钧的文字,都是在和消化不良、便秘、失眠、噪声的苦闷斗争中憋出来的。他形容珍妮的隐喻也可以用在他的工作上:乌云密布,只待雷鸣。
珍妮的书信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卡莱尔的看法,但圈内人评价“他们两人中,卡莱尔是高尚的那个”。正如塞缪尔·巴特勒所说:“上帝非常仁慈,让卡莱尔和珍妮结成夫妇,这样,世界上就有两个痛苦的人,而不是四个。”的确,他们不算快乐,但他们始终深爱对方——只是工作占用了卡莱尔太多的精力。
珍妮的每个忌日,卡莱尔都会到海德公园故地重游,摘下帽子在阳光底下曝晒,或任凭风雨吹打;他整理、注释了珍妮的书信集,这就是对她最好的补偿。时至今日,这些书信看似是珍妮对卡莱尔的诉状,实际则是卡莱尔写给珍妮的、不朽的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