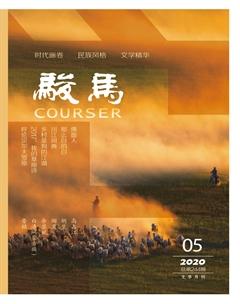额布格的烈酒
李蒙
我的额布格(汉译:祖父)一生最爱烈酒,每当那混着高粱或玉米香气的液体悠然滑过舌尖,又如一条火龙一样经过喉咙,燃烧在胃里,徐徐地游离在鼻腔中,悄悄地潜入血脉时,额布格就会觉得很幸福。那飘着芳香的甘甜,已经成了额布格身体的一部分。
额布格知道那是五谷在吸收了春露和霜天的养分,经过多少个年轮的发酵,才终得开缸扑鼻的芳香。
额布格的故乡躺在富饶的松嫩平原上,嫩江水养育了黑土地,土地上的儿女们恋着嫩江,人们用结实的肩膀扛着生活、扛着日子、扛着黑土地上的春夏秋冬。在这黑土地上,祖辈耕耘四季轮回,子嗣们在这片热土上繁衍、劳作、生活,面朝黑土背朝天。
在额布格的记忆中,伪满洲国时,日本人在额布格出生的西力吐村建立了兵民服务大队,其中有一部分日本兵专门负责征收当地的玉米、大豆和高粱。额布格亲眼见到插着日本旗的马车、汽车将家家户户的粮食强行征走,说是储存起来以备和北方的苏联打仗用。后来一个烧火的日本老兵在屯子里喝醉酒时说:“征粮其实是将粮食运到齐齐哈尔,一部分为军用,其中一大部分是用来做酒,发给前线的日本士兵,为士兵们缓解劳累和思乡情绪。”
额布格告诉我,日本人和后来的苏联人都特别喜欢当地烧锅作坊烧制的烈性酒,因为东北的土地肥沃,生长出的粮食饱满、养分足,所以烧制出的酒度数高也好喝。
想到这里,额布格就异常的气愤,那时候人们尚且填不饱肚子,日本兵还要征粮造酒。所以每到秋天征粮的时候,屯子里的人都将好的粮食藏起来,一部分留着自己吃,一部分给当地抗联。他们将掺有糠皮的粮食留给兵民服务大队,日本人若是问起来,就说今年的粮食收成不好。后来日本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于伪满康德八年,在洮儿河至查干浩特地区投放细菌炸弹来报复乡亲们。
直至几十年后,年迈的额布格始终觉得杯中的烈酒来之不易。喝酒时,额布格酒入口中先不咽,让烈酒在舌尖上尽情地舞蹈,他知道这酒不止是五谷的精华,其中更有着民族的气节。
额布格是个寡言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经常坐在堂屋中目送夕阳落山,听屋檐下的雏燕呢喃,所有的记忆都存放在额布格的沉默里。
额布格告诉后人:“烈酒虽好,但不能贪饮,它能壮了你的胆,也能蒙住你的眼……”
民国三十六年,解放东北的战役打得异常激烈。十七岁的额布格被选中去四平战场上出民兵。据额布格讲述,当时家里面必须要出一个男人去前线,那时额布格的哥哥已经成家,弟弟还小,上前线只能是额布格去。
在战场上,额布格负责抬担架、送伤员,在额布格长调般的叙述中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一排炮弹打过来后,阵地上就会出现很多的尸体和伤员,民兵在此时就要去抢救伤员。
半夜里,额布格被炮火吓得睡不着觉,同屋一位来自前郭尔罗斯的人给额布格喝了几口他带来的酒。在额布格记忆中,那酒有将近七十度,从口中直接辣到胃里,有时眼泪都能辣出来。这样一来,额布格能迷糊着进入睡梦中,第二天再上战场。
后来在一场战斗中,这位前郭尔罗斯来的人被炮弹的弹片击中小腿,额布格把他背回部队。晚上他疼得睡不着觉,额布格守在他身边,大家拿出苞米烧制的烈酒,说了一夜的话。
打完仗所有的人就都回了原籍,再也没有相见。倒是那火一样的烈酒,成了那些炮火纷飞的日子里额布格唯一的慰藉。
我抚摸着额布格的双手,粗糙而又弯曲,就像深秋白桦树发黄的枝干,仿佛吸纳了一个世纪的风霜雨雪。
我年迈的额布格呀,你曾经能将套着四匹儿马子拉满粮食的大车赶向高高的山岗,你能在没有一丝星光的黑夜中放牧马群,你也能扶着铁犁吆喝着黑牛耕种着干涸的土地。
“大鞭子一甩啪啪响咧,几辆大车上山冈咧……”五十年前的额布格双手高举套着红缨的竹鞭,带着各个村屯的马车,给公家送公粮。额布格是当时的车队长,他赶的马车就像夏天的河水既湍急又平稳,鞭哨儿清脆、嗓门儿也高,天不亮的时候,额布格的车队就出发了。
洮儿河的晨雾亲吻着额布格的脸頰,莫莫格的启明星为额布格当向导引路,额布格呷了两口烈酒,瞬间驱走了困倦和寒意。
额布格是地道的农民,他知道一颗种子在土地里发芽成长再到结穗收获是怎样的艰辛,额布格的马车上从来不轻易掉下一粒粮食。寒风刺骨,额布格晚上将烈酒倒入碟中点燃,揉搓着被冻得通红肿胀的关节,此时的一碟烈酒在额布格看来就是一剂良药,酒香随着蓝色的火焰挥发消逝,温暖着额布格冻僵的双腿。
年迈的额布格远离故乡搬到了城里居住,脚踩着水泥柏油马路,额布格想念混着草籽和牛粪的乡间土道。看着街上的车水马龙和整齐的楼房,额布格更留恋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村庄。
住在城市的额布格每天都要喝两杯烈酒,可是他不再犁地、浇地、放马、赶车……额布格经常盯着他的一双手看,他仿佛看到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在他满是老茧的手掌纹路里回荡。额布格知道他是农民,他的一切属于那片承载几代人梦想的黑土地。
白桦树一样的额布格真的老了,在梦里他经常看见他名叫“青大包儿”和“八个爪子”的两匹骏马向他奔来,它们用舌头舔着额布格的指尖,鬃毛蹭着额布格的胸膛,在他面前撒欢儿、奔跑,唿唿地叫着……
额布格曾是一个能带着日月行走的骑手,在一个牧马人眼里,脚下没有过不去的山岗。他走过的原野只有嫩江水知道,放过的骏马只有天上的雨露才能数清。
额布格说马最爱干净,压出的第一遍井水要先给马群喝,额布格说刚出生的马驹子最爱招狼,一定要在家拴好,不能放到马群里来,额布格说犁地的时候牲畜不走不要使劲打它们,要用青草引着它们走,额布格说地里和树上的鸟儿不能打,更不能下药毒死它们,鸟儿多了地里的虫子就少了,粮食收成就会增加。土地是额布格的灵魂,劳作的精髓渗透到额布格的骨子里。
额布格总想捋直他那蜷缩的双腿,可怎么捋也捋不直,年迈的额布格呀,你蜷缩的双腿是累弯的。家中奉养着老人,孩子们还要生活、上学、成家……我的额布格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耕牛在不停地劳作。额布格任劳任怨,就像黑土地一样不求回报,一杯烈酒足以让他满足,更能慰藉他疲倦的心。
晚年的额布格经常会收到晚辈们带来的礼物,好多包装精美的美酒让额布格看不过来。有清香型的、浓香型的、酱香型的……也有十年窖藏、十五年窖藏。但额布格始终热衷于烧制的烈性散酒,他说现在的酒水掺杂了太多的香料,少了泥土和粮食的气息。
额布格默默地倒上一杯烧制的烈酒,没有觥筹交错,更无须祝酒词,轻轻地抿上一口,额布格的故事融进了酒香里。
耄耋之年的额布格坐在轮椅上,浑浊的双眼中流淌出岁月的长河,满是皱纹的脸上映出夕阳的余晖,苍老的手背像老松树的皮。额布格无声地看着他的玻璃酒壶,它曾承载了多少烈如火焰的美酒,流淌过多少醇香绵长的滋味啊,他仿佛听见近百年的岁月在酒壶里回响。
额布格想喝酒了,他高兴地让我帮他接一口酒,虽然颤抖的手已拿不稳酒杯,但火一样的烈酒又一次在他的舌尖上飞舞,如歌在喉的时候,额布格又找到了久违的满足和幸福。他兴奋地讲着当年在三家子麦田如何打的野狼,在南边的湿地怎样救起一只掉队的大雁……他看向窗外的远方,上身立直稳坐,单手握拳,仿佛已经骑上了心爱的马儿奔向田野。
我的额布格一生最爱烈酒,从烈酒中品味百态人生。
责任编辑 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