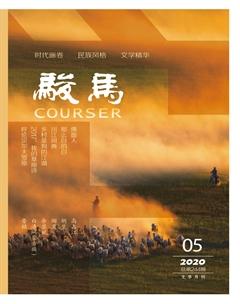逐云记
禄永峰
一块一块的白云或者黑云,像是长了脚,一会儿跑到村庄这头,一会儿跑到村庄那头。村庄的天空,除了云块,再什么也没有。
我不担心那些厚厚的云块落到树梢上,树会把它们托住。云块再大,树也不怕,它们能够托得住。村庄里的大部分树,都是为托住云而生的,它们天天追着云生长着,并渐渐长成一枝伞柄、一林伞柄。树长成了云的拐杖,把云块整天整天地托着,或者干脆在一场风中,把另一些快步跑动的云划碎。
我并不担心那些白云,白云远远看去像棉絮一样,落在树梢上,树叶一动不动。我担心的事情是,从树梢上跌下来的一大块一大块的黑云是不是很重很重呢。树梢托不住了就纷纷掉下来了。纷纷掉下来的那一块块黑云,把一面天都给罩实了,并一点一点朝大地沉落。开始是跌在玉米梢上、高粱梢上,渐渐又跌在麦田里的麦子上,一根根麦子被压得东倒西歪,一旦一整片一整片麦子被压得贴在地面上的时候,我知道,一大块一大块黑云同时已经重重地跌在了一块块草地上。
黄土地似乎没有一块会闲着,田里长满了庄稼,荒山荒坡上,各种各样的小草紧紧地贴着地面。许多小草长足了一年也没有我的脚面高,它们不露声色地潜伏在黄土地上,挨挨挤挤地依偎在大地的怀抱里。每一棵小草,都在努力地把阳光和雨水日复一日地汇聚起来,并顺着根须一点一点输入大地。大地装满了阳光、雨水甚至每一滴露珠。我看见黑云跌在草地上,草的茎叶不再柔软,它们已经把身旁的黄土划出了一道道口子。我想,村庄没有谁发现一片柔软的草叶竟会如此坚硬!(鲁班当年被柔软的草叶划破了手指,他正是看好草叶的坚硬,才发明了锯子。)
草叶起落,轻风泛起。我没有想到,比草叶更坚硬的,竟然会是乘黑云赶来的那一场场风。黑云卷起的风就像把铁梳子,把黄土梳理得松松散散,给四野洗脸去皮,让土地换上新黄。起风了,泥土的气息,如同鱼腥味一样随风乱窜,使村东头的黄土跑到村西头去,村西头的黄土跑到村东头去。而随风和黑云赶来的一场场雨呢,不知道在哪一年,竟然把村头的那座黄土山冲刷成一孔拱形的门洞,至今在村头伫立着。村庄人称其为“黄土之门”,也有人称其为“天下黄土第一门”。这道黄土之门,是村庄里的人,包括马牛羊,甚至风的必经之门。
在村庄里,黄土之门很普通,普通得如一个长在畦埂上的萝卜、一座败落的老庙,没有谁对它高看一眼。地里长出那么多吃食,没人对一个萝卜昼思夜想。日升月落,槐树枝在地上留下浓浓淡淡的影子,与老庙在村口投射出的影子一样,谁也不会去留意。甚至当脚踏上那些影子的时候都不会减力放轻,谁会在意踩疼一块影子呢。门的作用只供进出便足够了,犹如老庙的作用只供空洞地瞻望村庄。
多少年了,黄土之门默默地矗立在村口,就是专门供村庄人或者牛马羊穿行的。那些牛马,被人们牵着穿行的次数多了,即便无人牵着,它们也知道黄土之门是通往外界的必经之门。除了牛马羊,还有那些黑蚂蚁,不知道是谁告诉它们的,它们出出进进,也是沿着这孔门洞。蚂蚁喜欢爬行在村庄人和牛马羊走过的路上。它们一定知道,沿着村庄人和牛马羊的路爬行下去,会有一路的惊喜。比如那一块块庄稼地里,就有一群蚂蚁是沿着村庄人和牛马羊的路赶来的。蚂蚁对村庄像人一样熟悉,经过黄土之门,它们能够爬进村庄,也能爬出村庄。要不,一群蚂蚁只能翻过一座接一座大山,才能去往它们想去的地方。
沿着一座大山洞开的黄土之门,像一个人巨大的手掌,把村庄各处的小路都汇聚到了掌心。沿着掌心散开的每一条路,不仅仅只是供人走,也不仅仅只是供牛马羊和蚂蚁走。各条路上行走的、爬行的,谁也不会干扰谁,蚂蚁爬行蚂蚁的,马牛羊走马牛羊的,人走人的。村庄的路是窄,可村庄的路并不拥挤。有时候,人骑在牛马背上,蚂蚁也悄无声息地爬到牛马背上,一同被牛马带一程。没有哪一只蚂蚁会不喜欢跟着人悄悄地走村庄人的路。
风也喜欢贴着路面行走。风散步的时候,步子很缓很缓,它们还没有蚂蚁爬行得快。可是,风一旦跑起来,比村庄跑得最快的马匹还要快,风跑起来谁也不避让,甚至连同一路奔跑的风也不避让。风追赶着风,风摩擦着风。风一股脑儿地赶到村口,聚集在黄土之门周围,整个门洞成了个大风口,每一股风都争先恐后地猛冲着,像一股大水聚集在水洞口,水流湍急,不时激起飞溅的水花。我最不喜欢在黄土之门下过多地停留,站在风口,会被正在赶路的风掀个趔趄。
我在想,要是没有这孔黄土之门,风只能绕着一座接一座的黄土大山赶路。可是,黄土高原上的山太多了、太大了,如果风昼夜兼程,不知道风会不会累倒在半路上。还有那些牛马和人,会不会也同风一起累倒在半路上。如果他们都落在了半路上,那么村庄的牛马就难以成群,人就更难以群聚了,这座山头一户人家,那座山头另一户人家,整个村庄一下子便会显得四零五散起来。牛羊、人、树,还有风和一块一块的白云或者黑云,都是孤单的。我只能与牛羊为伴,与树为伴,与风和一块一块的白云或者黑云为伴,我也会孤单的。
一孔黄土之门,接纳了世间万物朝它涌来,牛马向它涌来,裹脚老太向它涌来,风向它涌来,几块白云或者黑云向它涌来,孩子们向它涌来,蚂蚁向它涌来,飞机向它涌来……这孔门,是村庄通往远方的幸福之门。要不是我一次次穿行过这孔黄土之门,我的世界又能大到哪里去呢?
春天里,我喜欢躺在黄土之门顶部的草地上,看一只只鸟朝村口飞来,穿过黄土之门,奔往别人的村庄,或者奔往远处的一棵棵大树。我惊叹鸟的探路能力,它们在空中一只紧盯着一只,拍打着翅膀飞翔、滑行,群起群落,它们不会一盘散沙。我知道,群鸟赶路的时候,最前面有个领路的鸟。那么一只鸟呢,它是怎么辨路的,它又是怎么才能找到群鸟,跟随群鸟一起飞翔的呢。一声声鸟鸣,清脆而幽远。这声音,是一只鸟向另一只鸟发出的召唤吗?村庄鸟的种类颇为繁多,麻雀低飞,老鹰高飞,燕子掠过……鸟的神奇并不仅仅在于飞翔,村庄的鸟儿倾巢出动,它们像村庄人随手丢出去的一把把石子,谁跟谁也不会撞在一起。天上不是地上,天上到处都是路。
“飞机,飞机……”正当我的目光追随着一群群鸟四处张望的时候,黄土之门下的小伙伴们早已仰头望着一架飞过村庄上空的飞机。飞机的嗓门真不小,“轰隆隆”的声响,像由远及近的雷声,每一次,总是声音先抵达村庄,好像是给村庄人报个信儿:“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大伙觉着飞机比一只鹰大不了多少,甚至还没有一只鹰大。以致我们中的好几个人,单从飞机传来的声音判断,一致认为飞机一准没有鹰飞得高,平着翅膀飞的速度也没有鹰那么快。
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秘密:那一架架飞机似乎跟村庄的黄土之门有个约定,隔几天总有同一架飞机在一天里的同一时间段经过村庄上空。白天,每一架飞机都要从黄土之门的上空缓缓飞过,一点一点消失在云里。当然,当那一大块一大块的黑云压在树梢上,或者压在高粱、玉米、麦子、草地上的时候,我只能听到“轰隆隆”的声音。这就像几架夜晚飞过村庄的飞机,夜空下我只能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只不过,到了晚上,我还会看见那几颗像星星一闪一闪的机灯,把村庄上空的夜幕拉得更长。黄土之门被璀璨的夜空紧紧地聚拢着,总不乏几颗星穿过厚重的黄土之门。
再后來呀,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了,我突然明白村庄所有小伙伴的梦,都会像鸟儿或者飞机一样,腾空而起,最后穿过黄土之门,飞向远方。还有,我曾经最担心的那一块一块的黑云,从树梢上成堆成堆地跌落下来,看似重重地压在黄土之上。其实,所有的树梢都朝着云块,像花朵似的,偷偷地舒展开了。高粱、玉米、麦子和草,也像花朵那样偷偷地舒展开了。它们就像在参差不齐的黄土地上,架起了一个巨大的花环,密密地把黄土之门围拢着,这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个转身,一块一块的黑云,或将给久旱的大地带来一场透雨呢。
终于,我像村庄其他人一样,对天空跌下来的一块一块的黑云,没再担心过。
责任编辑 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