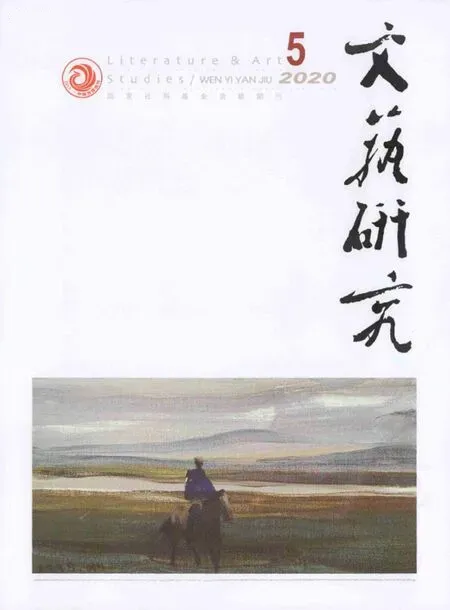反响、影响与历史回响
——苏联电影《生路》在中国
贾斌武
在20世纪上半叶输入中国的众多外国电影中,1933年公映于上海的《生路》(Путёвка в жизнь/Road to Life, 1931)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作为中苏复交后在华公映的第一部苏联电影,该片不仅在当时就获得了“新艺术的登场”①和“世界电影史值得大笔特书的作品”②这样的高度评价,更被认为是“不仅为正在成长之中的左翼电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楷模,而且还给中国电影界指出了一条广阔的道路”③。《生路》的分镜头脚本和文学剧本也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并成为中国电影人镜鉴的对象。时过境迁,当彼时观看这部影片的一部分观众成为新中国电影界的权威人士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念念不忘《生路》曾经带给他们的震撼与感动。连缀这些史实,我们不得不对这部来自苏联的电影产生浓厚的兴趣。《生路》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中国影坛和观众在其上映之初为何如此兴奋?它究竟在哪些方面给中国电影界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样板?它为何会像幽灵一样不断出现在中国左翼电影的历史叙述中?这些问题看似微观,却勾连着20世纪苏联电影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宏大课题,因此值得认真地加以思考。
一、《生路》及其电影史评价
《生路》(又译《人生之路》)是苏联电影导演尼古拉·艾克(Nikolai Ekk)1931年执导的一部有声电影。该片于1931年6月在苏联上映,被公认为苏联第一部有声电影。《生路》亦曾在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上映并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值得一提的是,在1932年举办的第一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该片曾获最佳导演奖桂冠。
《生路》中的故事发生在十月革命后的1923年。影片讲述了由于连年的内战,莫斯科街头聚集着大量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因为无人看管,这些孩子变成了专事偷盗抢劫的流氓,城市流浪儿童因此成为当时苏联国内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苏联政府对待这些作奸犯科的流浪儿,不是用暴力惩罚,而是通过互助公社的形式,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对流浪儿的改造并非一帆风顺。春天来临,冰雪融化导致互助公社的原料运输中断,流浪儿们旧态复萌,开始大肆破坏机器,有些人又重新回到了从前的犯罪帮派。就在此时,负责指导这群孩子的塞尔戈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项新的任务:修建一条连接公社和市镇的铁路。塞尔戈夫和大部分不愿意继续堕落的孩子精心策划,一举摧毁了犯罪帮派的阴谋。通过集体合作,这群曾经的流浪儿最终完成了铁路的修建。然而,就在铁路筑成的当天,这群孩子的领袖穆斯塔法却被此前操纵流浪儿童犯罪的帮派头目杀害。影片结尾时,火车载着年轻英雄的遗体奔向盛大的通车典礼。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生路》显然带有从默片向有声电影过渡的色彩。作为一部有声电影,该片中却穿插了若干字幕,这显示当时苏联电影人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有声电影的创作规律。《生路》给人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其中大量的特写镜头和蒙太奇手法,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早期影片。另外,这部影片还表现出浓厚的苏联意识形态色彩。不同于将观众缝合进叙事中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生路》的开头和结尾均有一位威严的权威人士慷慨激昂地对着观众宣讲苏联针对流浪儿童所实施的改造政策与巨大成就。
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在海外,《生路》均获得了很高的电影史评价。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在其编纂的三卷本《苏联电影史纲》(1959)中认为:首先,作为苏联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艺术片,《生路》在苏联电影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其次,该片是录音质量符合最严格音响要求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巧妙地运用了城市和自然界的各种音响;再次,《生路》是第一部以人物及其性格作为主要艺术对象的电影作品,在苏联国内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当然,苏联官方的电影史学者亦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部影片存在的缺点:“影片中的言语还显得有点拘束。作者仿佛还害怕言语。《生路》中的对话不多,而且过于简略。编剧和导演还不敢摆脱无声电影的传统,因此影片中的字幕在数量上要比人物所说的话多得多。”④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的《世界电影史》(Histoire du cinéma mondial, 1979)一书则称赞《生路》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电影新黄金时代未开始之前“第一部优秀的影片,同时也是最光辉的一部影片”⑤。作为著名的左翼电影史学家,萨杜尔主要强调的是这部影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纪录片式的手法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尾。美国电影史学者陈立(Jay Leyda)在他那部享誉英语世界的《苏俄电影史》(Kino: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Film, 1960)中对《生路》同样赞誉有加,他指出:“尽管这部影片的‘感伤主义’在当时曾引起争议,但由于其融合了技术、戏剧性和政治成就而在苏联电影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⑥同样,《生路》在中国亦备受推崇。1962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称赞该片在上海的公映为中国电影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并声称中国电影艺术工作者从这部影片中学到了“新的创作态度和新的创作方法”⑦。
将上述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电影史学家的评价联系起来,再加上笔者观看这部影片的直观感受,本文要强调的是:《生路》尽管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与同时期的苏联有声影片相比确实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从当时苏联国内的情况来看,受制于资源短缺、复杂的官僚体制以及朝令夕改的意识形态命令,苏联电影向有声电影时代的过渡一直十分缓慢,许多苏联电影人更是无法走出实验电影时代的影响⑧。在这一背景下,《生路》在艺术上的成就显得尤为引人瞩目,该片中充满张力的叙事、动人的配乐以及灵活的电影语言,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由于诞生在苏联电影风格的转捩点上,它得以结合20世纪20年代苏联电影的蒙太奇风格和后来成为苏联电影主导风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没有陷入模式化的窠臼。
本文接下来想要努力说明的是,《生路》在中国所引发的强烈反响并不全然与其艺术性有关,诸多电影之外的因素渗透进了中国电影界和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接受中。
二、《生路》在华上映后的反响
苏联电影在中国的放映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然而,自从1927年12月国民政府断绝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后,中国观众一时很难再接触到苏联电影⑨。建都南京后急需建立文化领导权的国民政府视苏联电影为洪水猛兽,将其列入必须严格检查和禁演的名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32年10月20日发给政府的公函中提出:“有关俄国革命之影片,虽未必尽属宣传共产主义之作品,但值此共匪尚未完全肃清之际,其抄摹红军胜利等,对于民众亦将发生不良影响,应请政府转饬主管机关,对于俄国革命之电影片概予禁演。”在收到这份公函不久,国民政府即以“密令”的形式将其转发行政院,要求“遵照办理”。此后,该密函又被教育部下发电影检查委员会予以严格执行⑩。不过,就在这份“密令”发出的同时,一度紧张的中苏关系却在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推动下发生了变化。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宣布复交,在这一背景下,一度中断的中苏文化交流也重新被提上日程。《生路》在上海的公映,即是中苏复交后恢复文化交流的初试啼声。
1933年2月12日,《生路》在位于虹口区北四川路的上海大戏院举行了试映,许多记者和影评人获邀先睹为快。如当时供职于《申报》“电影专刊”的凌鹤隔天便发表了对该片的评论。他的“没有恋爱,没有女人的大腿和绅士的高帽或夜礼服”⑪的印象式评语,很快就被简化为“没有女人的大腿!没有绅士的高帽!”的口号,并被发行商用作《生路》的宣传广告⑫。不过,《生路》真正在上海掀起舆论高潮则是在2月16日正式公映之后。在《生路》公映的当天,由左翼影评人掌控的《晨报》“每日电影”以整版刊载了对该片的评论。化名“黄子布”的夏衍评价《生路》为“一部继普多夫金的《母亲》和爱森斯坦的《战斗舰伯巧姆金》而出现的,世界电影史上值得大笔特书的作品”⑬。在当天刊登于“每日电影”的另一篇影评中,作者王启煦同样高度评价了这部影片:“在这里,我们探见了另一社会的建设的艰苦的同时,又感觉到新兴电影的艺术的伟大的建树。”⑭就在当天报纸的同一版面上,“每日电影”编辑部还组织史东山、王乾白、沈西苓、金焰、张石川、程步高、黎民伟、蒋军超、聂耳、苏怡、龚稼农等14位电影从业者发表了对《生路》的观后感。这些电影界的知名人士有的赞叹苏联电影所蕴含的力与美,有的对该片的技术和风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则惊叹苏联电影的群众性和教育性,无一例外均对这部影片给予了高度评价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晨报》“每日电影”继续对《生路》展开密集的宣传和评论。如洪深和席耐芳合写的《〈生路〉详评》一文,分别从“新艺术的登场”“题材的选择”“创作的方法”“技术的教训”“综合的结论”五个层面对该片进行了详细解读⑯。在左翼影评人的带动下,上海的其他电影副刊和杂志也纷纷对该片进行了正面的报道与评论,连一向对外国影片评价十分严苛的《电声日报》也给《生路》打出了“A上片”的评分⑰。从《生路》上映后的整体舆论看,上海各主流报刊大都对这部中苏复交后在华上映的第一部苏联影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正如一位左翼影评人所观察到的,上海的各大电影刊物,“所有的对《生路》的批评,差不多一致的是赞美”⑱。

图1 《晨报》上刊登的《生路》放映广告
在众口一词的赞美声中,偶尔出现的一些针对《生路》的批评则大都无关痛痒。如有评论者认为《生路》中的演员表演有些“过火”,并且“导演方面因为有几处重叠叙述的缘故,反而减了全剧紧张的情绪”⑲。另外,有些影评人抱怨该片被“剪删得太多,致使有几处不太连接”,并且希望俄文字幕能“译得更清楚一些”⑳。目前所能找到的一篇罕见地对《生路》给出差评的文章出自华文版的《大美晚报》,一反其他报刊的一致叫好,该报批评《生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且“粗”得像“俄国大菜”。这显然激怒了左翼影评人。尘无在一篇文章中猛烈驳斥了该文的观点,并直指该报的立场与其美资背景有关,从而将可能纯属审美层面的分歧上升到“反帝”和民族主义的高度㉑。通过这一小小的插曲,我们可以发现左翼影评人凭借占领各大电影副刊以掌控电影界舆论的策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围绕着对电影《生路》的批评,左翼影评人群体通过密集的议程设置,有效地压制了其他声音,以致一位非左翼的影评人无奈地抱怨道:“对俄国的片子,说了坏话,似乎总带着反动嫌疑。”㉒
在影评界铺天盖地的宣传下,《生路》的市场反响可谓异常火爆。这一点从《生路》的票价上就能反映出来。作为一家坐落在华界的三流影院,上海大戏院平时的票价不过两角,《生路》的票价竟然一路飙升到六角、一元和一元半,这无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生路》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虽然影院方肆意涨价的行为引起了一部分观众的不满㉓,但超高的票价依然没有吓退那些想要一睹这部苏联电影真容的上海观众。《生路》的良好口碑强烈吸引了许多看惯欧美影片的文艺青年,激发起他们“拼死吃河豚”般前往上海大戏院的热情㉔,而一些社会名流,如鲁迅㉕、宋庆龄、杨杏佛㉖等人,也在他们的日记或回忆中留下了观看该片的记录。
在各大报刊第一轮的评论高潮过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路》的舆论热度仍未消褪。如一位署名“冰”的作者就在《申报》“电影专刊”上发文质疑:为什么《生路》曾在27个国家上映过,却不能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开映?这一追问直接将话题引到了“反帝”的方向㉗。1933年6月出版的《明星月报》第2期更是趁热打铁,刊登了蔡叔声(夏衍)翻译的《生路》分镜头脚本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整个30年代,由于《生路》在观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此后在华上映的苏联电影如《重逢》(不详)、《金山》(Златые горы,1931)、《夏伯阳》(Чапаев,1934)等,大都被放在《生路》所确立的标尺下进行比照和评价。如第二部在华公映的影片《重逢》即被认为在各方面均不如《生路》优秀㉙,另一部苏联影片《无国游民》(Gypsies,出品年份不详)的广告则宣称该片“比《生路》生动,并为影坛的杰作”㉚。1939年5月,当尼古拉·艾克导演的新片《女壮士》(Сорочинская ярмарка,1938)在上海公映时,发行商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依然试图在唤起观众对《生路》的观影记忆㉛。面对《生路》在社会上的巨大反响,一些中国电影公司则蹭起了该片的热度,如强华公司1933年出品、文逸民导演的《我们的生路》不仅在片名上有“蹭热度”的嫌疑,其广告宣传语更是毫不掩饰地宣称:“《我们的生路》的演出与苏联巨片《生路》有异曲同工之妙。”㉜而事实上,该片与《生路》并没有什么关联。
回顾整个中国早期电影史,除了格里菲斯(D.W.Griffith)导演的《赖婚》(Way Down East,1920)和罗克(Harold Lloyd)主演的《不怕死》(Welcome Danger,1929)等为数不多的影片,恐怕很少有外国电影在中国引发过如《生路》这般强烈的社会反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部电影在当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呢?除了影片本身的艺术成就与中苏复交后第一部在华公映的苏联电影这一特殊身份外,我们至少还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正如前文指出的,这离不开左翼影评人的大力鼓吹与推动。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左翼影评人对苏联电影的宣传是有组织、有计划的㉝。其次,《生路》在内容上的讨巧,其宣扬流浪儿童救助的情节很容易在每日目睹大量城市流浪儿童的上海观众那里获得共鸣㉞。一位化名“OK”的观众在等待观看《生路》时,因看到影院外几个穷人家的孩子便联想到银幕内外中苏两国儿童的不同命运,从而产生了深深的共情㉟。无独有偶,在距离《生路》上映四年的1937年,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在看到现实中流浪儿童遭到殴打和驱逐的场景时,立刻便想到《生路》中那些在政府救助下走上“生路”的苏联儿童㊱。这些来自观众的反应无疑证明了在爱国、民族主义等时代话语之外,观影行为更是一种鲜活的个体化的生命体验。再次,《生路》之所以受到热捧还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电影界和公共舆论中强烈的反帝情绪有关。就像一位影评人在评论《生路》时所指出的那样:“上海的一般观剧者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似乎已经感觉厌倦了,因为他们玩的只是‘这么的一套’——黄金、胭脂、醇酒、美人,完全是颂扬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影片,不能不发生了相当的热望。”㊲在时人对《生路》的评论中,我们大都可以发现欧美电影在与苏联电影的对比中成为被猛烈批判的靶子——苏联电影的“力与美”比照欧美电影的纸醉金迷,苏联电影强烈的教育性对应欧美电影对观众的“麻醉”,苏联电影中真实的大众反衬欧美电影中虚假的明星……在某种意义上,对苏联电影的推崇实际上亦隐含着中国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欧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抵抗。

图2 《申报》上刊登的《我们的生路》放映广告
三、“我们的镜子”:《生路》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在与《生路》相关的舆论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部分人都提到该片对中国电影的启示意义。不仅有影评人热情地指出:“《生路》公映了,为中国电影界应该指示了一条‘生路’。”㊳“《生路》是中国影片的一面镜子。”㊴就连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也宣称:“《生路》给予我们中国电影界的,将是一个新的典型。”㊵一部分中国电影艺术家在观看《生路》后,更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面“他者之镜”来反思自身的电影创作,从中获得艺术的启迪。从目前所能找到的史料看,《生路》确实在当时中国电影业内部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概言之,《生路》对当时的中国电影(尤其是左翼电影)的影响和启示主要表现在题材、技巧和艺术观念三个方面。
早在《生路》上映之初,就有影评人指出:“中国影片应该以《生路》做一面镜子,在题材方面,应该给没落的中国人一种鼓舞的希望。”㊶电影界很快对此做出了回应。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不仅制作了一批以“路”为片名和意象的电影,如强华公司的《我们的生路》、九星公司的《新路》(1934)以及联华公司出品的《出路》(1933)和《大路》(1934)等,而且更出现了一批在题材上受到《生路》影响的影片。当然,这里所谓题材上的影响并不是指中国电影人照搬《生路》的情节设计,而是指一种基于本土化意义上的借鉴。中苏两国的国情和文化不同,直接模仿苏联电影的情节无疑会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郑正秋就说过:“中国的环境,决不会一时就适用苏联的作品,所以整个的搬将过来,未必会成功,而且难免要失败的,假使研究之下,心领神会于它的社会建设,变而通之,应用到自己的作品里去,能够用得进多少就用多少,我想至少限度是可以有利于中国的生产运动的。”㊷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一些电影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向以《生路》为代表的苏联电影取经和学习。从题材上看,程步高导演的《到西北去》就多少受到《生路》的影响。该片讲述了一位青年工程师顾策(龚稼农饰)响应政府“开发西北”的号召到西北参加建设,最终冲破当地官吏与劣绅的重重阻挠,带领乡民兴修水利的故事。抛开国民政府借助电影推动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诉求,我们不难发现,该片的创作明显存在学习《生路》的痕迹。作为该片的出品方,明星公司好像生怕观众发现不了这一点,其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宣称:“这是中国第一部鼓吹建设的影片,其意义的伟大,正如苏联五年计划中的《生路》一样。”㊸孙瑜导演的《大路》同样可以看出《生路》的影响④。仔细比对会发现,《大路》和《生路》在情节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在《生路》中流浪儿们要修建一条连接工厂和城市的铁路,在《大路》中六位城市失业青年要筑成一条抗敌的军用公路;《生路》中没有绝对的主人公,《大路》同样刻画了六位青年群像;在《生路》的结尾,英雄穆斯塔法在通车典礼前夕悲壮地死去,在《大路》的结尾,公路终于筑成,但六位青年却在敌机的轰炸中壮烈牺牲……
当然,要进一步探讨《生路》在题材上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就不能不提到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1936)。在拍摄这部同样以城市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时,蔡楚生一方面从《生路》中获得了大量的灵感,另一方面又不愿撇开中国的社会现实而在银幕上为流浪儿们建造一个乌托邦㊺。因此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尽管不时可以看到《生路》的影子,但又不得不承认二者有很大的不同:苏联的流浪儿经过改造后最终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而中国的小三子们则只能在畸形的都市里继续成为“迷途的羔羊”;《生路》的调子是昂扬的,《迷途的羔羊》则在喜剧的外衣下呈现出一抹悲剧的底色。从时人的评价来看,蔡楚生这种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借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有影评人指出:“这部片子的产生,无疑地是在《生路》的影响之下的,导演的手法也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生路》的模仿,它是中国的产物,所以它的内容也是中国的内容……”㊻
《生路》在电影技巧或曰“新的创作方法”上亦对当时的中国左翼电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技巧”首先是指苏联电影那种粗犷有力的银幕构图与摄影风格。《生路》中大量的特写镜头、独特的拍摄角度以及对比度强烈的布光所产生的那种激昂有力的美学,确实令当时的中国电影人耳目一新。这种与好莱坞柔和、流畅的银幕美学迥然不同的电影美学,被左翼电影人称作“苏联镜头”或“罗宋镜头”㊼,并被他们借鉴到自己的电影创作中。如时人在评价郑应时导演的《春潮》时指出,该片男主演高占非“有些劳工阶级化,在许多场面中,他能够描写成一个时代性的人物,并且上下连贯一气,我见了他的表情,好像在苏联出品《生路》《金山》中所见一般”㊽。如果再次对比一下孙瑜导演的《大路》和艾克导演的《生路》,就会发现,前者在银幕美学上同样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这一点只要对照一下《大路》中众人筑路的场景和《生路》中流浪儿修建铁路的镜头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电影创作者在学习苏联的银幕构图与摄影技巧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时人在评价吴印咸的摄影技巧时便指出,他的那种“偏重于厚、有力、健美”的风格乃属于苏联一脉㊾。

图3 《生路》中流浪儿修建铁路的场景

图4 《大路》中的筑路场景
其次,《生路》还在蒙太奇技巧方面给中国左翼电影人带来深刻的启示。早在《生路》在华上映前,来自苏联的蒙太奇理论就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与电影方法令左翼电影人异常着迷。然而,正如笔者在此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由于概念的陌生性和异质性,“蒙太奇”一词在中国从一开始就笼罩着一层神秘感㊿。《生路》的到来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电影人的焦虑,并成为他们学习蒙太奇技巧的课堂。洪深和郑伯奇曾说过,这部影片中的“新的技巧”“第一便是Montage的特异。在这里Montage简直超越技巧的范围,而突入到故事的本身了”。《生路》中大量的节奏蒙太奇、抒情蒙太奇和对比蒙太奇的段落被当时的左翼电影人所借鉴,成为他们用以制造影片节奏、进行抒情、揭示现实和表达阶级意识的手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生路》里的抓捕流浪儿以及科尔卡(流浪儿中的另一位领袖)的母亲被小流氓杀害等场景中,那种利用大量短镜头的加速和累积以产生强烈感官冲击的节奏蒙太奇,在30年代的左翼电影中很常见。左翼电影人借鉴这种纷繁破碎的镜头剪辑技巧,用以表现半殖民地上海的异质性。再比如《生路》中有一个为人称道的蒙太奇段落,是将穆斯塔法初次在工厂割皮制靴的镜头和他此前行窃时割破一位妇女的皮大衣的镜头剪辑在一起。这种利用前后两个镜头在形式上的相似和内容上的反差以制造强烈冲击性的蒙太奇,亦在30年代的左翼电影中屡屡出现。在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女主人公韦明和她的追求者一起跳舞时,影片突然将舞池中的脚部特写和街头劳动者的脚部特写剪接在一起,由于这两个镜头均是通过一个圆形的表框来呈现的,因此便产生了上述《生路》中那种特有的艺术效果。进一步而言,在30年代的左翼电影中,蒙太奇不仅仅被当作是一种技巧,而且还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融入了左翼电影人的创作观念中。有学者指出,由于强调镜头内与场景之间冲突的蒙太奇与左翼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某种同构关系,30年代的左翼电影人大都能够以蒙太奇思维构建其叙述,并将阶级冲突、贫富对立等话语缝合进电影这一通俗化的娱乐形式中。
作为一部探索性的有声电影,《生路》对中国早期有声电影更是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中国早期有声电影受制于落后的录音技术,尚不能做到全部片上发声,如何让声音元素超越自然复制而成为影片表意的一部分,就成为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这方面,《生路》在声画关系上的探索给中国电影人以很大的影响,其利用声画之间的分离与对位以产生强烈蒙太奇效果的艺术实践,被当时的中国电影艺术家视作好莱坞“对白片”(talkie)之外的一种可取的替代性方案。夏衍指出:“(《生路》)在技术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位性录音’的成功。这是对一切欧美有声影片认为唯一录音方式的‘同时性’录音的反叛。在这声片里面,有许多画面不一定和音响一致,可是在这种相互克制的中间,却能对观察者给予一种融然的理解……”苏联电影人所倡导的声画分离或对位的方法实际上是要求将声画关系视作蒙太奇的一种自然延伸,这种观念被当时的中国电影艺术家接受,并被广泛应用于中国本土有声电影的实践中。值得注意的是,《生路》对人物对白的谨慎态度以及对自然环境音响的创造性运用,亦给中国电影人带来了启悟。在苏联电影及其理论的影响下,当时的中国电影人大都将过多的对话视作一种舞台化倾向,而对使用自然音响则持欢迎的态度,因其不会破坏默片时代就已经成熟的银幕美学。在许多左翼电影中,音响不仅被用来塑造银幕空间的真实感,更成为影片蒙太奇叙事的一部分。典型的如《桃李劫》的结尾,当男主人公陶建平被执行枪决的时候,沉重的脚步声和铁链声、临刑时的枪声以及画外的《毕业歌》声,相互交织,产生了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如果将这个段落与《生路》结尾穆斯塔法被杀害那一场戏的音响设计(将轨道车摩擦轨道所发出的金属噪声、水塘中低沉的蛙鸣声、凶手破坏铁轨时金属工具所发出的轻微的叮当声以及穆斯塔法由远及近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动人的魅力)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推测《桃李劫》某种程度上是借鉴了《生路》的。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影坛对苏联有声电影的认知实际上包含了很大程度的理想化成分。事实上,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苏联有声电影在当时都难言是先进的。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初断绝了进口西方的电影技术和胶片,这导致苏联电影迟至1935年才基本完成了从无声时代向有声时代的过渡。在艺术上,苏联电影工作者对声画同步的拒绝也并非完全出于美学上的考虑,而更多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许多人认为好莱坞的声画同步对人的知觉和感官的强调意味着电影退回到了革命之前的资产阶级艺术,而苏联电影的任务是使声音成为电影中独立的、具有表现性的材料⑤。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苏联电影人将音响和音乐放在远比人声更重要的位置,其结果是苏联最早的一批有声电影大都难言成功。回到历史语境中我们发现,中国影坛当时对苏联有声电影技艺的崇拜不得不说是一种信息错位。在《生路》这面“他者之镜”面前,中国电影人与其说是发现了“他者”,还不如说是发现了自己的时代关切。
在新的题材与“新的创作方法”之外,中国电影人亦从《生路》中学到了“新的创作态度”。首先,《生路》带来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观念。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那种将摄影机对准社会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尽管我们在上文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必须承认这也是该片之所以打动中国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在描写现实的同时不忘对未来的允诺以及乐观向上的精神,就像夏衍在看完影片后所惊叹的:“新的代替了旧的,健全而明快的情感,代替了颓唐而伤感的情调……建设和崩溃、朝气和衰老、健康和衰弱、欢呼和悲叹、泼辣和沉滞、愉快和伤感,这是何等明白而尖锐的对比!”《生路》亦启发中国电影艺术家去思考什么是真实以及电影应该呈现什么样的真实。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电影艺术家逐渐认识到:“所谓真实,不是作者死模仿着现实去呆呆描写,而是在使观众心中生出逼真的情感。”电影不仅应该深刻描写现实,还应该“给没落的中国人一种鼓舞的希望”。受这一观念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从整体上一扫此前主导中国银幕的柔弱、感伤的鸳鸯蝴蝶派美学,而是在揭示现实和批判现实的同时呈现出一种高亢、雄浑的时代强音。
其次,《生路》还启发了中国电影艺术家将群众/大众作为银幕主体的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些看过《战舰波将金号》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对爱森斯坦“用群众来做主体”的做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有影评人观察到,中国电影长期“不会应用群众”,“多数导演只注重主角的戏,而没有注意群众的表演动作”,更不用说将群众作为银幕的主体。从大的时代语境来看,群众作为一种主体在中国银幕上的登场与30年代左翼思潮的兴起是分不开的,但苏联电影所带来的影响无论如何亦不能被低估。《生路》那种将个体成长缝合进国家建设之中的叙事策略,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改造成对整个社会有用的劳动者的主题,塑造英雄化的群众主体的银幕美学,在长期受到好莱坞明星制影响的中国电影人那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他们不仅惊呼“激动我们心灵的,是集团的生活的力量,是集团的生活的意志”,而且更以此来反思自己的创作。沈端先(夏衍)在回应影评人批评其编剧的《狂流》没有表现出“群众的力量”时大胆承认说:“当我看完了《生路》那几幕有力的表现之后,真使我们觉到这片子里面的所谓群众力量的贫弱得可怜。”受到《生路》以及其后到来的《重逢》《金山》等苏联电影的影响,一些左翼电影人亦开始探索如何将“群众的力量”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在《大路》《十字街头》等影片中,“群戏”作为一种新的表演形式被用来呈现“集团的生活”,一批健康向上、充满生命力的底层大众的形象开始出现在中国银幕上。彭丽君(Laikwan Pang)在分析左翼电影中的男性形象时曾指出,与“五四”文学中那些感伤的、个人主义的形象不同,左翼电影中的男性形象往往更具男性气质,他们也被鼓励为男性化的集体事业献身。即使在大部分仍然以个体作为主人公的影片中,我们发现浪漫的个人主义也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一种负面的价值,个体只有投身革命的集体或群众洪流中才能找到出路。
至此,我们主要论述了《生路》在题材、技巧和艺术观念上带给中国电影的启发。不过,假若我们将短期影响与长远影响、影坛内与影坛外的影响一起涵括进来的话,《生路》在中国的实际影响情况可能要远比我们的论述复杂得多。不同于即刻可见的短期影响,长期影响可能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发酵和显现,而《生路》在当时倾向进步的青年观众心中所种下的革命火种更是很难单纯地进行量化。
四、历史的回响
20世纪4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的影响力在中国急速上升,《生路》开始进入各种公开的论述和私人化的回忆之中,并继续在中国产生持久的历史回响。在1940年出版的《中苏文化》“苏联戏剧电影专号”上,阳翰笙、郑伯奇、史东山、司马森、葛一虹等人不仅继续高度评价《生路》的艺术成就,而且以历史亲历者的姿态总结了近十年来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成长的影响与启示。1941年,《生路》在大后方的重映进一步唤起了部分观众的历史记忆,如向锦江评价说:“自《生路》第一次在我国开映后,对于我们电影与戏剧影响至巨,稍远的《迷途的羔羊》,到最近的《乐园进行曲》,剧作者都是从《生路》中取得一些构成作品的因素的。”不过,在紧张的战时语境下,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显然已经发生了转移,《生路》的重映除了引起一部分儿童保育工作者的注意之外,并没有在大后方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
《生路》在中国的故事此后依然在继续。继夏衍20世纪30年代将《生路》的分镜头脚本翻译成中文后,《生路》的文学剧本也在40年代末由阮潜翻译成中文并附录在其编写的《电影编导简论》一书的结尾。在国内外众多的佳片杰作中,编写者为何选择《生路》作为新中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学习的对象?这显然是与该片在中国所留下的历史记忆和1949年前后的历史语境分不开的。阮潜这样说明道:“本书附录了一个有声电影的分场剧本《生路》,这是苏联第一部有声电影。很多年前,曾到中国放映过,但从没见过该片剧本的介绍,因为这是一部苏联革命后初期的电影作品,在内容上和我们今日的生活颇多接近,同时从一个文学剧本说来,对于如何写作电影剧的技巧有启示,可供欲从事电影编剧者的参考和揣摩。”很显然,阮潜认为《生路》所反映的苏联革命初期的社会问题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十分相似,因此相信中国电影人可以从这部电影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除附录的文学剧本外,该书还几乎逐段分析了《生路》的剧本结构与电影化技巧。如果再联系到《电影编导简论》是阮潜任职东北电影厂期间为新入行的电影工作者编写的一本入门教科书,那么《生路》对新中国电影的影响恐怕就更加不容小觑。
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生路》频繁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电影界权威人士的回忆录中。由于这些回忆文章的撰写者正好是《生路》当年在中国上映时的第一批观众,他们的文字因此不仅成为时代的见证,更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历史细节,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苏联电影在中国早期的接受与影响情况。如陈荒煤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就讲述了当年只有19岁的自己和吕骥、张庚等人在武汉观看《生路》后是何等的“兴奋若狂”,他们三人还“化名写了许多评论文章,热情歌颂这部第一次看到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电影”。司徒慧敏在他晚年文章中亦回忆道:“在有声电影《生路》中,导演尼古拉·埃克(即艾克——引者注)既能很好地掌握声音和画面的对位法运用,又能表现声音与画面同步的很强烈的真实感。苏联有声电影一上场就吸引了我。它把我从门外汉或半门外汉引入了电影的大门。”他还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利用熟人关系,在电影散场后和夏衍到上海大戏院用倒片机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地学习《生路》《金山》等苏联电影的场景。《中国电影》杂志在1957年更是以两期的篇幅邀请电影界专家畅谈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启示,蔡楚生、张骏祥、钟敬之、赵慧深、白杨、舒绣文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了《生路》当初带给他们的强烈震撼。如钟敬之回忆道:《生路》等“许多苏联有价值的影片,对青年的我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以至对我以后树立新的人生观也具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那些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亲历者,如夏衍、阳翰笙、于伶、柯灵、凌鹤等,也大都通过各种各样的纪念和回忆文章提到了《生路》当年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些文章后来悉数作为党史资料被收入《中国左翼电影运动》(1993)一书。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认为历史具有“三调”,即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并指出作为神话的历史为满足当下现实的需要总是有意识地提取某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信息。本文认为,《生路》之所以不断地出现在中国左翼电影的历史叙述中也应作如是观。《生路》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20世纪上半叶中苏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而且还在于它是左翼电影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到学术史的脉络,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十七年”时期,还是1980年之后的“新时期”,左翼电影的身份都被不同程度地加以重新解读。如果说在前一个时期,当新政权沿着“解放区文艺”到“社会主义文艺”的轨迹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时,诞生于上海十里洋场的左翼电影难免与这一历史叙述有些游离,他们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才能跟上新时代的节奏,那么在“新时期”,当改革开放催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学术界主流时,左翼电影不能不面临一定范围内的被质疑乃至被忽视。在此背景下,那些来自“左翼十年”的亲历者的反复言说,尽管表面上看他们的做法透露出一种充满焦虑的自我辩护与自我建构,但更为真切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成为了红色传统的有力坚守者。从另一个角度看,《生路》之所以被铭刻进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中,还在于它开启了20世纪中国电影以苏联电影为师的序幕。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电影一步步向苏联电影师法,直至在电影体制、电影理论、银幕美学、表演体系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接受了苏联电影的影响。而当后世追溯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轨迹时,自然需要不断地回到《生路》这一历史的原点。
结 语
在《生路》公映后不久出版的《上海周报》上,一位观众用颇有气势的排比句写下了他对该片的观感:“《生路》是苏俄电影的大成功!《生路》是欧美电影界的当头棒!《生路》是弱小民族的兴奋剂!”忽视这句话中的感性因素,其显然表明《生路》在中国的巨大反响包含了许多非电影的因素。左翼影评人的大力鼓吹尽管有着宣传左翼意识形态的动机,但却直接提升了《生路》在电影市场上的能见度与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强烈的反帝情绪亦间接地创造了《生路》在中国的际遇。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再加上“辱华片”风波,使得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欧美电影在中国的形象开始动摇。另外,《生路》的题材和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苏联政府对流浪儿童的人道主义救助令一部分观众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本国儿童的命运。更进一步,如有论者所言,当一个国家和社会存在诸多矛盾,心怀不满的成员在接受“异域”或“他者”文化时,“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域’,把‘异域’构造为自己的乌托邦”。显而易见,中国社会对《生路》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想象,亦包含着一个“弱小民族”的特殊心理。
由于种种机缘,《生路》在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和历史记忆确实可能更持久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孤立地来考察这部影片。笔者认为,我们最好将《生路》作为20世纪中国电影整体性接受苏联电影影响的一环来看待。与其后在中国上映的其他苏联电影一道,它们不仅成为了几代中国人观影的历史记忆,更是对中国电影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20世纪40年代以后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跃升,《生路》中那种塑造群众主体和“新人”想象的影像机制以及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银幕上。
③ 张伟:《前尘影事:中国早期电影的另类扫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211页。
④ 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编:《苏联电影史纲》第1卷,龚逸霄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342—347页。
⑤ 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徐昭、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⑥ Jay Leyda, Kino: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Fil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84.
⑦ 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194—195页。
⑧⑤ Cf.Lilya Kaganovsky,“Learning to Speak Soviet: Soviet Cinema and the Coming of Sound”, in Birgit Beumers(ed.), A Companion to Russian Cinema, Malden: Wiley Blackwell, 2016, pp.296-302, pp.296-302.
⑨ 这期间唯一的例外是普多夫金导演的《成吉思汗的后代》,该片曾于1931年4月4日在上海百星大戏院上映。
⑩ 参见《国民政府禁映苏联革命影片的令文》(193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378页。
⑪ 凌鹤:《评〈生路〉》,《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2月13日。
⑫ 参见《晨报》1933年2月16日广告。
⑭⑲㊲ 王启煦:《〈生路〉评二》,《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2月16日。
⑮㊵ 参见王乾白、史东山等:《中国电影从业员的〈生路〉观后感》,《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2月16—17日。
⑯ 参见洪深、席耐芳:《〈生路〉详评》。
⑰ 参见闪光、雷鞭:《苏俄电影界第一炮,〈生路〉之总检讨》,《电声日报》1933年2月17—18日。
⑱ 尘无:《〈生路〉的尾声——关于〈生路〉的批评》,出处不详。据《中国左翼电影》(1993)与《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1994)两本史料集的注解,该文刊登于1933年2月17日的《晨报》“每日电影”副刊,但笔者查阅当日报纸并未发现此文。
⑳ 鲤庭:《看〈生路〉》,《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2月13日。
㉑ 参见尘无:《〈生路〉的尾声——关于〈生路〉的批评》。
㉒ 赵瑶:《苏俄的〈金山〉》,《大美晚报》“银花”1933年9月5日。
㉓ 参见胡予谷:《看了〈生路〉后关于上海大戏院的几点》,《电声日报》1933年2月17日。
㉔ 程步高:《影坛忆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199页。
㉕ 鲁迅在1933年2月19日所写的日记,刘思平、邢祖文选编:《鲁迅与电影(资料汇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㉖ 参见杨小佛口述、朱玖琳撰稿:《杨小佛口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1—72页。
㉗ 参见冰:《〈生路〉为什么不准在租界内开映?》,《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5月5日。
㉘ 参见丁谦平:《有声电影摄影台本〈生路〉》,《明星月报》第1卷第2—4期,1933年。
㉙ 参见包时:《看了〈重逢〉之后》,《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2月27日。
㉚ 《申报》1937年5月7日广告。
㉛ 参见《申报》1939年5月5日广告。
㉜ 《申报》1933年7月7日广告。
㉝ 参见夏衍《左翼十年》和于伶《回忆“剧联”话影评》,广播电影电视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选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784、935页。
㉞ 上海街头当时有许多以乞讨和偷窃为生的流浪儿,上海人称之为“小瘪三”。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以及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对此均有生动的反映。
㉟ 参见OK:《一个镜头》,《联华画报》第1卷第25期,1933年。
㊱ 参见陈伯吹:《生路与死路》,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15—116页。
㊷ 郑正秋:《如何走上前进之路》,《明星》第1卷第1期,1933年。
㊸ 《申报》1934年10月1日广告。
㊹ 彭丽君认为,《大路》受到美国电影《大阅兵》(The Big Parade,1925)和《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1930)的影响,显然她并没有看过《生路》。Cf.Laikwan Pang, Building A New China in Cinema: The Chinese Left-wing Cinema Movement, 1932-1937,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p.102-103.
㊺ 参见蔡楚生:《〈迷途的羔羊〉杂谈》,《联华画报》第8卷第1期,1936年。
㊻ 示:《中国的〈生路〉——看了〈迷途的羔羊〉试演以后》,《读书生活》第4卷第6期,1936年。
㊼ 参见田汉:《怎样从苏联戏剧电影取得改造我们艺术文化的借鉴》,《中苏文化》第7卷4期,1940年;宣影:《访古中国之歌导演人费穆先生》,《银銮殿》1941年4月创刊号。
㊽ 与之:《〈春潮〉之我见》,《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10月33日。
㊾ 参见罗曼:《论吴印咸君的摄影——观〈生死同心〉后》,《大晚报》“剪影”1936年12月8日。
㊿ 参见贾斌武:《现代电影观念的启蒙——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坛对蒙太奇理论的译介与探索》,《文艺研究》2018年第3期。
⑥ 陈荒媒:《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陈荒煤文集》第2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