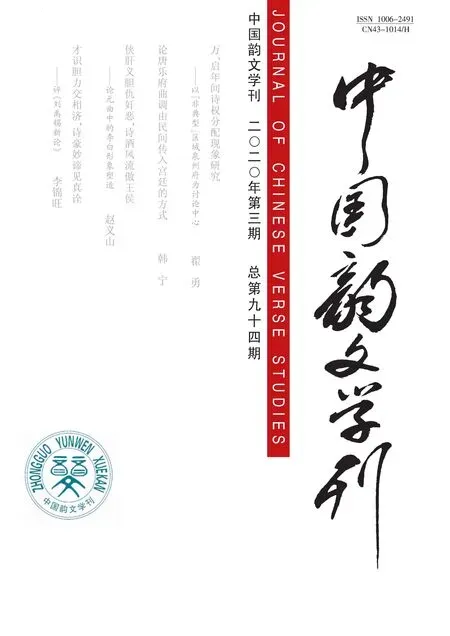歌功颂德之外:西晋奉命诗文的历史认识价值举隅
来森华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西晋皇室成员基本上都不具文才,但是出于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出身自儒家大族的他们喜好利用尊位频繁主事赋诗为主的文学活动,当时的职官制度更为其保证了较为稳定的作者队伍(1)西晋常规设有“太常博士”“秘书郎”“著作郎”等职,掌其职者经常参与皇帝组织的文学活动。另,据《晋书·职官志》记载,咸宁四年始置太子中舍人四人,“以舍人才学美者为之,与中庶子共掌文翰”;又载:“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详参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43页)故太子、藩王也常有令侍从文士赋诗、作赋、作颂之举。。基于此,西晋时期产生了不少应制、应令与应教诗文。不可否认,这些文学活动中大量产生的奉命诗文歌功颂德动机明显,不论内容还是体式,学界对其评价普遍不高。但是也应该客观地看到,这类诗文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个别篇章具有历史认识价值,对当时的政治事件、社会面貌等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可以起到证史或补史作用。此不揣谫陋,以具体文本为例,略做探析。
一 潘尼《后园颂》
此颂通篇用四言作成,双句句尾押韵且多有换韵,尤其后半部分每十二句同韵。从文体形态进行考察,与西晋时期应诏而做的数首四言多章颂体诗实无二致,堪称时人挚虞《文章流别论》中所谓“诗之美者也”[1](P1905)。便于深入讨论起见,兹节录相关文本于下:
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从皇以游。长筵远布,广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岩岩峻岳,汤汤玄流。翔鸟鼓翼,游鱼载浮。明明天子,肃肃庶官。文士济济,武夫桓桓。讲艺华林,肆射后园。威仪既具,弓矢斯闲。恂恂谦德,穆穆圣颜。赐以宴饮,诏以话言。黍稷既登,货财既丰。仁风潜运,皇化弥隆。征夫释甲,战士罢戎。遐夷慕义,绝域望风。无或慢易,在始虑终。无或安逸,在盈思冲。[1](P2002)
依“赐以宴饮,诏以话言”两句可知系应诏作颂。“征夫释甲,战士罢戎”两句加之颂文上半部分亦有“华夏既宁,八荒静谧”之辞,可以判定这篇应诏之作产生于晋武帝平吴之后。因为平吴当年冬武帝下诏罢州郡兵,“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2](P2575)。另外,结合潘尼仕历可以更进一步推定此颂作时。《晋书》载:“初应州辟,后以父老,辞位致养。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历高陆令、淮南王允镇东参军。”[3](P1510)太康十年(289)司马允徙封淮南王并统军事,潘尼离洛入其幕府,加之前面高陆令之职掌,此颂唯有作于其在太康中任太常博士任上之可能。
“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从皇以游”四句道出天下一统后时人意欲放松之心态以及君臣畅游宴饮之旨趣。“黍稷既登,货财既丰”“遐夷慕义,绝域望风”两处一内一外描摹的恰是“太康盛世”的社会画卷。就前者而言晋宋时人孔琳之在《废钱用谷帛议》中也如是描述:“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1](P2584)当时民间更是有“天下无穷人”的谚语流播。而就后者亦可从史家“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的表述中找到印证[3](P1071)。关于“远夷宾服”的情况,《晋书·武帝纪》亦载之甚详,兹以一简表览之:
据表1,不难看出潘尼“遐夷慕义,绝域望风”的概括具有历史依据,而绝非妄言。

表1 平吴后武帝朝外交事件时间表
除此之外,颂文结尾“无或慢易,在始虑终。无或安逸,在盈思冲”四句,表明当时的朝臣已经认识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2)亲历平吴战争的杜预亦有此见,据《资治通鉴》卷八一《晋纪三》记载:“杜预还襄阳,以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乃勤于讲武,申严戍守。”(详参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573页),可谓对当下政治生态的敏锐体悟与自觉反思。晋武帝平吴后一改之前勤于朝政的作风,转而开始注重耳目之娱,“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3](P80),骄泰之心日渐膨胀,奢靡之行乐此不疲。此颂加之太常张华作于同一时期的《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中对后园游宴盛况的描写,从中即可窥其“耽于游宴”之一斑。而晋武帝以上行为更是为后世所诟病,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对其平吴后的行为如是评价:“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以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3](P81)同样,太宗贤妃徐惠在《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中认为晋武帝后期 “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4](P980),苏辙也以“苟安而无远虑”评价武帝之为人[5](P1245),明显在批评晋武帝后期没有居安思危的政治远见。
综上,抛开对武帝功业的颂赞与游宴盛况的铺叙,潘尼在此篇应制之颂中对“太康盛世”社会画卷的经典描摹以及应该处安虑危的谆谆告诫,均为后世的史家记载或者政治家评价这段历史之先声。[6]
二 王赞《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诗》等
据《晋书》记载,太康十年(289)发生了一次涉及王室成员的徙封,其中徙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3](P79),其政治目的在于“镇守要害,以强帝室”[3](P81)。当时的太子司马衷深陷废与立的政治舆论旋涡之中,正是在如此关键的政治节点上祖饯即将出镇的司马玮、司马允二王,并令时任太子舍人的王赞赋诗。诗云:
于明圣晋,仰统天绪。
易以明险,简以识阻。
研彼群虑,俾侯授土。
郁郁二王,祗承皇命。
睹离鉴亲,观礼知盛。
皇储降会,延于公姓。
瞻彼行役,并憩同林。
分涂殊轨,靡不回心。[7](P761)
诗中前四句基于以往奉命诗的套路颂扬天命归晋,而接下来“研彼群虑,俾侯授土。郁郁二王,祗承皇命”四句有史可依,《晋书》载:“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3](P80-81)紧接着四句指出祖饯的背景与宴请对象,而最后“瞻彼行役,并憩同林。分涂殊轨,靡不回心”四句安抚、团结之意不言而喻。
司马衷作为皇储宴请即将出镇的族亲,显然是在朝廷的诏令后为改变自身不利局面而做的努力,祖饯宴会上令侍从文人赋诗又起到了政治关系的润滑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其做太子期间不止一次依托赋诗活动协和族亲关系,如王赞《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诗》中“乐此棠棣,其甘如荠”两句巧取《诗》义以强化兄弟和睦之情[7](P760),又如王赞《三月三日诗》中希望宴请的姻族“右载元首,左光储辅”从而使得晋“大祚无穷,天地为寿”[7](P760)。很明显,三次赋诗所呈现出的政治目的基本一致,那就是争取其他政治势力的支持。可是,检视今之所见史书,服膺东宫期间的司马衷不但由于资质平平而未彰帝王之潜能,而且在朝臣不绝于朝的废弃之声中也未见其有进取之心,就连武帝晚年的所谓能力考察,也是在太子妃贾南风的安排下抄录张泓事先草拟的“答卷”以应付了事。综上,王氏三诗无疑有补史之功,可以丰富司马衷的太子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上举《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诗》中的宴请对象亦为司马玮,因为咸宁三年(277)八月司马玮被立为始平王,至太康十年(289)徙封楚王,其间再无改封之举。(3)据《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三年正月曾立司马裕为始平王,然月内即薨,加之王赞入东宫在太康中,故宴请对象不可能是司马裕。两次宴请同一皇室成员并令侍从文士赋诗,据此可略窥司马衷作皇储时主动与“少年果锐”的异母弟交好。这场政治交好,更为不久就爆发的后宫之乱与八王之乱埋下了一颗暗雷。永平元年(291)二月,“镇南将军楚王玮、镇东将军淮南王允来朝”[3](P90)。藩王入京的目的何在呢?据《晋书·杨骏列传》记载,司马玮是得到贾后消息为讨伐外戚杨骏而入朝,“肇报楚王玮,玮然之,于是求入朝”[3](P1179)。入朝之后在贾后的精心设计下先后参与了诛杀杨骏与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的一系列政治角斗,最终又被贾后矫诏除去。纵观这场政乱,司马玮虽有作乱之举,但并无不臣之心,其所参与的争斗并未直接危及惠帝,本欲清君侧,终了落了个卸磨杀驴的下场。
简言之,通过对《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诗》为代表的王赞的几首应令诗从内在呈现和外部生成两方面进行考察,足以识见晋惠帝做太子期间主动团结与拉拢族亲,尤其是与司马玮交好,而这方面正好可补史籍之阙载,从而丰富其政治与历史形象。
三 潘岳《关中诗》
潘岳《关中诗》通篇四言,凡十六章,萧统《文选》选入“献诗”一类。根据唐臣注解,其为应诏而作,如李周翰注曰:“晋惠帝元康六年,氐贼齐万年与杨茂于关中反乱,人多疲敝,既定,帝命诸臣作《关中诗》。”(4)本节所引《文选》唐臣诸注,俱见萧统编、六臣注《文选》卷二〇“献诗”,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6~369页。不再一一赘注。李善注亦云:“岳上诗《表》曰:‘诏臣作《关中诗》,辄奉诏竭愚作诗一篇。’”依唐修《晋书》载:“九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伐氐,战于中亭,大破之,获齐万年。”[3](P95)综上,此首应制诗当作于元康九年(299)。
就内容而言,除去首章称颂晋祚稳固、末章赞扬惠帝体恤百姓以及第三章为尊者讳而对前后平叛不利的赵王司马伦与梁王司马肜亦有颂言外,中间部分基本上线索清晰地交代了平叛过程以及当时的战地艰苦条件等,可以印证甚至补充史书记载。
其一,参加这次平叛的众将事迹在诗中均有提及。如第三章有言:“翘翘赵王,请徒三万。朝议惟疑,未逞斯愿。桓桓梁征,高牙乃建。旗盖相望,偏师作援。”第四章云:“谁其继之?夏侯卿士。惟系惟处,别营棋跱。”第六章云:“周殉师令,身膏氐斧。人之云亡,贞节克举。卢播违命,投畀朔土。为法受恶,谁谓荼苦。”第九章云:“命彼上谷,指日遄逝。亲奉成规,稜威遐厉。首陷中亭,扬声万计。”(5)此诗详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7~629页。下文所引不再赘注。对参加这次平叛战争的司马伦、司马肜、夏侯骏、解系、周处、卢播、孟观等人事迹均有交代,其中“上谷”即指上谷郡公孟观。以上诸人战中事迹,参以唐修《晋书》多与之合,唯缺司马伦“请徒三万”而朝议不许、卢播所违何命以至于贬至北地之事。《文选》李善注引朱凤《晋书》云:“伦请三万人往平齐万年,朝议不许。”刘良注亦云:“赵王,名伦。请兵三万往平氐、羌,朝议疑,不遣,故此愿不逞。”可知,齐万年叛乱后,时任征西大将军的赵王司马伦曾有平叛之心而请求增兵,但是朝议不许。而至于司马伦被召还的缘由,史载略有不同,《文选》李善注引傅畅《晋诸公赞》云:“伦诛羌大酋数十人,胡遂反。朝议召伦还。”唐修《晋书·赵王伦列传》亦言:“伦刑赏失中,氐、羌反叛,征还京师。”[3](P1598)《解系列传》却载:“会氐、羌叛,与征西将军赵王伦讨之。伦信用佞人孙秀,与系争军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挠,而召伦还。”[3](P1631-1632)可知在召还之前,司马伦亦曾参与前期战事,故有请求增兵以继续征讨之举。卢播战时之举,《梁王肜列传》云:“肜与处有隙,促令进军而绝其后,播又不救之,故处见害。”[3](P1128)《周处列传》亦载:“弦绝矢尽,播、系不救。”[3](P1571)又,《文选》李善注引王隐《晋书》云:“卢播诈论功,免为庶人,徙北平。”吕向注亦有此说。综合二说,诗中概括的卢播之事甚明。
其二,诗中陈述了战前、战时的一些信息,其具有补史之缺的价值却极其容易被忽略。如第一章最后有“微火不戒,延我宝库”两句,第二章又有“虞我国眚,窥我利器”之言,据唐修《晋书》记载,齐万年叛乱上一年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3](P93)。在潘岳看来此为各族反叛提供了契机,可谓灼见,因为时人亦有此识,据《宋书·五行志》载:“张华、阎纂皆曰,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矣。”[8](P934)又如第二章言“岳牧虑殊,威怀理二。将无专策,兵不素肄”,第五章言“夫岂无谋,戎士承平。守有完郛,战无全兵。锋交卒奔,孰免孟明”,指出对于如何处理关中叛乱之事大臣中有讨伐和安抚两种意见,同时又对当时晋室军队的战斗力有客观叙述,承平日久而经不起战斗的考验;再如第十五章最后两句言“绛阳之粟,浮于渭滨”,唐修《晋书》只是记载元康八年(298)正月,“诏发仓廪,振雍州饥人”[3](P95),并未明言是绛阳之粮,据此诗可补史。
其三,诗中还在表达悲悯之余描绘出当地黎民百姓遭受战争、饥饿、疫疠等疾苦。如第七章曰:“哀此黎元,无罪无辜。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晋民,化为狄俘。”第十五章曰:“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所叙述的苦难是当时战地百姓的真实写照。据唐修《晋书》记载,元康六年(296)十一月,“关中饥,大疫”[3](P94);七年(297)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3](P94)。天灾人祸并存,饥饿疫疠交织,民生凋敝,疾苦尽显。
其四,诗中在战后诸事的处理方法上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其中个别细节的呈现不载于今见史籍。在第十、十一两章,针对有司对孟观虚报战果一事的态度,潘岳认为孟观虽有过但解雍城之围“功亦不测”,如第十一章言“雍门不启,陈汧危偪。观遂虎奋,感恩输力。重围克解,危城载色”,《文选》李善注引《晋中兴书》云:“观从中亭北出,何恽领二万人以继之,雍围解。”第十二、十三两章言及孟观、夏侯骏关于齐万年的最终下落各执一词之事,如第十二章有“曰纳其降,曰枭其首”两句,李善注引王隐《晋书》云:“初,夏侯骏上言斩氐帅齐万年。及孟观至,大战数十,生送万年。”诗中所言即此事。潘岳亦用“畴真可掩,孰伪可久”“既征尔辞,既蔽尔讼。当乃明实,否则证空。好爵既靡,显戮亦从。不见窦林,伏尸汉邦”数言表明应该据实查证、公正赏罚的立场,在其《上〈关中诗〉表》中也有“而死生异辞,必有诡谬,故引证喻,以惩不恪”这样相似的谏言[12](P1991)。而以上诸事,唐修《晋书》阙载,清人何焯即言:“观《晋书·孟观传》所载事甚略,此诗可补其阙。”[9](P666)
姑且不去深究潘岳较多笔墨地为孟观开脱及主张如实查证异辞是出于朝臣的公道良心还是其他深层次的政治立场或利益所驱,就产生于平叛背景下的潘岳《关中诗》对当时战前、战中、战后的相关情况尤其是战力、饥荒、疫情等的如实叙述观之,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诗史”价值。中国“诗史”传统源远流长,而以往的聚焦点多在名家名篇,应在更广阔的诗歌样式中寻绎其踪迹,丰富其内涵,挖掘其价值。
四 结语
基于以上三处个案分析,西晋时期的部分应制与应令诗文由于产生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之后或特定的政治生态之中,故在主流的歌功颂德之外对此又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而使其呈现出历史认识价值。这在方法论层面启示我们:其一,立足于客观细致的文本分析,对于文学性存在一定缺陷的作品应该本着尊重文本的态度,客观看待其他方面的价值,而非因为固有的文学史视角造成的刻板印象盲目地全盘否定,主观地不予置评。其二,历代学者虽然就史、文(诗)之别做出过不少立场坚定的论断,但是持文史汇通、文史融通、文史互鉴等学术主张者同样不乏其人,以史释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等研究方法更是被大力提倡与广泛运用。循此,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就不应该完全忽略那些具有史识价值的边缘性材料,而这些材料作为辅助和旁证往往又能证史或者补史之缺。前贤早有“六经皆史”之说,近来亦有时修提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主张还要涵盖尚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10]。这些论说成立与否之关键和前提,反映到微观层面,即要求分析的文本和探讨的对象客观具有史料及史识价值。合理利用好史学研究中的“旁证”,更有助于拨开历史迷雾,丰富历史画卷,甚至于廓清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