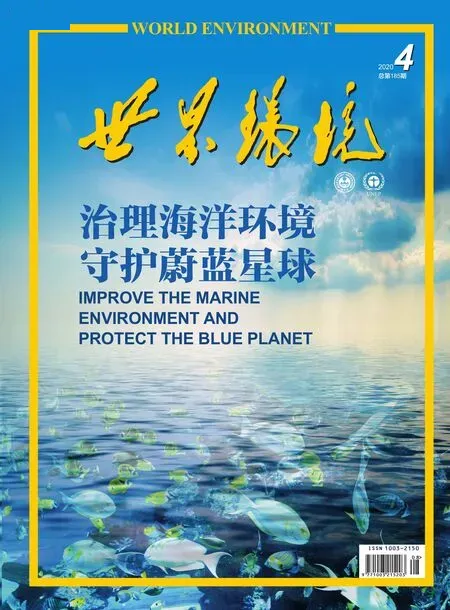建立公海“禁渔”保护区对全球渔业有什么影响?
■文 / 周薇

2019年6月,绿色和平拍摄的在北大西洋捕捞鲨鱼的作业渔船。 © Kajsa Sjölander / Greenpeace
渔业捕捞是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影响最大的人类活动,也是约占全球海洋面积2/3的公海(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上规模最大的开发活动,是公海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
公海渔业自1950年后迅速发展,目前已遍及至少48%的公海面积。与此同时,过度捕捞,破坏性的捕捞方式,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渔业等问题也被带到了这片“全球公地”,对公海生物和栖息地造成了严重威胁。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20年最新报告指出,公海渔业资源形势非常严峻,作为公海渔业主要捕捞对象之一的金枪鱼,有1/3的种群被过度捕捞。公海渔业捕捞每年造成数万只海鸟,大量的鲨鱼、海洋哺乳动物、海龟等意外死亡。底拖网对多处脆弱深海生态系统和那里特有的生物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加之气候变化、海水酸化、塑料污染等多重压力和累积影响,公海生物多样性正面临危机,亟须得到有效的保护。
科学证据表明,保护区在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强其应对累积影响的恢复力方面,是最有效的工具。保护区分为不同级别,保护力度越大,所带来的各种效益也越大。不允许任何开发或破坏性活动、并将其他人为影响最小化的“完全保护”级保护区,将产生很高的保护回报。

2013年7月,菲律宾阿波岛的绿海龟。 © Steve De Neef/Greenpeace
建立有效的保护区意味着将某些海域划为“禁捕区”,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有的公海渔业活动。公海渔业行业能否认可保护区的渔业效益,接纳这一措施,积极支持并参与保护区设计和建立的进程,对公海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渔业的未来都至关重要。
保护区能产生诸多不可替代的渔业效益
保护区的首要目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与渔业管理侧重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渔业资源的目的不同。保护区通过提供全面、综合的保护,能产生许多即使是非常好的渔业管理也无法提供的效益。比如,保护区内的大鱼不会被捕捞,在完全保护的区域内鱼类个体大小能增加至少28%。鱼类个体和年龄越大,产卵会越多、卵的存活率也越高,这一点随着体重增加会翻倍提高,例如,1条30公斤的雌性大西洋鳕鱼产下的卵比28条体重2公斤(总重56公斤)的雌鱼产的卵还多。
在完全保护的保护区内,鱼类生物量能得到显著提升,比未受保护海域高670%,比受到部分保护的海域高343%。区内丰富的渔业资源会补充到邻近海域,提高周边的渔业效益,在同样的捕捞投入下,保护区周边海域的渔获量比建立保护区之前高4倍。
保护区在提高海洋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恢复力方面也有重要效用,而气候变化也是渔业正在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FAO的预测表明,到21世纪末,如果温室气体排放没有显著减少,各国海洋渔业捕捞潜力将整体下降16%-25%,中国将下降9%-24%。
规划合理的保护区网络,将为物种适应气候变化做出的种群分布变化提供便利,例如为物种扩散提供廊道和歇息场所,为无法移动的物种提供庇护场所等。保护区还能够加强对食物链顶层捕食者的保护,提高种群数量,丰富遗传多样性等,这些都终将增强渔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完全保护的保护区还能防止其他人类活动(如采矿、噪声等)的破坏,使渔业部门的保护成果不受这些活动影响。基于这一优势,保护区还可以充当天然的实验室,研究不受人类活动干扰下的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渔业管理措施提供基础数据。

2012年11月,太平洋公海上,潜水员与巨大的金枪鱼围网。 © Alex Hoあord/Greenpeace
填补全球海洋保护的“空缺”,公海保护区正备受期待
虽然保护区的价值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公海保护区的面积比例还非常低,根据MPAtlas数据库,保护区仅占公海面积的1.2%,其中完全或高度的保护区仅占公海面积的0.8%。
对于未来应有多少公海被设为保护区,目前存在许多不同的倡议,包括应将50%、30%或10%的公海设为保护区等。各个倡议中,受期待最高、共识最强的 “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海洋”的目标,已经得到至少20个国家政府,科学界,环保人士和NGO的广泛支持。
虽然对目标的共识在不断提高,但目前仍然缺少在公海建立保护区的全球性法律机制,正在联合国磋商的“BBNJ”协定被寄望于创设这一机制。“BBNJ”协定指“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定的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2018年,该文书进入政府间会议谈判阶段,原定于2020年3月底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受新冠疫情影响,目前会议处于延期状态。
此外,“BBNJ”协定还被寄望于改善当前支离破碎的公海治理模式,补充和加强渔业、采矿、航运等现有各种部门性和区域性的协定、框架或机构的管理措施的效果,确保保护的连贯性和全面性。
公海保护区不会损害公海渔业,而且将使包括公海渔业在内的全球渔业受益
首先,渔业活动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贡献是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就业和生计,但研究表明,公海渔业在这些方面的贡献不大。公海渔业捕捞量约占全球海洋捕捞总量的4.2%,如果将水产养殖和淡水捕捞的产量也计入,则仅占全球水产品总产量的2.4%。而且,目前多数公海渔获物最终进入的是并不缺乏食物的富裕国家市场。

2019年4月发布的 《30×30:全球海洋保护的蓝图》 中推演出的数百种海洋保护区网络规划(橙色部分)方案之一。 © 绿色和平
大部分公海鱼类资源属于跨界鱼类,由公海捕捞船队和沿海国家共享。研究估计,假如没有公海渔业,沿海渔业资源会增多并带来捕捞量增加,全球渔业总产量不会有净损失。在许多沿海国家,渔业是当地居民重要的生计和食物来源,而公海渔业的经营者多是商业公司,从这个角度看,公海保护区可能对粮食安全和就业产生更大的效益。
公海保护区在很大程度上不会损害公海渔业行业的利润,因为目前公海渔业的盈利高度依赖于渔业补贴。据研究,2014年,公海渔业行业共接受了42亿美元补贴,去除补贴后,行业利润仅为14亿美元至负3.46亿美元,如果没有补贴,54%的公海渔场上的渔业都无法盈利。
其次,一些以“到2030年,保护30%的海洋”这一目标为背景的研究显示,达到该目标并不必然造成公海捕捞量的减少。保护区会使一些海域成为“禁捕区”,但捕捞船队可以转移到其他渔场(前提是遵循可持续渔业管理且不对新渔场进行过度捕捞)。通过大数据和计算机技术,科学家可以规划出若干保护区方案,在达到保护目标的同时将对公海渔业的影响降至最低。
2019年,绿色和平与牛津大学、约克大学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只需对现有22%的公海捕捞投入进行重新布局,就能够实现30%的保护目标。2020年最新发表的一份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该研究证明,在将公海捕捞热点区域纳入模型后,保护区73%的规划都可以保持不变,表明保护区对公海渔业的整体布局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不过,保护区的确会带来捕捞产量的重新分配,有些国家的船队可能会从中受益,有些国家的船队可能面临损失,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是未来公海保护区设立的关键点。对此,各方应当尽早开展相关研究,加强沟通和合作,从已有的区域实践中汲取经验,以助力这一问题的谈判和妥善解决。
最后,虽然建立保护区在短期内会对公海渔业带来布局调整、产量重新分配等影响,但长期来看,保护区带来的资源恢复和增长,增强渔业应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韧性等各种成效,将使包括公海渔业在内的全球渔业都从中受益。
中国远洋渔业转型与公海保护区的“协同增效”
中国是公海保护区建设密切的利益相关方。截至2016年底,中国有公海作业渔船1329艘,产量132万吨,分别占世界公海渔业总量的6%和12%。
在经历了数年的捕捞能力快速增长后,2017年《“十三五”全国远洋渔业发展规划》确立了以“转方式、调结构”为核心的一系列发展目标。中国的远洋渔业行业可以从积极参与公海保护区,特别是带有禁捕措施的完全保护级的保护区的建设之中,找到与行业转型升级、提高质量效益、提升国际形象等诸多发展机遇。
公海渔业长期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不在产量,而在质量。可持续、生态友好的渔业产品,不仅可以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而且便于进一步拓宽市场。近年来欧美等公海渔获物的重要进口方,出于履行其在可持续渔业和生态保护方面的责任等原因,不断提升进口水产品的环境标准,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或地区设立或加强此类进口标准。此外,水产品加工、销售企业以及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生态友好的产品正得到越来越多市场的青睐。
此外,积极参与公海保护区建设,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也有望作为远洋渔业行业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新路径。一些走在前列的渔业企业,如南极“负责任的磷虾捕捞企业协会”、挪威的Fiskebåt渔业企业联盟都已经找到了捕捞与禁捕、开发与保护携手并进的发展动力,树立了很好的范例。

2014年5月,印度尼西亚科摩多国家公园,日出照映下的珊瑚礁。 © Paul Hilton/Greenpeace
在“后BBNJ时代”正式开启前,中国的远洋渔业行业可以为积极参与公海保护区的建设进行充分的准备。一方面,应继续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强化监督执法手段,提高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与水平。对渔业部门而言,执行公海保护区与执行现有的禁渔期、禁止跨界捕鱼等措施没有本质差别。
除了加强海上执法合作外,还应强化其他环节的管理,例如提高水产品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强化港口管理,以防止在保护区内捕捞的非法渔获物流入市场,或者利用卫星、遥感、电子监控等手段监督渔船活动,及时提供执法信息。
另一方面,应加强公海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科学研究、数据收集和共享,促进国际合作和沟通交流。在完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基础上,保护区的规划设计方案并不唯一。
在“后BBNJ时代”,公海保护区的划定方案仍将以磋商谈判形式产生,这必然会是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提前为保护区划定方案进行准备,既有助于明确表达中国远洋渔业行业的相关诉求,更能推进保护区设立的进程,促进保护目标的达成。
多方资源应当被调动起来,一同服务于渔业转型加速。例如,“有害”的成本性补贴应被转移用于渔业管理、服务、科研、保护区建设等“有益”的活动;增强多学科交流;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