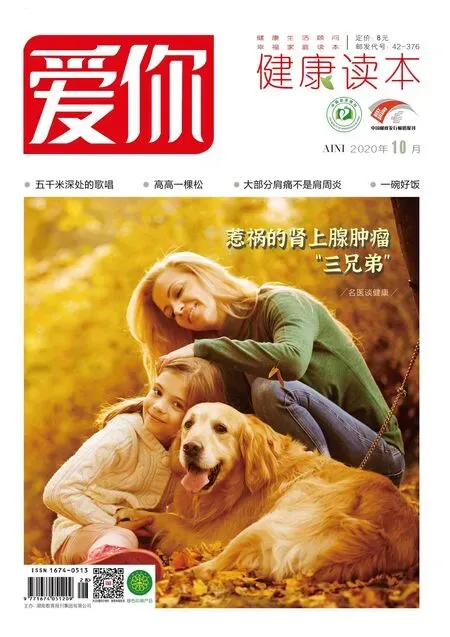“不正确”旅行
□ 陈思呈

最近带孩子去了两次顺德,精心设计路线,带他听有意思的故事,讲知识点。回来问他,这次顺德之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手机掉进池塘里了。我要掉手机,哪里不能掉,用得着辛辛苦苦跑去顺德掉吗?
想起之前我们去旅行,问他对辽宁岫岩县松嘴沟印象如何,他说那里日本弓背蚁特别多。问他对小兴安岭印象如何,他说在那里能看到草地铺道蚁。我问他这蚁那蚁的,广州有没有。他如果说有,我就有点儿遗憾了;他如果说没有,我就很满意。毕竟是旅行,总得遇到点儿在广州所没有的事情才值得留念。
比如掉手机,在广州也能掉,没有必要专门组织一次旅行来掉。
不过,想到自己,我就很宽容了。有时候我去了一个地方,甚至不想离开酒店,只想在房间里睡觉。那样的旅行岂不是更浪费,要睡觉哪里不能睡?但我心里很明确:当然不是,在这个城市睡觉,跟在广州睡觉还是有不同的感觉。
以上这些旅行是“不正确”的旅行的几个范例。与它们相反,“正确”的旅行是合理利用时间,增长了见识,享受了生活,提高了品位。要“会玩儿”,看到目的地的各种亮点,包括风景、美食和文化,否则就是“不会玩”。
但我很欣赏那些不怎么“正确”的旅行。比如,前不久看到王鼎钧的书,里面写到他到达任何地方,都会发现很多非常无聊的趣味。他分享北桥儿童的乐趣;看人在村首的大槐树下理发;看别人买一斤花生堆地上,大家围成一圈边吃花生边交换新闻,最后吃完了,还要把花生壳再淘一遍——这观察也是够细致的。他还看乡下的猪的样子,觉得它们脸上有耐人寻味的皱纹。
另一个旅行者赖瑞和是一位研究杜甫的学者。几年前看他的游记,觉得他的旅行也不是十分“正确”。他来到济南,攻略没做好,吃了一顿失败的海鲜午饭之后一时不知去哪里,就去山东大学。骑了半天车,路上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祁门红茶”,然后他用了三页半写他见到这牌子的惊喜,目的地山东大学则用两个自然段随便带过。这种原产地为安徽的茶,本与他这趟旅行毫无关系,这游记简直“跑题”。但作为旁观者,我的观后感特别好,那些名山大川,仿佛都输给了这500 克红茶。
说起自己那些并不“正确”的旅行,其实我也敝帚自珍。我们去的地方不多,但多数地方都会反复去。这些地方,我把它们称为根据地。比如草原上朋友的家就去了几次,若不是非常时期,我恨不得带上打印机,到草原上去上几天网课。
我自己固然享受,我也愿意孩子在他的童年里有这样的“几城记”。那些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细节,可能是比知识和见识更让我珍视的经历。一个地方的生活,总是因为与另一个地方的生活比较而变得鲜活细致起来,如果不相比较,它们彼此都会习焉不察。
家中老人会觉得,反复去一个地方,不够增长见识。有时候一说要去某处,他们会有些疑惑:“怎么又去?不是已经去过两次吗?去些新的地方才能开阔眼界啊。”
老人的这个句式,有点儿像我几年前在报社里做一个亲子阅读专题时收集到的家长意见的几个常见句,其中一个就是:“这本书你都看过多少遍了,怎么还看?看些新的书才能有进步啊。”
我们去的地方,往往不是因为它很精彩,而是因为方便。比如有熟人,或者路途近,或者恰好因为一个偶然的工作机会需要常常去。
比如,乡下的老家或者广州的周边,这些地方都不算很理想的旅行地点,前者是我从小看熟的地方,回乡和远行,毕竟还是有很大区别;后者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太接近,这样的旅行,也当然没有去远方的刺激。
但我认为,把生活里的局限性利用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技能。把理想生活寄托在远方,恐怕很容易造成眼高手低。只要有一点儿时间,我希望可以做到脚一抬就去旅行,一小时的车程正好匹配我这样的行动力。
旅行归根到底就是创造记忆,记忆没有什么正确和不正确可言。日本纪录片《人生果实》讲的是一位日本建筑师修一和他太太英子在名古屋郊区一栋房子里的生活。老奶奶英子说了一句话:“要为孩子们的人生留下一些丰盛的东西。”她说的不算什么惊人的真理,每个人都想把丰盛的东西留给孩子,至于这丰盛的东西是什么,则很值得探讨。记忆也许是最丰盛的,因为别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只有记忆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