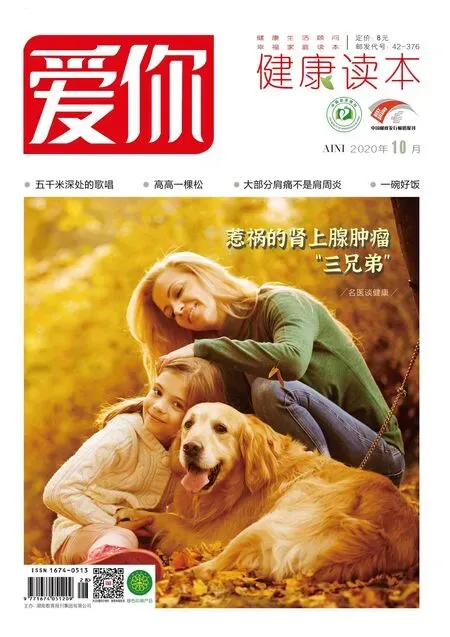蚂蚁“拌饭”
□ 璞石
20 世纪60 年代初,连续几年巨大的自然
灾害,加之大国逼还外债,全国所有物质实行凭票计划供应。为支持国家建设,全民缩衣节食过上了苦日子。
此时期,刚过五十的父亲积劳中风,只能在家自疗,母亲上班早出晚归,两位姐姐先后从卫校毕业且都分到了外地工作。于是,正读小学四年级的我与父亲有一段长达近三年难以释怀的密切生活交集。
那时,家中“常住人口”就是父母亲与我。全家基本生活轨迹单调、重复。通常是每天傍晚母亲下班买菜回来,急忙搞晚餐,同时把第二天三个人的中餐饭菜准备妥当。第二天清早,母亲就带着自己的那份中餐去上班了。中风瘫痪、行动不便的父亲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我,午时放学回家把饭菜加热后,一起进餐。
那时的家用煤炉不仅天天需要干柴重新生火,而且时间稍长一点,煤炭烧尽就自然熄灭了,必须有人适时打理,疏通添加新煤才能保持炉火延续。

为了确保家中的煤炉中午与傍晚都能尽快达到煮饭炒菜的火候,尽管当时父亲坐卧活动的范围仅在方“尺”之间,但是父亲在上下午“尽心尽职”烧完两壶开水后,还须及时通炉出灰,换上新炭,保证家中煤炉用时可旺。
白天时段,我要事先把煤炉、搅和好的湿煤以及烧水壶、热水瓶等物,放置在父亲的病榻旁。床边的煤炉三九严寒尚可取暖,春暖花开还能勉强应对,酷暑秋燥高温烧烤,坐卧炉旁实际比在户外烈日暴晒还难受难熬,犹如身在釜甑中。
当时,中午一放学,自己必须尽快拔腿跑回家,所以总是眼馋小伙伴们在放学途中能磨磨蹭蹭地玩耍,并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是家中最“累”的人。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年少太幼稚懵懂了。无论是精力与体力,每天母亲的付出是最大的,而时处中年的父亲病中只能卧床和坐立,他内心所承受的痛苦与压力远远超过常人。
然说到物质匮乏的60 年代,就像讲“天方夜谭”。当时根本无从知晓冰箱为何物,夏秋两季,家中隔天预留或剩余的饭菜,都装在瓷碗内,放在竹篮中,设法置于阴凉通风之处,有条件的则悬吊于清凉的水井里,一般大多吊挂在房屋中空气流通的高处。
我们家通常是将饭菜篮挂于过道晾衣的竹竿上。有时天气实在太热,在吃过数次馊饭菜后,索性把剩饭仍留在煮饭锅内,放在紧依水缸底边的潮湿地面上。这样,尽管天热,第二天吃馊饭的次数倒还略有减少,但没隔多长时间,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
记得在夏末秋初的一个中午放学后,我急忙跑回家中已是满头大汗,熟练完成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父亲床边将煤炉移至房外,接着火急火燎地热好隔夜菜,再到水缸边端饭锅,谁知打开锅盖,竟看到锅内黑压压地挤满了“兴奋异常”、不停爬动的大小蚂蚁,我几乎同时感觉到端锅持盖的两手痒痒的,原来瞬间蚂蚁就爬了上来。我这才注意到,就连黑黑的饭锅外壳也早被密密麻麻的蚂蚁大军包围占领了。
当时,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饭还能吃吗?”父亲看了后,立马面带焦虑地说:“能吃,能吃!倒入冷水,蚂蚁就会爬出来的。”反复几次实施父亲传授的“水攻”浸泡,蚁口夺食“战术”,仍有不少“置生死于度外”的顽固分子硬是“与阵地共存亡”。
看来锅内米饭中的蚂蚁用水是不可能“全歼”的,加之下午还要上课,时间不允许。于是,仍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只好把还黏附着不少蚂蚁、被水浸泡得湿漉漉的米饭倒入炒菜锅中加热。
在不时地翻炒的过程中,米饭内不断地爬出一些残余的蚂蚁,可还没有爬到锅边,很快又原路撤回了。在翻动米饭的同时,自己也不停地捻掉了不少“不知所措”的蚂蚁。实在觉得根本无法清理干净了,饥肠辘辘的父子俩也顾不了那么多,最后连同米饭和蚂蚁一并吃了个精光。至今还依稀地记得,刚开始父亲看到我皱着眉头,极不情愿地扒着饭时,开朗地调侃说:“蚂蚁‘拌饭’比馊饭的味道好多了哦!”听到父亲的开导,我也狼吞虎咽地很快就吃完了。
后来我们俩似乎都感觉到有点腹胀。当然,也搞不清是蚁毒的“功效”,还是米饭被水泡发了的缘故。
自从有了第一次速吞蚂蚁“拌饭”后,不知是蚂蚁有记忆功能,或是蚂蚁饭至少比馊饭容易咽下,接下来大凡高温的日子,全家三口都有多次吃蚂蚁“拌饭”的经历。其实,在那个年代,说出来也没有人笑话,绝大多数家庭为填饱肚子都有这样类似的心酸“囧”事。
璞石有话说
从前的苦日子早已离我们远去。当下全国人民边抗疫情,边加快建设祖国,我们是伴随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老人,也是往事的见证者,对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感慨万千,有责任诉说与告知年轻一代,且行且珍惜,为更强、更富、更美的祖国明天活出民族本真,干出强国真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