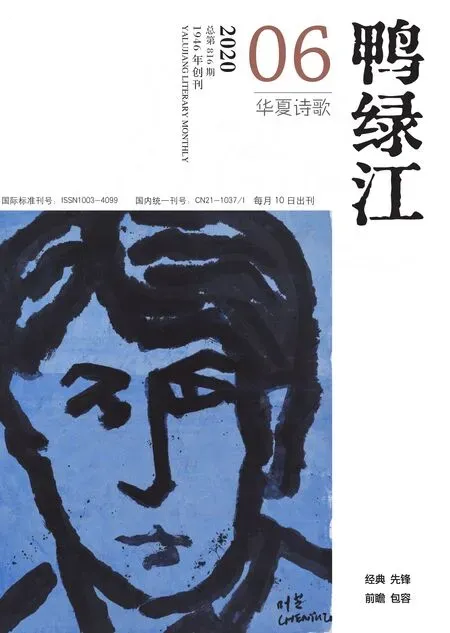大诗人皆半神,说出他的预言
方文竹

方文竹,安徽怀宁人,供职于媒体。80年代起步于校园诗歌。出版诗集《九十年代实验室》、散文集《我需要痛》、长篇小说《黑影》、学术论文集《自由游戏的时代》等各类著作21部。“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风云人物”之一(姜红伟)。1997年6月11日中直三家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方文竹作品暨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研讨会”。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2005——2006),中国·散文诗大奖(2011),“中国当代诗歌奖(2011—2012)”等。作品入选英汉对照版《中国新诗300首》《百年诗经》《世界诗歌年鉴2013》《1991年以来的中国诗歌》等。少数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史诗性长诗就像一艘巨船,将一切都装进去。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史诗的创作是一场冒险:“货物”少了,成就不了一次满意的旅行;超负荷则易于造成船体沉没。只有通盘运筹,战略战术并用,大事细做,具体而微,才会称得上满载而归。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正体现出如此卓越的功夫。这艘诗歌之船不仅没有消沉,而是扬帆远行,旌旗飘荡,蔚然大观。诸多名家对其高论甚多,颇领教益,本人意在绕道而行,另谋他途,避免面面俱到、步人后尘,而有意挂一漏万、撷取几个感受较深的方面求教于大家。
索隐
我不认识作者。初读《沉船》,除了知道作者名,仅是白纸黑字。这样当然也能解读一首诗,但是对于一部史诗来说,则远远不够,必要的背景信息会挥发出诗意的深度和广度。黑暗中的景象比明眼看得出来的景象更精彩,没有说出的部分远远优于说出的部分。一首优秀的诗不仅由说出的部分组成,更多的由未说出的部分暗示出来。牵扯、共生与烘托,在明暗、有无、前后的闪烁之间,史诗的神秘性资质不断地处于敞开之中。
写作时间为作品的内容增强了力度和厚度。《沉船》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人文精神跌落、商业气息弥漫的特殊时期。无疑,《沉船》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发出了异端的声音,是一部时代的控诉书、启示录,同时也是一部个人的心灵史。由此可窥其思想和艺术的更为不易。
诗人的出身。诗人的祖籍青海循化,民族为撒拉族,处于青藏高原东部,人口虽稀少,多种语言却意即“战斗”“武装”“征服”等,与全诗所表达的气息颇为合拍。这是一种原本、现成的诗性。遵循着诗人的民族出身,让一艘“沉船”从制造、试水到远航、沉没等找到了落脚之处。当然,民族性并未限制诗歌意义的增殖反而扩大至人类普遍性。这里应验了歌德的那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作为少数民族,诗人上学的专业为英语、汉语,大大加强了跨进中国经验和世界视野的门槛。又担任某书画院院长,中国书法的气势和中国画的写意画面渗透于“沉船”的全过程。他执掌的《大昆仑》杂志可谓聚集了当代顶级名家,使其创作的起点、立足、眼光、要求高远。还有其它许多,笔者正在索取之中。
“沉船”:史诗启动的按钮
长诗难写是诗人们的共识,她是对诗人的全部积累和思想艺术水平的终考。而史诗性长诗的写作则是难上加难,稍有不慎,便易流于大而空,堆砌而浮泛,漂浮而散漫,大有铺摛异体、无从下手之虞。我认为最麻烦的在于结构形式,这里结构形式直接建构着内容本身。因此不少诗人为此伤透了脑筋。带来“远古的传说和久远的往事”,阿尔丁夫·翼人选择“沉船”作为题名和史诗之“元”,亦即中心线索,自然构成了整部作品的总体象征并被诗人赋予了生命,带动和包容众多主题词的感性激活,统领所要表达的材料,使诗性柔软、散开、铺展。问题是,紧扣“沉船”实属不易,稍加松手,整部作品会是一盘散沙,如何进行内在的勾连却是成败之关键。为此,诗人采取辐射法,由“沉船”衍生出河流、河岸、观望、大地,等等,在大地与天空之间腾挪,从而化解了一般史诗的硬块,而显得诗意浓郁且脉络清晰。
“沉船”无疑是一个民族——撒拉族的孕育、诞生、成长、苦难、搏斗与迷茫的隐喻。它构成了民族的精神母体与象征,托象引义的线索。
“沉船”于是成为史诗“原道”之见证,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囊括能力:
人的走向依然是河流的走向
长河啊 当思想的船只沉入深深的河底
属于我的船只得搁浅在何处?
此刻 流动的香云
滑过天顶 流向岸边
苍茫的上空
这样,“沉船”统领了全诗的总命脉,成为全诗的按钮、总开关,像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长蛇布阵、通变无方,虑密连骨,万取一收。全诗皆“沉船”的变异、衍展、放大与暗含。放得开又收得回,不弥散,不凝固。无关而有关,没有游离于外的散片和多余枝丫,距离较远的“有关”反而给作品增添了诗性张力。经历无数挣扎,请看全诗结尾:
湿润的眼睛早已化作蒙昧的花园
在期待和迷恋中 返回
幽幽的灵魂深处——
叩伏于母亲的营地
在旭光中向内陆挺进
这分明是“沉船”精神的再现与复活。既曰“沉船”,就是一个具象,或美学事件,是一个诗性化的总体象征和民族寓言,形成意义的生值与增殖。内容又回归于形式,或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形成圆环式的自足体系。是一首地地道道的诗!
题旨
史诗即大诗,包容一切,天地神人共驻一体。与此相应,《沉船》的容量大得惊人,但并非没有基干和脉络,这就是它所包含的人类基本问题:时间。历史。家园。宗教。生命。爱情。英雄。永恒。生死。苦难。幸福。真理。灵魂。尊严。彼岸。超验。……真的是应有尽有,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次主题 :罪恶。泪水。黑夜。太阳。土地。运动。变化。悲壮。热血。情绪。孤独。……一切最终归结于人。《沉船》就是诗性化的一部哲学人类学词典。其内容是异常丰富的。
史诗意义求索的全部内容可以抽象出“词”,就像维特根斯坦言:哲学即解词。同理,史诗性作品不得不钉牢几个关键词进行诗性打磨。不仅如此,还应有地域和诗风意向等的不同表现,尤其是中西文化的遥隔与勾环,《沉船》作者正是如此更进一步,偏向异境求索:
哦,乔吉娃 亚当罪恶的化身
哦,玛斯木 夏娃母性的火种
世界本一。达于原(源)始性的寻求,意在拯救存在的遗忘状态。史诗之史,达于人类的普遍性。
各个题旨之间并非水火不容或各走一边,而是相互映射、蝉联一体。这一切皆与“沉船”相关。“沉船”正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聚拢”,是收归、放开、敞开、召唤、互孕。
化解大词的功夫
对于这样一部异常厚重的民族史诗,由于浸透了强烈的人文精神,一些大词的运用必不可免,但是稍有不慎或艺术表现火候欠佳,会造成诗性的梗阻和主体意念的爆胎而显得空乏。很多作者为此伤透了脑筋,甚至为此不敢涉足长诗。知难而进的《沉船》作者如何面对这一写作上的拦路石?我认为,诗人在化解大词方面显示出点石成金的功夫。
大词在诗性叙述中变成诗性元素。全诗始终站着一个“我”——第一人称的抒情主人公,甚至直接充当自己民族的代言人,但我们触摸到他的肉体,他语气急促,抑扬顿挫,始终有一种引吭高歌式的激情,通过这个视角,一切大词皆为强烈的个人气息所过滤、熏染,抽象的概念化为可感的“材料”,冰冷的大词进入叙述的热度熔炉,道存目击,道成肉身。通过燃烧式的理性化约,诗性之石纷纷粉碎,转为七彩的云霓。
大题小做。大词与大词的碰撞、相嵌,需要细心呵护、化隔为缘,这是一种聂鲁达式的抽象与具象的联姻:
熄灭世界的晚景
使那些大地的情人
丢下思想的山脉
开始转向现实汹涌的河岸
化生命为流浪的歌谣”
总体诗境的营造。“沉船”是一个喻体。读过《沉船》,我有一种气息贯注的感觉,这缘于诗人异常强大的气场,在不动声色中运用语调和语态的高超技巧,以至于看不出半点“技巧”的痕迹。从而,什么大词的大量运用造成诗艺的走钢丝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其实,气息是神为诗人代言的表现。从这方面看,诗人的工作不是创造,而是发现。
互文
《沉船》与作者的其它长诗《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耶路撒冷》《母语:孤独的悠长和她清晰的身影》《遥望:盛秋的麦穗》《我的青铜塑像》《神秘的光环》《光影:金鸡的肉冠》《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被神祇放逐的誓文》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照应的文本效应,显示出一个诗人的总体实力和“解释学循环”。这种互文式的写作,不仅增加了长诗的容量,开拓了新境,而且体现出个性化风格。由此诗人的全部写作不是孤立的,则是相互启发、纠偏、补缺、增量、增殖,万变不离其宗,最终的目标皆指向一种至境甚至一个主题、一个词。哲学家柏格森说,很多哲人终其一生只为追究一个词。同样,伟大的诗人一生只写一首诗。
作品还在题词中引用了墨西哥大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句,如此致敬不仅仅是一种写法问题,而是引导向异域延伸,增加一首诗的背景,化无为有。既遥远又亲近,对于一张“脸”的寻找,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是对于神秘的沉迷与玩味。这让我想到:大诗人皆半神状态,天亮时说出他的预言。我还看到,由于充当了预言家和先知,诗人对于现代性的寻求与呼吁,大大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而在当代中国诗坛,似乎这一切都遭到了指责和解构,但是,《沉船》作者恢复了诗人的神圣使命,坚守诗人的责任,恢复“当代史诗”的名誉,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深思“诗人何为”这个老问题。
海德格尔通过最喜欢的诗人荷尔德林提出,诗人乃“半神”,即:非人非神,亦神亦人。我的意思是:“半神”乃“神”与“人”的“中介”,向“人”传达“神”的信息,贯彻“神”的意旨,天空和大地于是一片光辉。问题在于,芸芸众生中为何独独选择诗人承担此项使命?无疑,诗人是几率极低受到神青睐的人,其特殊的秉赋和天职由此彰显。而阿尔丁夫·翼人正是这样的诗人,他让命运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