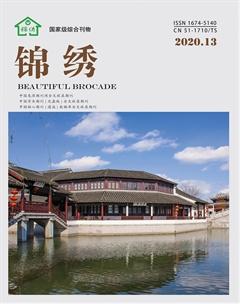失语中分裂与反抗:祛蔽的赵姨娘形象
任祥欣
摘 要:《红楼梦》女儿国中,赵姨娘是一个妖女式的独特存在。在父权制社会的压制之下,在“受歧视、欺辱的嫡庶关系的处境”之中,赵姨娘被扭曲成一个“妖妇”式的人格。另一方面,赵姨娘正是通过这种恶魔附身的策略,来积蓄反抗的力量,以报复和毁灭这一不合理的父权体系,达到自我拯救。而在探春对待母女关系的态度中,其站到了维护封建父权制的一方,从侧面反映出了“父权制对于女性谱系的压制与剥削”。
关键词:《红楼梦》;赵姨娘;女性主义;女性谱系
在《紅楼梦》一众有血有肉的圆型人物中,夹杂着一个变态的、愚昧无知又让人厌恶的毒妇式的扁平人物,那就是赵姨娘。而扁平人物并不是劣于圆型人物的,杰斯特顿认为扁平人物具有夸大生活面的作用。而赵姨娘的存在,正是体现了另外一种,不同于红楼众女儿的真实。
一、“女儿国”中的男性霸权
《红楼梦》中建构了一个女儿国式的大观园,上至林黛玉、薛宝钗这样的千金小姐,下至袭人、晴雯甚至是芳官这样的下等丫鬟,各个都是“水作的骨肉”,千姿百态、婀娜风流,让人可怜可叹、可歌可泣。许多学者认为《红楼梦》表现了强烈的女儿崇拜意识,这一说法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曹雪芹具有当下意义上的性别平等观念。《红楼梦》中所崇拜的仅仅是未出嫁的女儿,但是对于人老珠黄的妇女们,就变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凡女儿个个是好的了,女人个个是坏的了”。可见,所谓的女儿崇拜,在曹雪芹诚恳的笔下,也隐含着当时社会思想中对于女性把玩的态度,而对于女人,曹雪芹的态度就更不友好了。
戴锦华在《雾中风景》中提到:“一个女人的主题似乎首先是关于一个沉默的主题,始终是象征性的:那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个被囚禁的、被迫沉默的女人,她唯一的行动是以仇恨之火将她的牢狱变成一片废墟;关于她的一切和她的阐释是男人们给出的,她被命名为疯人,因而永远地被剥夺了话语权与自我陈述的可能。”[2] 赵姨娘就是在叙述中被剥夺了话语权和解释权的一个“沉默”女人。在曹公笔下她永远都是被解释的那一个:她是贾政的妾室,探春贾环的生母,荣国府的一个姨娘,没有出身,下咒谋害叔嫂的阴险之人,为兄讨赏银而辱亲女的愚昧蠢人,为儿出气与下人厮打成团的低贱小人。
作为接受者也无法感知到赵姨娘内心的真实独白,只能看到她插科打诨地粉墨登场,匆匆狼狈地落荒而逃,或对其一笑而过,嗔其愚劣,或咬牙切齿,嗤之以鼻。这样的一个赵姨娘,是父权制话语下对其真实境遇和自我陈述的遮蔽。那么本文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为赵姨娘这个形象祛蔽。
二、向恶魔借力的赵姨娘
一个有趣的对照:红楼众人无论男女上下以及许多文本的接受者,对赵姨娘都持有一个相同的批判态度,那就是看人家周姨娘,她不招惹人家,人家也不招惹她,意思就是周姨娘才符合一个做姨娘的体统:顺从、本分、驯良。这里可以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的“天使与妖妇”这一概念来类比周赵姨娘。[3]
周姨娘属于父权体系下被驯化的“天使”,是完全按照男性的审美理想来塑造的,她膝下无子,境况实际上比赵姨娘更惨,因此她对于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希冀,唯图在父权社会中苟全性命,实则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赵姨娘则被塑造成了一个妖妇,但在深层文本中,在被男权话语压抑和歪曲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不肯顺从、不愿放弃个体的具有反抗力量的存在。赵姨娘虽然低贱,但她有儿有女,所谓母凭子贵,这给她看见了突破囚笼,获得人的尊严,拥有更好人生的希望。但在父权体系之下,她永远只能当一个低贱的姨娘,即便儿女能够享有主子的地位,她却终究得不到的尊重。在贾府众人中,她看得上薛宝钗,仅仅是这位冷面小姐对任何人都不会表露厌弃,而她却误以为是对自己的尊重。
在父权制社会的压制之下,在“受歧视、欺辱的嫡庶关系的处境”之中,赵姨娘被扭曲成一个“妖妇”式的人格。另一方面,赵姨娘正是通过这种恶魔附身的策略,来积蓄反抗的力量,以报复和毁灭这一不合理的父权体系,达到自我拯救。这是赵姨娘的唯一选择,虽未能改变她的悲惨境遇,但确为贾府“树倒猢狲散”的结局,给予了微薄一击。在《红楼梦》之后,也出现了赵姨娘一类的形象序列,例如老舍笔下的虎妞、曹禺笔下的周繁漪以及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等等,这些妖妇一般的女性人物,都在向恶魔借用力量,挑战着封建父权的权威,令人动容。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物的毁灭力量也愈见强大,而这些人物形象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赵姨娘。
三、“女性谱系”中赵、探的母女关系
把目光聚焦到探春对于赵姨娘的态度,就更加能够明确父权社会中对于母女关系的扭曲。探春对其母赵姨娘处于完全不认同的状态,她恨自己的生母不仅不能帮衬她,反而频繁地给女儿使乱子,所以探春便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不认赵姨娘这个母亲,说自己的母亲只有王夫人一人。这也就是说,如果赵姨娘像周姨娘一样,虽然低贱,但安分守己一点,探春也就能够接受了。
伊瑞格瑞所主张的“女性谱系”,吸收了精神分析批评中的“恋父情结”主张,认为女孩对母亲的认同是一种对“双性同体”母亲的遗弃,实际上是对父权制的认同。[3] 可以发现探春认同的母亲形象其实就是被封建父权制所“阉割、被动的母亲的认同,实际上是对父权制的认同”,而赵姨娘对封建父权的挑战触及了探春在父权制下的社会经验,故遭受到了女儿的放逐。由此可见,即使是探春这种富有英气的女性,也难逃父权话语体系的暴力。
以往我们所认识的探春、黛玉等一干女儿们,都是那么有个性、那么独立的女性,但遇见赵姨娘这个挑战封建父权制的角色时便自觉站到了父权制一边,不自觉地充当起了封建礼教的维卫道者,可见父权制对于女性谱系的压制与剥削深入到《红楼梦》中女性的意识当中,放逐了女性的最高自由选择。而很多人深恶痛疾,认为是插科打诨式的赵姨娘这一形象,却作为“妖妇”式的女性,在失语中潜藏着突破封建礼教的力量,这对于接受者从微观上认识红楼女性有着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曹雪芹 著 / 高鹗 续.《红楼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6.
[2]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6:125.
[3]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三版)[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14:288-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