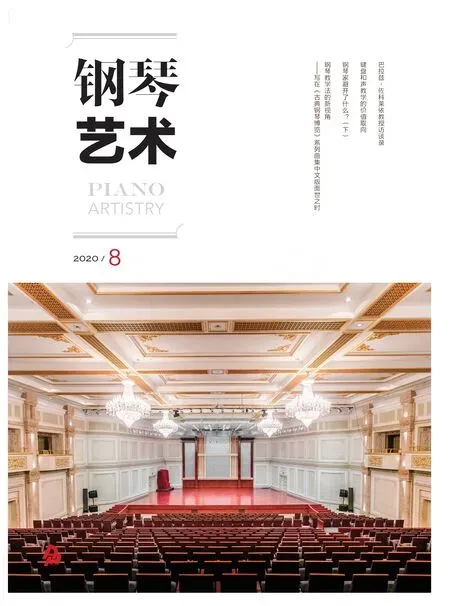钢琴家避开了什么?(下)
文/ 张可驹
Avoidance of the Piani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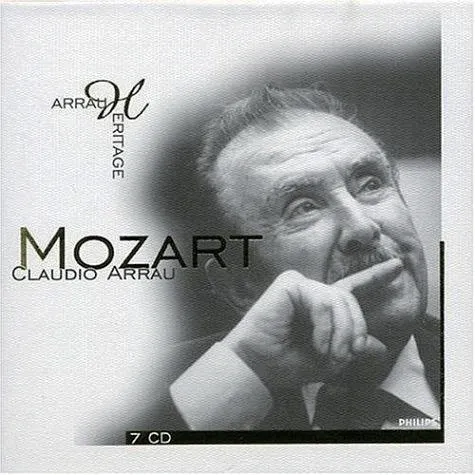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了解到鲁宾斯坦这样尤以曲目量广泛而著称的钢琴家也有自己所回避的领域,科尔托这位肖邦与舒曼的权威演绎者恰恰是在他最擅长的范围中有自己的取舍。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几位钢琴家,多数都拥有超乎寻常的广博曲目,所以他们的回避也就更耐人寻味。
吉塞金
在里赫特出现之前,似乎没有哪位钢琴家的保留曲目之宽广能够媲美吉塞金,此人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能够以准确的风格掌握许多不同类型的音乐。目前很多钢琴家都追求做到这一点,有人可能还做得不错。然而,能达到那样一个层面的,也许只有吉塞金与里赫特,连阿劳都不算,因为他的俄罗斯曲目和现代音乐弹得都比较少。吉塞金同时在德彪西、拉威尔,以及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中取得的成就已不用多说。他也是那个时代灌录巴赫作品最丰富的钢琴家之一,并且他还没有忘记亨德尔和斯卡拉蒂的键盘音乐。吉塞金也弹了很多现代音乐,虽然其中大部分可能没留下录音。
这位钢琴家演奏的斯克里亚宾是那个时代的名演;在民族乐派方面,他弹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为作曲家本人所推崇;面对格里格,也不仅是灌录热门的钢琴协奏曲,而是将抒情小品“大录特录”。舒伯特作品的录音少一点儿,可能是时代趋势使然;舒曼和勃拉姆斯的作品他也都留有一定数量的录音。在主流的作品方面,吉塞金仿佛是没有死角,虽然我没考察过他是否弹西班牙音乐,但这样的广博在同时代人中已属罕见。况且,吉塞金对很多作曲家的掌握是相当全面的,通常情况下不会只弹几首作品而已。那么,钢琴家避开了什么呢?居然是肖邦的音乐。
吉塞金不是不弹肖邦,而是弹得非常少。在差不多同时代的几位德奥钢琴家,以及阿劳这样德国学派的外来者当中,巴克豪斯与肯普夫演奏肖邦比较多,阿劳更是比较完整地灌录了肖邦的主要作品,塞尔金也留下《24首前奏曲》的录音。与他们相比,吉塞金的肖邦录音明显少了许多,但真正让我好奇的,是他演奏肖邦的纯正感。德国学派的钢琴家弹肖邦往往免不了有“德国味儿”,巴克豪斯与肯普夫的肖邦虽然很不一样,却都有那种味道,阿劳的演奏亦然。吉塞金却完全没有这种倾向。他的肖邦确实比较古典,而不贴近霍夫曼、莫依塞维奇他们所代表的浪漫一路,但那样的古典风格是节制而明朗的。《摇篮曲》的演奏同科尔托分庭抗礼都没问题,《F大调前奏曲》(Op.28,No.23)虽然仅有短短一分钟,其触键中的色彩变化结合古典风的镇静却为浪漫派演奏提供了绝佳的互补,足可一听再听。
也许我们会喜欢更浪漫一些的《船歌》,但吉塞金所呈现的自然仍有望使之成为一款经典演绎。除了速度控制中的自然,钢琴家的踏板也用得十分节制,音响在古朴中又有足够丰富的变化,既非巴克豪斯那样德国式的严肃,也不是拉赫玛尼诺夫、霍夫曼那样的绚丽多彩,可谓自成一格。在这种情况下,钢琴家为什么对肖邦采取如此审慎的态度?也许真正的原因只有钢琴家自己知道了。仅是寥寥数曲的演奏就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以《船歌》的部分而言,吉塞金的演奏固然杰出,却仍旧没有他弹莫扎特、贝多芬、德彪西那么杰出,也许面对这位作曲家,他还是弹不到自己所认可的顶尖水平?但如果以《摇篮曲》《F大调前奏曲》中的成就推向其他的肖邦作品,钢琴家所到达的高度应该是不会比他弹古典派与印象派低多少的。
阿 劳
正如先前所提到的,阿劳所拥有的宽广的保留曲目仅仅稍稍逊色于里赫特、吉塞金,换一个角度来看,他甚至也并不逊色于他们。诚然,钢琴家在现代音乐与俄罗斯作品上涉猎较少,但他演奏巴洛克、古典与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往往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系列,而面对一位作曲家,里赫特往往更有选择性。
阿劳的演奏风格初听是厚重、深刻、偏慢的,但越熟悉这位钢琴家的艺术,越能感受到他在这样的外表下隐藏着怎样强烈的激情。那偏于厚重的音响中既有朴素,也有金碧辉煌,演奏既有理智与清晰性,也有奔放不羁的自由速度,钢琴家心目中的理想风格可以追溯到李斯特。阿劳灌录巴赫与莫扎特作品的数量都不少,即便不如吉塞金那样丰富,他也能够以舒伯特的音乐来弥补。贝多芬的奏鸣曲全集钢琴家录过两次,协奏曲全集更是录过三次,勃拉姆斯的两首协奏曲也都至少录过两次。钢琴家也比较完整地灌录了肖邦、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的独奏作品,至少对他那一代人来说是相当完整了。
在民族乐派这方面,阿劳常见的录音仅限于柴科夫斯基与格里格的协奏曲,他年轻时也弹过《图画展览会》。钢琴家对现代作品其实很有兴趣,但录音并不多,BBC Lengdes发行过他弹勋伯格的现场记录。纯粹以录音来考量阿劳的保留曲目确实有些不够(尽管他的录音已很丰富),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钢琴家的曲目也发生过不小的变化。年轻时,他的音乐会曲目简直包罗万象,亨泽尔特与胡梅尔的作品都有,还有一些现代音乐,以及一批南美作曲家。另外还有布佐尼,阿劳热爱他的艺术,甚至还弹过阿尔坎的作品。尽管比重不是很大,但这些作品确实展现出惊人的丰富性,并且让我们看到除了李斯特的音乐,阿劳也喜欢其他技巧繁重,内容又为自己所认可的作品。到20世纪50年代,西班牙音乐、福雷的作品都还在他的节目单上,他对于布佐尼也一直念念不忘。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阿劳确实将他的保留曲目缩减了,可我们仍旧看到除了吉塞金之外,他是德国学派中最热衷于演奏法国印象派作品的钢琴家。他为Philips录了不少德彪西,我原本以为他偏厚重的音响不太适合拉威尔的精雕细琢,不想钢琴家也喜欢演奏《高贵而伤感的圆舞曲》和《夜之幽灵》,后者有录音传世。60年代也正是阿劳同Philips开始紧密合作的阶段,他系统灌录前述那些人的作品就是从此时开始的。我们或许看不到许多冷僻的作曲家,但阿劳在每一位大师身上的“展开”,其深度超过鲁宾斯坦,把握不同风格的广度也超过了巴克豪斯、肯普夫。然而,正像先前提到的鲁宾斯坦和科尔托那样,阿劳所回避之曲目最明显的体现不是在节目单的边缘,而恰恰是在钢琴家的德奥腹地——他没有录下任何一首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阿劳的协奏曲录音从贝多芬开始,经过舒曼、肖邦、李斯特、勃拉姆斯,一直到柴科夫斯基与格里格。这就是一部主流协奏曲的“编年史“,其中许多作品他还都录过两次或两次以上,加上现场记录就更不得了。可是当这样一份“编年史”中独缺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惊奇,倒不如说是接近于“刺目”了。在钢琴协奏曲的领域,莫扎特的作品可说是“冠冕之作”。虽然它们在19世纪一度受到忽视,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些作品不仅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还渐渐成为擅长德奥音乐的钢琴家几乎必弹的曲目。
在录音比较困难的年代,一些人没录莫扎特的协奏曲,也许是出于条件的限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对于这些协奏曲,钢琴家们趋之若鹜,很多不以德奥音乐见长的人也灌录了相关唱片。在德奥专家这边,哪怕科瓦切维奇表示他与莫扎特并不很投合,也录了两首(他不喜欢奏鸣曲)。这个问题在阿劳身上之所以让我感到神秘,是由于他其实是弹了一些莫扎特协奏曲的。在20世纪50年代,钢琴家手上还有几首中晚期的协奏曲。他确实比较早就不弹这些作品了,最后一次是在1964年。但是,跟随他学习过的加里克·奥尔森还特别提到,自己从阿劳那里学过的曲目包括莫扎特的《c小调钢琴协奏曲》(K491)。阿劳是对待音乐特别严肃认真的钢琴家(奥尔森将他跟随阿劳的学习称为“我上过最密集、最完整,也最丰富的课”),如果一部作品进入到可以传授的范围,钢琴家应当不至于对其演奏多么不满意。
原本我想当然地以为,阿劳是考虑到自己演奏中偏厚重的倾向同这些作品难于调和,从而认为它们不适合自己。后来却发现,这样的想法显然是不对的。首先,阿劳的厚度多少也适合于莫扎特的两首小调钢琴协奏曲;同时,钢琴家的个人特色鲜明不假,但他从来不会“一道汤”地处理自己宽广的曲目,总能根据作品本身的特点来设计整体的音乐表现。更重要的是,阿劳系统地灌录了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如果担心风格方面的问题,那种厚重在奏鸣曲亲切的小格局中会更难施展。阿劳却毫不在意地录了许多,此外,他还留下很少的莫扎特室内乐的现场录音。协奏曲被完整地、有意地、彻底地跳过,甚至于钢琴家虽然在舞台上弹了一些,却没有现场录音问世。照理说,目前唱片公司对于录音资料挖掘这么尽心,阿劳弹莫扎特的协奏曲应该是很有号召力的。我实在很难相信没有录音留下是种种现场条件所构成的巧合。
钢琴家似乎通过某种办法使自己弹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痕迹完全在录音史上消失了。这同他录音的整体走向,以及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定位都是严重地不协调,阿劳却做得干净彻底。
里赫特
最后,想谈谈两位俄罗斯钢琴家——里赫特与贝尔曼。为何将这两位钢琴家放在一起来谈呢?因为他们虽然同为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名家,但二人的共同之处似乎仅止于此。从细分上看,里赫特属于涅高兹学派,贝尔曼属于戈登威泽尔学派。贝尔曼主要以浪漫派曲目为世人所推崇,如果范围再收紧些,就是以李斯特的作品为主,再加上俄罗斯的后浪漫派。里赫特的曲目则是博古通今,简直“无所不弹”,并且基本上他对每一时代、不同风格的曲目之演奏都有深远的影响力。贝尔曼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自己的声誉,然而同里赫特的巨星光辉始终难以相比。仅是二人有一个关键性的共同点,足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就是他们选择完全避开不适合自己的作品。
哪位钢琴家在曲目方面的取舍不是舍去不适合自己的作品?但里赫特与贝尔曼仍旧做得太绝了。通常,钢琴家们选择曲目时的舍弃是方向性的,可能是某一时代、某一风格的作品,也可能是特定的某些作品。而划定这样的方向以后,钢琴家通常还是要面对现实环境,或者说根据市场需要来处理一些问题。里赫特却似乎完全不管这些。齐默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对录音曲目的要求比以往多,“你不可能只录肖邦的前三首《叙事曲》,而不录第四首,大家会问这钢琴家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他特别提到了里赫特,表示后者在这方面就完全不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居然连肖邦的《前奏曲》都选着弹,实在是太绝了。
我们知道,齐默尔曼还是一位在曲目选择上颇为审慎的钢琴家。但只要大环境如此,他也很难少录一首叙事曲,或少弹几首前奏曲。拉赫玛尼诺夫、霍夫曼、列维涅这些大师的超技到目前仍是不可复制的传奇,可他们选择的曲目何尝又很全面?当时的环境容许他们只弹最拿手的作品,现在却需要那种全面性,从而就带出或多或少的勉强,这对于追求完美的演奏家来说势必是痛苦的。齐默尔曼就是位完美主义者,以至后来他回收了早年一些不满意的唱片,甚至在一次签名活动中引发尴尬事。所以他特别提出里赫特的例子就不足为奇了。
从保留曲目本身来看,里赫特实在像是想要弹遍古往今来所有他热爱的音乐。他从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弹到格什温的协奏曲,从亨德尔的组曲弹到贝尔格的作品。如前所述,除了吉塞金之外,录音史上似乎很难有人能够与之相比。而在这份宽广当中,里赫特可以将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完整地反复演出,以至于留下至少三次现场录音,对于《哥德堡变奏曲》《帕蒂塔》等许多巴赫专家趋之若鹜的作品却始终不闻不问;将肖邦的《24首前奏曲》选着弹固然是“惊世骇俗”(他偏爱大调前奏曲),对于Op.10和Op.25这两套练习曲,钢琴家分别选弹其中一部分的做法却更有可能是道出了许多同行的心声。我曾见过不止一位名家表示,要将肖邦这些练习曲都弹到同一个高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早期的钢琴家就非常谨慎(戈多夫斯基中风前正准备灌录全集,惜哉)。
里赫特对于贝多芬的奏鸣曲、舒曼的作品——这些他最擅长的领域——各有取舍,而面对几乎是最强烈地体现其个人特色的舒伯特奏鸣曲,钢琴家又会在伟大的“三连作”(最后三首奏鸣曲)中单单跳过D959,简直让人遗憾到“无语”。由于里赫特手中独特的取舍实在太多,反倒无法展开来谈了。不过,钢琴家对于避开不适合自己的作品固然是无所顾忌,他的取舍却也并非单纯以此为准。里赫特还有两个诡异的习惯:一方面,如果哪部作品他听到了令自己满意的演奏,他就不会再弹那部作品了。据我所知,古尔德弹的《哥德堡变奏曲》,雅科夫·弗莱尔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还有里赫特的老师涅高兹演奏的贝多芬《“皇帝”协奏曲》就是这样的演奏;另一方面,钢琴家感到某些作品被演奏得很多了,他就不会再去弹。
里赫特曾表示,他不弹肖邦的奏鸣曲就是后一种原因。我猜想,钢琴家比较全面地弹了德彪西的前奏曲,却不弹《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或不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等,可能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总之,他这些习惯无论哪一种都会令热爱他艺术的人们长久抱憾。
贝尔曼
拉扎·贝尔曼弹李斯特《12首超技练习曲》的录音是传奇性的,他表示当初正是里赫特的杰出演绎让他深深地倾慕这些作品,但里赫特只弹了其中的八首。有一次两位钢琴家碰面,贝尔曼就问里赫特,为何他只弹八首呢?里赫特回答,因为剩余那四首自己并不喜欢。贝尔曼感到好奇,因为里赫特不弹的部分也包含那首《雪景》,而它正是贝尔曼特别喜欢的。“你怎么会认为《雪景》是不好的音乐呢?”贝尔曼哼唱起其中的一部分,“你不喜欢吗?”“我确实喜欢这部分”,里赫特回答,“但是这里(他哼唱另一部分)我完全不喜欢”。
对于这样的角度,贝尔曼是完全认同的,因为他自己也是如此选择自己的保留曲目。在他身上可能并没有混入里赫特那样的奇特想法,而是单独着眼于“喜欢/不喜欢”“适合/不适合”的角度来考虑,说实话,在这方面我佩服他更胜于里赫特。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二人在曲目范围方面的不同。里赫特的演奏曲目几乎是过于广博了,所以当他跳过某一部分的时候,对于整体的魅力全然没有影响。反观贝尔曼,他的曲目虽然也涵盖了古典时期的部分作品,以及某些现代音乐,整体上却仍是以浪漫派作品为主轴,算不得十分宽阔。在这种情况下,钢琴家大胆舍弃许多作品就更不容易了。贝尔曼是戈登威泽尔的学生,戈登威泽尔擅长演奏德奥古典作品,门下的弟子却有不少成为演奏浪漫派的专家。贝尔曼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通常来到戈登威泽尔、涅高兹这样的大师门下学习的时候,学生往往已具有较为成熟的演奏水平(里赫特是例外,他到涅高兹那里的时候,各方面的情况难以界定),贝尔曼却是在神童阶段就被直送到戈登威泽尔身边学习,从9岁开始,一直学习了十八年!
可以说,他是与这位超级名师关系最密切、最深厚的学生。但最终,贝尔曼仍旧成为独特的浪漫派大师,而没有继承戈登威泽尔的那种全面性。他也弹奏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却并不被视为钢琴家的长项。然而,当我们面对贝尔曼在李斯特《二十首超级练习曲》中怒涛万丈的表现时,不受触动几乎是不可能。由此我们认识到钢琴家在所擅长的范围内究竟能够成就什么,并很自然地希望能多听一些这样的演奏。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贝尔曼仍旧以鲜明的态度做出了取舍。由于在苏联灌录的《12首超技练习曲》,以及钢琴家为DG录制的全套《旅行岁月》,贝尔曼成为录音史上数得着的李斯特专家。可当有人建议他灌录全套《匈牙利狂想曲》时,钢琴家并没有接受,因为他单单喜欢其中的第九首,他只将这一首录了音。
在苏联之外,同贝尔曼合作最为频繁的当属DG,而钢琴家在这家公司的录音目录恰好反映其特立独行的选曲风格。贝尔曼侧重于李斯特,而少录肖邦,没有协奏曲、奏鸣曲,或叙事曲的录音,尽管他的风格似乎颇适合这些作品。钢琴家录下肖邦的六首波罗乃兹(没错,他只录了六首),略过了最后的《“幻想”波罗乃兹》。舒曼的作品则根本没有录。后浪漫派中,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倒是录了一些,包括全部六首《音乐瞬间》,还有少数前奏曲。看得出来,虽然勋伯格指出贝尔曼演奏拉氏的作品特别具有说服力,钢琴家还是在曲目方面有所保留。并且关于贝尔曼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还有一件趣事:钢琴家录完《音乐瞬间》之后,奥德萨的拉赫玛尼诺夫协会极为欣赏,居然将其当作“代理会歌”使用——每次开会前放一首。他们又写信给钢琴家,表达激赏之情,同时建议他灌录拉赫玛尼诺夫全部的前奏曲。贝尔曼原本也同意了,与Melodiya之间的协商也没问题,但最终,钢琴家发现许多前奏曲还是吸引不了他,因此这个录音计划仍旧是无疾而终。
出于相同的原因,贝尔曼也没有弹舒曼的《托卡塔》、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这些浪漫派钢琴家特别能引发听众狂热的作品。而在浪漫派以外,贝尔曼对比较现代的音乐也有他的取舍。以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为例,《第八奏鸣曲》是贝尔曼情有独钟的作品(他跟里赫特学的),现场记录和商业录音(DG)都有保存,可对普氏的其他奏鸣曲,他就很少问津了。
文章所提及的这几位大师都在录音史上拥有屹立不倒的地位,贝尔曼的地位可能不及前几人,但他在自己所专长的领域纵横一生,而不妥协以迎合市场与听众,也是一代超技大师的气派。当初想到“钢琴家避开了什么?”的主题,又选择这些巨匠来观察,并不是想要指出大师们也有弱点存在。正相反,观察这些人一方面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能坦然避开自己所需要避开的领域,其实让我深感一份对艺术的真诚。
如果这样的钢琴家都要为了艺术而有所取舍,许多钢琴新秀或自愿或为环境所迫,而在不适合的曲目中“苦苦挣扎”,是何等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