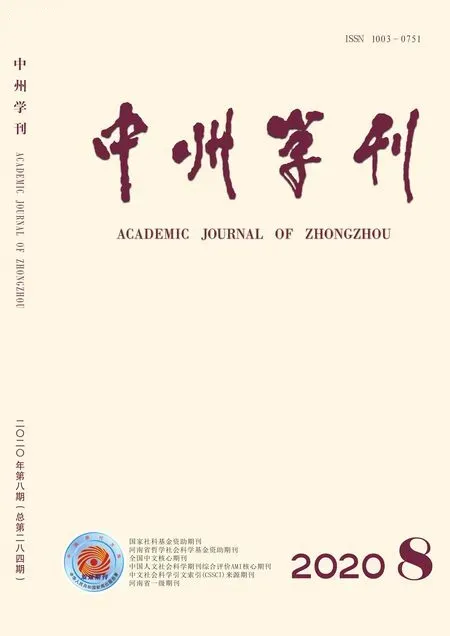《诗经》弃妇诗与凶丧礼*
罗 家 湘
以礼解《诗》,是郑玄《毛诗笺》开创的传统。在吉、凶、军、宾、嘉五礼系统中,能够与弃妇诗联系起来的礼是凶丧礼。从凶丧礼角度看《诗经》弃妇诗,可以发现,传统弃妇诗研究只关注了出妻、出妇现象,缺少对出母现象的关照,对弃妇诗的功用分析也多局限在对弃妇个人命运的哀叹,没有认识到其维护家庭道德秩序的价值。
一、弃妇诗当属凶丧礼
今人编礼书,把结婚与离婚放在一起。如钱玄《三礼通论》礼仪编之婚礼通释有“离弃与再嫁”条①。王贵民、杨志清编著《春秋会要》卷十四嘉礼婚礼下有“离异”条,且将《卫风·氓》《邶风·燕燕》当作典型例证②。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要》卷十九“婚嫁”条最后录《韩非子·说林上》卫女“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③的故事。王巍著《诗经民俗文化阐释》第十章中把弃妇称为特殊的婚姻形式,与抢婚、杂婚、对偶婚、自愿婚等并列④。这种分类受到现代婚姻法专设离婚章节的影响⑤,但不符合古代礼书的写法。
在吉、凶、军、宾、嘉五礼系统中,吉礼是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企图通过祭祀等手段建成自然与社会、神灵与人类、祖先与子孙相互沟通、和平共处的神人共同体。但是,在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嘉礼可以加强社会内部的团结,宾礼则接受来自社会外部的善意。凶礼用来处理社会内部有关纠纷,军礼用来处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嘉礼的功能是“亲万民”,其中的婚冠之礼是用来“亲成男女”的。夫妻离异标志着婚姻关系的解散,这与增进人们亲密关系的嘉礼的功能是相背离的。传统的礼书凡涉及出妇者,皆放在凶丧礼中论述。
如出妇服丧的义务,《礼记·丧服小记》分为五种情况:“妇当丧而出,则除之。为父母丧,未练而出,则三年。既练而出,则已。未练而反,则期;既练而反,则遂之。”⑥依据孔颖达《礼记正义》的解释,第一种是“正当舅姑之服时,被夫遣出者也。恩情既离,故出即除服也”。因此,出妇不必为原来的舅姑服三年丧。第二种是妇人自己的父母去世,按丧服规定当服期年齐衰,但未及十三月的小祥,妇人被丈夫休弃,回家后当随自家兄弟一起服三年斩衰丧。第三种是“既练而出”,亡父母小祥已过,出嫁女子已完成为父母期年服丧的义务,这时被休弃返家,“不更反服”。第四种是出妇正为亡父母服三年丧,还没有过十三月的小祥,却被丈夫召回复婚,这时只需服满期年齐衰就可以了。第五种是出妇为亡父母服丧已过小祥,被丈夫召回复婚,这种情况下,需要继续完成三年斩衰的义务。
至于子辈该如何服出母之丧,《仪礼·丧服》也有规定。若父在,“出妻之子为母”⑦当服期年齐衰之丧。《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出其妻,其子“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孔子就说:“嘻,其甚也。”⑧他认为伯鱼为出母服丧超过一年不对。《檀弓上》记载,孔伋(字子思)出其妻,其子孔白“母死而不丧”。人们觉得孔白的做法不符合《丧服》的规定,子思却赞同儿子的做法,给出的解释是:“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自从子思立制之后,孔氏就有了“不丧出母”的传统。郑玄认为这个传统不好,其《礼记注》云:“记礼所由废,非之。”⑨若父殁,“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丧服传》以为,为父后者“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唐贾公彦《仪礼注疏》释曰:“父已与母无亲,子独亲之,故云私亲也。”⑩但为丈夫服丧结束后又再嫁的女子,仍能得到前夫之子的尊重。《礼仪·丧服第十一》云:“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贾公彦释曰:“云‘父卒继母嫁’者,欲见此母为父已服斩衰三年,恩意之极,故子为之一期,得伸禫杖。但以不生己,父卒改嫁,故降于已母。虽父卒后,不伸三年,一期而已。云‘从为之服’者,亦为本是路人,暂时之与父片合,父卒,还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从为之文也。‘报’者,《丧服》上、下并记云报者十有二,无降杀之差。感恩者皆称报。若此子念继母恩,终从而为服,母以子恩,不可降杀,即生报文。”
唐代杜佑在《通典》中也将出母之丧放在凶礼类分条论述,如卷八十九下有“父卒母嫁复还及庶子为嫡母继母改嫁服议”“父在为出母服议”“父卒为嫁母服”,卷九十四有“庶子父在为出嫡母服议”“为父后出母更还依己为服议”“为人后为出母及出祖母服议”“为父后为嫁母及继母嫁服议”“为出继母不服议”“出母父遗命令还继母子服议”,卷九十五有“母出有继母非一当服次其母者议”“从母被出为从母兄弟服议”,卷九十六有“所后之母见出服议”,卷一百〇二有“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议”“母非罪被出父亡后改葬议”等条。根据这些礼书的规定,弃妇诗在礼仪性质方面应属于凶丧礼。
二、“弃妇”的一名三义:出妻、出妇、出母
以“弃妇诗”为诗题,首见于《玉台新咏》卷二所收录的曹植作品,其中诉说无子见弃的悲伤。清代陆奎勋《陆堂诗学》卷三中明确指认《诗经》弃妇诗,云:“《中谷有蓷》,《集传》从郑《笺》指为弃妇诗。”该诗郑《笺》云:“有女遇凶年而见弃,与其君子别离,慨然而叹,伤己见弃,其恩薄。”《诗集传》云:“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妇人览物起兴,而自述其悲叹之词也。”这两处都没有直接出现“弃妇诗”一词,只是说因遭遇凶荒年景而“见弃”“相弃”,“弃”不过是各自逃生的手段。诗中虽有对于人事的怨恨,但更多的是对遭遇自然灾害的伤悲。
《卫风·氓》“三岁为妇”,郑《笺》“有舅姑曰妇”。女子称妇,是因为她已出嫁有了婆家,离开婆家即为“出”。礼书用“出”字,把人们的思路引向“七出”之条,在女人身上找过错。在《诗经》注解体系中,“出”的身份,一般用“弃”字标出。如《邶风·谷风》毛《传》“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氓》毛《传》“华落色衰,复相弃背”,《中谷有蓷》毛《传》“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绿衣》朱熹《诗集传》“絺绤而遇寒风,犹己之过时而见弃也”,《谷风》朱熹《诗集传》“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氓》朱熹《诗集传》“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元代以后注释多用“弃妇”一词,如元代梁寅《诗演义》注解《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云:“荼虽苦而甘如荠,喻弃妇之苦有甚于荼也。”《诗演义》注解《小雅·小弁》“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云:“《谷风》作于西周之世,故此诗引之。弃妇之望于夫,屏子之望于父,其情一也。”元代刘瑾《诗传通释》总结《卫风·氓》诗义云:“愚按:此诗及《邶·谷风》皆弃妇所作,故其辞意多同。”明代曹学佺《诗经剖疑》解释《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云:“泾水浊,渭水清,兹虽泾渭之难分,然亦有水渚之清洁者,此弃妇之自喻也,岂遽能纯以渭浊哉!”弃妇一名具有三重含义,从夫妻关系退出为出妻,从婆媳关系退出为出妇,从母子关系退出为出母。合而言之,弃妇就是一个离家的女人。用“弃”字表达了对女性的怜悯之情,写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被动和无辜。
《诗经》弃妇诗表现了被丈夫休弃、离开婆家女子的情感状态与生活内容。根据徐中原的梳理,关于《诗经》弃妇诗篇章,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张亚权、边家珍、尚永亮、费振刚、褚斌杰五家。具体分类见表1。

表1 关于《诗经》弃妇诗的分类
以往对于《诗经》弃妇诗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出妇角色,关注出妇的权利与义务。这种研究有两点普遍性的不足:一是对于弃妇中的出妻与出母角色有所忽略,二是没有从礼制角度加以把握。
周公制礼作乐,其文化设计的根基在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既是一个可以安身的物理空间,又是一个人与土地、庄稼、牲畜共生互成的生活空间,还是一个家人之间情感凝成的精神空间。男女通过婚姻结成家庭,稳定的核心家庭由夫、妻、子三方构成。一个处于壮盛阶段的家庭必然具有分裂出新家庭的能力,丧失了分裂能力的家庭就进入其老年期了。如果将家庭看作一个生命体,它也具有生成期、发展期和衰老期。
如果在一个家庭的生成期夫妻关系解散,弃妇从家庭的物理空间退出较为容易。如果在一个家庭的发展期,弃妇是从家庭的生活空间退出,要切断的不只是夫妻关系,还有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等人际关系和个人与土地、庄稼、牲畜等形成的劳动关系,面对这种活生生的切割,大多数人都恋恋不舍,悲伤至极。如果在一个家庭的衰老期,弃妇主要面对精神上的割弃,原来的家庭亲情已无力维持或者不值得维护,弃妇需要以直面死亡的心情来承受个体人生价值被彻底否定的痛苦。
弃妇被迫离家后,居于社会边缘位置,也处于不定的生活状态,各种人伦关系被人为切断,失去参加各种礼仪的资格。弃妇诗关注的重点不在弃妇个人,而是家的破灭。古人把弃妇问题放在凶丧礼中谈,充分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极力通过礼的设计为弃妇回归家庭保留退路,守护家庭所代表的价值观念。
三、家庭生成期的“留车反马”之礼:保护出妻的尊严
父系社会逐渐养成女从男的婚姻形式,但对于男方的不信任普遍存在。《左传·桓公十五年》记载,郑国祭仲之女问母亲:“父与夫孰亲?”母亲的回答是:“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卫国女子出嫁时,母亲传授的秘诀是“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为了保护女子的尊严,家长在嫁女之时就要做好接回女儿的准备。具体的做法就是陪嫁一辆马车,为出嫁女儿留一条退路。而男方需要“留车反马”,留下送嫁车,送回拉车的马,表示自己能够完全承担照顾妻子的责任。《左传·宣公五年》记载,鲁叔姬秋九月出嫁到齐国,嫁给齐大夫高固,“冬,来,反马也”。何休作《膏肓》以难《左氏》,言礼无反马之法。郑玄《箴膏肓》引《诗经》等来证明“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车反马之礼”。孔颖达《正义》曰:“礼,送女适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马,谦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弃,则将乘之以归,故留之也。至三月庙见,夫妇之情既固,则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马,以示与之偕老,不复归也。……留车,妻之道也;反马,婿之义也。”婚礼中,男方有迎娶的婚车,女方有送嫁的婚车。三个月后成妇道,男方送还马匹,留下送嫁来的马车。
《诗经》婚礼诗解释多以留车反马之礼自明。如孔颖达《召南·鹊巢正义》云:“《士昏礼》‘从车二乘’,其天子与大夫送迎则无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车,故郑《箴膏肓》引《士昏礼》曰:‘主人爵弁纁裳,从车二乘,妇车亦如之,有供。’则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车也。又引此诗,乃云:‘此国君之礼,夫人自乘其家之车也。’然宣五年‘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反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车,故郑《箴膏肓》又云:‘礼虽散亡,以诗义论之,天子乘其家之车也。’然宣五年‘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反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车,故郑《箴膏肓》又云:‘礼虽散亡,以诗义论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车反马之礼。’”“故《泉水》云‘还车言迈’,笺云‘还车者,嫁时乘来,今思乘以归’,是其义也。知夫人自乘家车也。言迓之者,夫自以其车迎之;送之,则其家以车送之,故知婿车在百两迎之中,妇车在百两将之中,明矣。”《鹊巢》《何彼襛矣》《泉水》诸篇因叙及车马,用来证明留车反马之真。但《何彼襛矣》“王姬之车”,《箴膏肓》取三家诗说,以为“齐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车远送之”,总有些不妥。女儿长大,要出嫁了,其母当年的婚车质量真的有那么好吗?新娘坐一辆十余年前或更早造的旧车出嫁,心里真的愿意吗?徐正英先生将《周南·汉广》解释为“一首反映西周贵族留车反马之礼的乐歌”。其中“游女”为出嫁之女,贵族“成妇礼”有三个月的培训期,在女子进行三个月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训”期间,男子“言秣其马”“言秣其驹”,以礼相待。
留车反马之礼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杨秀礼先生将“反马”礼与《周易》卦爻辞结合解读,认为《睽》初九爻辞“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应该写的是主人嫁女之后,其送嫁之车马,与出嫁的女子一并离家不见,但不用着急追找,因为车马将会由人护送回来。如女子所见遇(出嫁)为恶人,她可随车马一起返回,故而不会得咎”。《中孚》六四爻辞“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也是说“三月庙见克成妇礼后,夫婿遣人将女方父母送嫁所用车马,送返女方父母”。有车马送嫁的女子,可以得到父兄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在夫家能受到尊重。留车反马之礼不仅让新妇有底气、有面子,而且也让她的父母放心。三月之内,即使姑娘被人嫌弃了,她也不用低声下气求人,坐着自己的马车回家就行了。
弃妇诗中最能体现留车反马之礼的价值。《卫风·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妇人大归时,所乘坐的马车应是当初送嫁时留下来的车子。这辆车与当初的迎亲车前后映照,可以证明确有留车反马之礼。有迎亲车,有送嫁车,说明嫁娶双方地位不低,至少经济上是宽裕的。该诗中的妇人拒绝私奔而要求聘娶,把做人的尊严看得比情爱重。当她发现丈夫“二三其德”“至于暴矣”,就主动坐着自己的送嫁车回娘家了。这不是被丈夫抛弃,而是妇人主动离去,因此周坊先生以为“旧说解此诗为弃妇诗,这也是不恰当的”。靠着父兄的经济支持,靠着当年留下的送嫁车子,妇人主动追求真爱,敢于为爱付出真情,愿意为爱忍受劳苦,但她又能不被情感迷惑,不受婚姻捆绑,一旦发现爱情丧失,她为了捍卫爱的尊严,坐着自己的车体面地离开夫家。一去一回,车成了维护女性尊严的关键道具。留车反马之礼虽然不能给予女性经济独立的地位,却为女性提供了捍卫人格尊严的条件。
四、家庭发展期的“三不去”规定:保障出妇的生存
中国古代社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维持了社会秩序。但女性被排除在很多礼仪之外,绝大多数时候属于“游离于主流社会和政治规范之外的群体——不定生活的群体”,动辄遭受暴力伤害和驱赶的威胁。《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卫女“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追求经济独立,成为一种罪过。插入夫妻关系中间的是“其姑”,也就是丈夫的母亲,媳妇的婆婆。中国古代盛行亲上加亲的姑表亲、姨表亲婚姻,婆婆往往是自己父亲或者母亲的姐妹。《诗经》中有几篇提到舅姑的诗,如《邶风·泉水》:“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小雅·伐木》:“于粲洒扫,陈馈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小雅·頍弁》:“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大雅·崧高》:“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但这些均不是弃妇诗。《大戴礼记·本命》讲“妇有七去”,第一条就是“不顺父母去”,因为这是以下抗上的逆德,会严重破坏家庭秩序。妇人若因此而被弃,只能是自作自受。因此,《诗经》中没有存留公然抱怨婆媳矛盾的弃妇诗。《卫风·氓》中“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这几句对妇劳与家暴的抱怨,可能有婆媳矛盾的影子在。
在男尊女卑的等级社会中,弃妇成为剩余的人。对于婚姻破裂、家庭关系无法维持的弃妇来说,如果爹娘健在有娘家可回,回娘家自然是好的选择。但也有无娘家可回或不愿意回去的妇人,对于她们来说,社会上并没有为她们提供独立工作的机会,她们也没有掌握独立生活的本领。为了保障弃妇的生存,礼中专门有“三不去”的规定。《大戴礼记·本命》云:“妇有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三不去”的规定为这些妇人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有所娶,无所归”一般指父母已亡故,只有兄弟在的妇人。妇人在家从父,父母亡故后,就成为孤儿。这时她被丈夫休弃,很难被兄弟接纳。《邶风·柏舟》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卫风·氓》:“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妇人被弃的痛苦无人理解,受到的侮辱无法洗刷,失去了家园无人接纳,漫长的未来无人依靠,怨怒、委屈、惶恐、伤心,一切只能暗自消受。为了活下去,她们不得不忍气吞声,苟全性命,离婚不离家。《柏舟》中的“静言思之,寤辟有摽”“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氓》中的“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写尽了妇人的痛苦和无奈。为了留住旧好,妇人抓住丈夫的衣袖不放,哀求他别分手。《郑风·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袪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妇人对于丈夫的新欢也有规劝,《氓》中有“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此四句写女主人公诚恳地劝告另外那个女子不要和有妇之夫纠缠,这会招来社会的非议,也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被抛弃的妇人对丈夫的新欢充满了羡慕、嫉妒和怨恨。《邶风·谷风》中言:“宴尔新昏,如兄如弟。”“宴尔新昏,不我屑以。”“宴尔新昏,以我御穷。”《小雅·我行其野》中言:“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有时弃妇会对前夫产生幻想,幻想对方有一天会后悔当初抛弃自己,会来哀求自己与他和好。《召南·江有汜》:“不我以,其后也悔。”“不我与,其后也处。”“不我过,其啸也歌。”有些绝望的女子会咒骂前夫,指责其人品不好。《邶风·日月》:“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小雅·白华》:“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被丈夫遗弃后,弃妇只能将自己的情感转移到生活空间里的动物和植物。《邶风·谷风》言:“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毋逝我梁,毋发我笱。”但这种带着偏执的劳作、护持,无法解开被弃留下的心结,反而不断加深弃妇情感的痛苦。
在《诗经》中,未见夫妻共同“与更三年丧”的记述,只有为夫亡守丧的记述。《桧风·素冠》写妻子见丈夫体枯肌瘦的遗容,抚尸痛哭,表现出“迸发的、肝肠俱裂的伤痛”。失去爱人的悲伤和对亡夫的怜惜,使得她那种“与子同归”的誓言显得非常真诚。《唐风·葛生》中的“独处”“独息”“独旦”者不仅指死者独处于墓地,也指生者孤居于家园。《仪礼·丧服》规定,夫死,妻为夫服斩衰之丧,“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菅屦”。三年丧服期间,寡妇常常来到葛生蔹蔓的墓地向亡夫倾诉,期待自己“百岁之后,归于其居”,能够与丈夫再次同床共枕,愉快生活。
弃妇诗多有妇人倾诉自己婚后的辛劳和家境前后变化,“前贫贱,后富贵”,自己却被赶出家门,以此指责男子无情。如《邶风·谷风》:“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卫风·氓》:“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小雅·谷风》:“将安将乐,女转弃予。”能共贫贱,不能共富贵,这就是人性。危难之中,贫贱之时,人们需要合力打破困境,因而往往谦卑恭顺,眼中多见他人长处。一旦享有富贵,人就会膨胀骄狂,对他人多出猜忌和轻蔑之心,觉得别人都在占自己的便宜。世事如此,婚姻也不能摆脱怀疑,保证信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的规定,提醒人们要抑制心中的恶念,多记住他人的好,行事留有余地。这样的规定有利于维持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五、家庭衰老期的再嫁与大归:呼唤对母亲的孝道
凶丧礼中,关于为出母服丧的讨论很多;弃妇诗研究却从未把出母纳入讨论范围,这是不合理的。上文已经阐明“弃妇”的一名三义,出母诗必然属于弃妇诗。古礼讲妇有“三从之义”,《仪礼·丧服》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妇无所从即为弃,出妻、出妇、出母都是离家的女人。丈夫去世后,妻子抚养儿女长大成人。但等到儿子们娶妻成家后,母亲却成为多余的人。《邶风·凯风》写到七子之母以再嫁的计划迫使儿子改变对自己的不孝态度,《邶风·燕燕》写到戴妫的亲子被杀,庶子州吁逼迫其离家,两个母亲的命运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春秋会要》把《邶风·燕燕》树为“离异”典型虽有些问题,但认为《燕燕》是写戴妫大归的诗,将其归入弃妇诗中是有道理的。小序云:“卫庄姜送归妾也。”《说文解字》:“归,女嫁也。”“归”的本意指女子出嫁,出嫁就是归家。家是中国文化给人指定的归宿。对于女性来说,“之子于归”,与丈夫共建的家才是真正的归宿。青年男女从各自父母身边离开,通过婚姻关系组成新的家庭,这是家的裂变,是社会生命扩张的方式,受到整个社会的欢迎和祝福。小家庭解散,妇人重回父母的家也叫归,称为“来归”或“大归”。《谷梁传·隐公二年》:“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大归曰来归。”何休注:“大归者,废弃来归也。”《左传·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大归意味着一个社会细胞的死亡,属于凶险的事情,需要有应急救助。一般情况下,夫死或子死才有大归,故归往死亡也是归的本来含义。人从自然来,死后又回归自然,自然如家。马瑞辰妙解《诗经》中的“归”字:“《尔雅》‘鬼之为言归也’,郭注引《尸子》:‘死人谓之归人。’《吕氏春秋·顺说、求人篇》注并曰:‘归,终也。’终亦死也。《说苑·反质篇》杨王孙曰:‘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葛生》诗‘归于其居’、‘归于其室’,皆以归为死。(《蜉蝣》)‘归处’、‘归止’、‘归说’义亦同。”顺从自然召唤,如同回家一样平静死去,这就是归人。有生成性的归,有死亡性的归,无论哪种归,家都是目的地。
出嫁之归与大归之归形成强烈反差,《邶风·燕燕》将二者并置以表达绝望的心情。前三章采用重章叠唱的手法,以“燕燕于飞”兴起送女出嫁的伤感,自然淳朴而饱含深情,具有鲜明的民间色彩,符合“至德不孤,善言必三”的民俗风格。第四章的风格则与前三章大相径庭,出现“仲氏”“淑慎”“先君”“寡人”等词语,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贵族特色。边家珍认为前三章是一首完整的诗,第四章是另外一首诗的结尾部分,显示出君王身份的语言特色。张剑从艺术风格、作者身份、内容以及叠咏章与独立章的关系等四个方面辨析前三章与第四章的巨大差异,继续佐证这一说法。林光华认为《燕燕》第四章遭到了后代学者的篡改,是强加的儒家思想,其目的是沾染儒家色彩,维护封建统治。李学勤指出第四章应该是散逸的《仲氏》一诗。基于李学勤的说法,晁福林进一步研究,认为第四章是混入的错简,属于《仲氏》散逸后的一部分。张慧芳认为这首诗“是庄姜‘且赋且作’的结果,即前三章是庄姜‘赋诗言志’,第四章是庄姜‘作诗言志’”,这种解释是符合春秋时代用诗传统的。
庄姜赋《燕燕》前三章送戴妫归于陈,符合春秋时代上层社会赋诗言志的交流方法。赵逵夫先生指出:“人们一般不是赋自己作的诗,而是赋《诗经》中的作品或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其他作品。”作为一名贵族妇女,庄姜在送别戴妫时,吟诵《燕燕》以表达自己的情意,这是正常的方式。在赋诗言志的过程中,赋诗者经常为了表达自我情感的需要而“断章取义”。庄姜赋《燕燕》,以送嫁诗送戴妫大归,也符合赋诗言志中“断章取义”的默认规则。首先,庄姜是齐国的公主、卫国的国母,而戴妫来自陈国,是卫桓公的生母,因此两人的别离除了私人情谊之外,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外交色彩,适合赋诗言志的场合。其次,《燕燕》是一首送嫁诗,与庄姜送戴妫大归一事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无论是出嫁还是大归,都涉及“女性”“婚姻”和“送别”等因素。最后,原诗中“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等部分诗句与“送别”的主题紧密相关,契合“断章取义”的基本要求,能够让对方明白自己所表达的意思,不至于造成交流上的障碍。总之,《燕燕》的前三章不是庄姜所写,而是她“赋诗言志”时“断章取义”赋过的诗。
《郑笺》:“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燕燕》第四章可看作庄姜“作诗言志”。《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女弟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庄姜因婚后无子,将戴妫生的儿子完视如己出。卫庄公死后,完继位为卫桓公,后来被卫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州吁所杀。庄姜与戴妫共同经历了丈夫死去、孩子被杀、逆贼掌权等重大事件,同病相怜,让二人成为好友。戴妫因丧子而大归,庄姜对戴妫的离去充满了难舍之情。这种对友人的惜别之情,往往掺杂着对自身处境的映射。面临同样的艰难处境,戴妫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在亲人的身旁寻求慰藉;而身为一国之母的庄姜却只能看着她离去,然后独自一人对抗朝不保夕的生活。清代李诒经《诗经蠹简》称:“如此痛哭是为戴妫,其实还是为自己也。”此评价甚是精妙。庄姜的眼泪不仅为一场别离而流,更是为自己而流。诗中“仲氏”指排行第二的人,一般用于兄弟之间,如《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庄姜称戴妫为仲氏,应是舍弃两人之间妻与妾的身份区分,而申之以同胞姐妹一般的亲情。“寡人”一词《左传》中多次出现,一般被认为是“寡德之人”,是国君的谦称。然而,“寡”字也有“嫡”之意,可指国君的正妻,如《大雅·思齐》中的“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诗传》曰:“寡妻,適(嫡)妻也。”孔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庄姜虽然无子且受到冷遇,但仍是卫庄公唯一的嫡妻,自称“寡人”并无不妥。庄姜自作正是《燕燕》第四章表现出贵族特色的原因。
庄姜“且赋且作”,于是有了《燕燕》的混搭风格。“诗中有诗”,于归的期待与热闹同大归的绝望与冷清形成强烈对照,戴妫大归,夫与子俱亡,庄姜与之同悲。戴妫返回陈国亲人的身旁,而庄姜失去唯一的朋友,其伤悲更深一层。诗中重提卫庄公的“先君之思”,表达了对失去的共同家庭的怀念。郎宝如考辨《邶风·燕燕》,认为“此诗前三章与末章是一脉贯通,前后呼应,不容分割的艺术生命体,合则神完意足,离则彼此俱残,根本不存在‘误合’、‘错简’的问题。”赋与作有风格差异,合为一体,则显示出一种奇趣,似乎离婚的队伍与结婚的队伍走了个头碰头,离婚大归的一方特别尴尬。而造成这种伤悲和尴尬的罪人是庶子州吁,《燕燕》因此成为对州吁不孝的控诉。
《邶风·凯风》也表现了母子之间的关系,《毛诗序》以为“《凯风》美孝子也”。“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寡母养大了七个儿子,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连一句问候辛劳的话都没有听到。真是养儿不如养鸟,养鸟还能听它鸣叫。“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寡母心苦身亦苦,“为劳苦而思嫁”,无奈之下,她提出“再嫁”计划,逼使七子自省自责其“颜色不悦,辞令不顺”,改变不关心母亲的态度,从此“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从编者角度看,把《凯风》放在《邶风》中,可以与《燕燕》构成对比关系,用《凯风》的七子自责行孝对照州吁弑兄逼母的横暴,加强对州吁不孝的批评。
六、余论
《诗经》弃妇诗不仅描写了弃妇处于社会结构边缘的不定化生活,表现了弃妇自我边缘化的心理,而且力图通过对尊重、怜悯、孝顺等家庭伦理道德的认同,把弃妇重新纳入社会秩序中。这种努力值得赞赏。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社会秩序的基点在家庭。家庭是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群组织,具有许多重要的社会功能,如生育功能、生产功能、教育功能、医护功能、祭祀功能等。《诗经》以家为归,女性的嫁与归是一个以家为归宿的小循环,人类从生到死是一个以家为归宿的大循环。个人是家的成员,不作为单独的权利单位。家包容个人,保护个人,个人努力回报家,建设家,个人成就首先体现在支撑家。家为秩序之核,国是家的扩展形式。
古礼把弃妇问题放到家庭中来思考和解决,为当事人保留体面,让参与者感受到社会温暖。家庭是以血缘联系构成的社会组织,其权利等级自然形成,容易被人接受。古代社会通过家庭建设实现社会建设的目的,社会统治成本较低。但是,血缘家庭的封闭性,必然导致内部压制和外部争夺,对于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的维护有不利的一面。弃妇问题不能放在保护个人权利的现代法律体系中解决,那样很难保障解决方案的公平。
注释
①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93页。②王贵民、杨志清:《春秋会要》,中华书局,2009年,第309页。③杨宽、吴浩坤:《战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④王巍:《诗经民俗文化阐释》,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6—255页。⑤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全文共分为8章,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共27条。198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第四章“离婚”下,包括第31—34条离婚,第35条复婚,第36—38条子女抚养,第39—42条财产处理。⑥⑧⑨〔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96、1281、1274页。⑦〔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04、1104、1104—1105、964页。〔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页。〔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吴兆宜注,成都古籍书店影印世界书局1935年版,1980年,第39—40页。〔清〕陆奎勋:《陆堂诗学》,“续修四库全书”第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2、325、303、324、331—332、284、298、763、1101、301、302、302、301页。〔宋〕朱熹注:《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12、15、26页。〔元〕梁寅:《诗演义》,夏传才主编:《诗经要籍集成二编》第11册,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29、153—154页。〔元〕刘瑾:《诗传通释》,夏传才主编:《诗经要籍集成》(修订版)第11册,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明〕曹学佺:《诗经剖疑》,夏传才主编:《诗经要籍集成二编》第19册,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32页。徐中原:《30年来〈诗经〉“弃妇诗”研究综述》,《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八辑),学苑出版社,2015年。详见张亚权:《试论〈诗经〉中的弃妇诗》,《镇江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边家珍:《〈诗经〉弃妇诗探析》,《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尚永亮:《〈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学术论坛》2012年第8期;费振刚主编:《诗经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褚斌杰:《诗经与楚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傅隶朴以为“车马分言,是用的互见法”(《春秋三传比义》中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165页),但据《诗经·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车,《泉水》“还车言迈”等经注,车并没有同马一起送还。〔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72、1872、1861页。徐正英:《诗经学公案再认识》,《光明日报》2017年1月5日。杨秀礼:《〈周易〉“丧马”为“反马”婚俗考论》,《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周坊:《〈诗·卫风·氓〉新解》,《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蓝江:《身体操演和不定生活——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朱迪斯·巴特勒》,《西北师大学报》2019年第5期。〔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255页。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388页。〔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67页。〔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436页。〔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第575页。边家珍:《〈邶风·燕燕〉是两诗误合》,《学术研究》1988年第2期。张剑:《关于〈邶风·燕燕〉的错简》,《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林光华:《〈诗经·邶风·燕燕〉质疑与文化阐释》,《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李学勤:《〈诗论〉与〈诗〉》,《清华简帛研究》2002年第2期。晁福林:《上博简孔子〈诗论〉“仲氏”与〈诗·仲氏〉篇探论——兼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张慧芳:《〈诗经·邶风·燕燕〉新解》,《美与时代》2019年第8期。赵逵夫:《论先秦时代的文学活动》,《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30—31页。李诒经:《诗经蠹简》,《丛书集成续编三辑》,中华书局,1987页。孙世洋:《试论〈诗经〉诗篇结构的“诗中有诗”现象》,《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郎宝如:《〈邶风·燕燕〉“错简说”考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