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态危机与技术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科学技术
作者简介:谢玮璐(1997-)女,汉族,广西钦州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关系的分析
马克斯·舍勒等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我们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我们的灾害的根源”,将生态危机归咎于科学技术,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明确指出生态危机不是由科学技术本身引起的。
威廉·莱斯认为“科技在人类面前就好比处于被利用的角色,仅仅是人类征服自然、驾驭万物的一枚棋子”,否定生态危机的产生是由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舍勒等人认为科技是“灾害的根源”,而莱斯认为真正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源是使用科学这一工具的人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即某种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而非科技本身;科学控制自然的功能只是现象,科技本身只是控制自然的手段和工具。在其著作《自然的控制》一书中,莱斯明确指出造成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然”的观念。根据他的考究,“控制自然”观念最初来源于基督教教义——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类由此对其他生命具有的派生统治权,而后文艺复兴运动发展了这一观点,并最终由培根奠定了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与之相适应的,人们对科技的关注开始向控制自然转变,以利用科技获取自然隐藏的财富。“控制自然”的观念与现代科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并在资本增值的逻辑下被祛魅化,“社会成为唯一有意义的和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的支撑结构”。在此观念的支撑下,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崇敬,自然界沦为了纯粹人类满足非理性欲望的对象,技术则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攫取工具。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技术被异化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最终造成了技术的异化与生态的破坏。同时,在“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下,资产阶级技术通过将外在需要不断内化为人自身的需要使人成为丧失自身意志而纯粹追求物质欲望的奴隶,技术由此不但成为控制自然的工具,而且转化为控制人的工具。
本·阿格尔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咎于异化的消费观和技术观。他从分析资本主义的消费入手,指出正是由于资本逻辑所打造的消费观膨胀了民众的物质欲望,使得资产阶级无节制地运用技术来掠夺自然资源,以期不断扩大生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欲,技术由此成为资本控制自然、剥削自然的“帮凶”。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为了延缓自身经济危机,通过大力宣传消费主义价值观诱使人们将自身价值与幸福程度与物质商品消费联系在一起,同时由于异化劳动施加给人的痛苦,也使得个人把对物质商品的消费作为释放自身本性的唯一手段,主动从物质消费领域寻求虚假的幸福,致使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最终导致生态问题的出现。
戴维·佩珀认为技术作为人类开发自然的工具,本身对自然是无威胁的,关键在于运用技术背后的人所处的社会制度。资本的增殖逻辑决定了它的反生态性,生态危机因此产生。这一危机是在资本驱动下导致的,而非科技本身所造成的。
而对于技术悲观主义所要求的放弃技术、返回前技术时代以谋求生态危机的解决的态度,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持否定态度,他指出:“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相比起极端地征服自然,又或彻底放弃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更为重要。
既然明确主张生态危机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那么就不存在仅仅依靠技术就能解决当前危机的可能,因而技术乐观主义所主张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依靠技术手段得到解决的观点,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同样也是不现实的,他们认为那种以为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只是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幻觉。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运用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
福斯特在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对能否依靠科学技术克服生态危机的问题作出了回应,明确指出技术进步所实现的高效利用只会造成资源消耗总量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致使这一结果出现的原因在于为使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资本家会借由技术发展来降低生产成本,但在资本逐利本性的制约下,生产规模的扩张不会停止,因而只会导致更多资源的消耗。资本本身利润绝对优先性的逻辑决定了无法依靠资本主义技术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只会选择与其逻辑发展相符的技术,而不会选择那些不能固有现存社会关系、即便具有更多环境合理性的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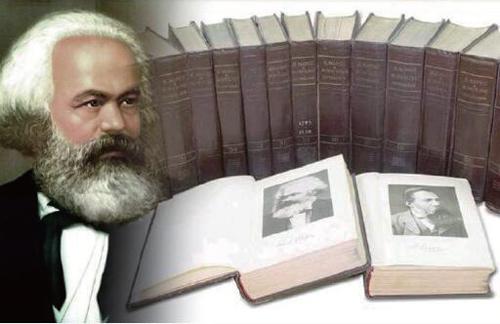
高兹结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将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的技术观和经济理性观,同样指出资本主义对技术的选择不会遵从生态友好的原则。高兹明确反对“技术中性论”,但肯定了科技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提倡将科技分为“遵从经济逻辑的技术”和“温和美丽的技术”。他认为,前一种技术被用以开发自然资源、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这种技术的发展目的是使资本主义通过控制其达到对人的控制;而后一种技术则主要是新型技术,對环境友好,甚至有助于当前生态危机的改善,但这种技术往往具有潜在的反资本主义性质,因而资本主义在对技术进行选择时,只会考虑服务于自己的、即“遵从经济逻辑的技术”,而非考虑技术的运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和原则决定了技术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进行运用。资本主义生产虽然要依托自然系统,但“自然”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归宿,“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产技术将会是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经济功能也决定了技术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运用。正如福斯特所说的那样,生产技术的进步虽然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了能耗,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无限扩张性决定了技术进步不过是加速了对自然的剥削进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快速扩张必然与地球有限生态系统之间产生矛盾冲突,而资本主义所鼓吹的消费观念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冲突,由此,生态危机出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生态化出路的探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既不在于限制经济增长,也不在于否定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技术,以及我们如何实现这种选择。
莱斯通过对“自然的解放”的论述,明确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和谐而非控制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与自然和谐生存并不意味着拒绝现代文明和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同时也不能将之理解为对现代科技的拒斥,而应该是“消除浪费性的生产和对环境的破坏”。而对于“自然的解放”的实现,莱斯从两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必须改变使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功能日益突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不仅使科学技术成为控制自然和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而且也必然导致对人控制的加强和社会冲突的加剧。只有建立一个广泛的公民社会,避免控制自然的科技为少数人所占有,才能真正实现自然的解放。其次,要将技术从非理性运用的处境中解放出来,推动其本质和功能的生态复归,就必须寻求从“控制自然观”到“生态道德观”的转变。在此,莱斯强调的是一种伦理观念的觉悟和进步——“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理解,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學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控制自然”不应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伦理或道德的发展,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即要求重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限制人的非理性欲望,在利用技术开发自然时应充分尊重自然系统的内生价值,停止把“人类技术的本质看作统治自然的能力……应该把它看作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只有把“控制自然”理解为对人的非理性需要和欲望的合理控制,让技术在伦理道德的指引下,更好地为人类与自然地解放服务,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解放,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阿格尔从消费领域分析了技术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要把技术从资本主义扭曲的消费观中解救出来,就必须重塑马克思主义的需求理论,正确处理人的真是需要与商品消费之间的关系,抛弃将幸福标准与商品消费挂钩的观念,建构起适度的消费观念。阿格尔认为新消费观的建立一方面是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压力驱使下,主动关注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从资本主义宣传的虚假消费中觉醒,审视内心真正的需求,自觉以“够了就行”的消费原则来置换受资本迷惑的“越多越好”的价值原则;另一方面,新消费观也受马克思“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的启迪,人们逐渐摆脱幸福与商品消费有关的影响,转向从非异化的劳动中寻求真正的幸福。
在技术本身的改造上,阿格尔倡导用小规模的分散化技术来取代现有的规模宏大的集中型技术。在资本逐利性的鞭策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技术正朝着规模化、大型化的方向发展,以越来越暴力的姿态向自然掠夺,摧残着生态环境与人类个体。为了遏制技术当前这种破坏性的前进趋势,阿格尔在批判继承舒马赫“中间技术”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小规模技术”代替资本主义大型工业社会那种资金密集、高耗能同时又节省劳力的“大规模技术”的主张。在这里,阿格尔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指的是介于原始技术与高新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这种“小”技能能够主动顺应生态系统的平衡规律,并且在资源的选择上倾向于可再生源,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技术是“‘民主的技术‘人民的技术——一种人人可以采用的,而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专有的技术”。这种技术服务的是人类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削弱人的个性与创造,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
高兹通过对“科技中性论”的批判来展开自己对技术生态化出路的探寻。在高兹看来,“技术中性论”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技术是服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而在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下,技术进步不仅不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而且加快了自然资源的耗费,导致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生态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高兹主张以生态学为指导来对技术进行改造,用社会主义的“软技术”代替资本主义的“硬技术”:他把技术分成资本主义独裁式的“硬技术”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软技术”。前者奉行资本主义一贯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具有规模化、集中化、专制化的特点,与民主背道而驰,易造成技术独裁与严重的生态问题。而“软技术”则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有望技术的生态化。和阿格尔的“小技术”有类似的特点,高兹的“软技术”也具有生态性,符合自然界的演化规律,以实现人类自身解放为终极追求,是一种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小规模、分散化、人性化的技术。
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指出要使技术从奴役自然的状态转向保护自然的状态,就必须将“反对‘坏的技术与追求‘好的(替代)技术的斗争必须联合起来……当今反对‘坏的技术的斗争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发生在工作场所和社区之中,例如,‘知情权和‘节约资源运动;第二种是指现存机制之外发展替代技术的运动。”。因此在奥康纳看来,对“坏的技术”的避免主要通过民众对技术运用后果的知情权以及发展替代技术来实现。对于替代技术,奥康纳主要从新能源与新产品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在新能源方面,奥康纳指出由太阳能所孕育的新技术可以摆脱目前由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能源技术所造成的困境;在新产品方面,奥康纳特别强调了农业中的“新林业”替代技术,即通过自然手段来取代有害化学制品的使用,从而克服对环境的影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思想的价值
在技术与生态的关系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技术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反对把科学技术运用的消极后果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也因此明确了限制经济增长或者技术进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技术时的立场与方法,对技术的批判并不停留在技术本身,而是指向了技术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既突破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全盘否定技术的“技术原罪论”,也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盲目相信技术的技术乐观主义。这对于人们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努力压制其负面影响而充分利用其正面效益给予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在论及技术的生态化出路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限于从技术本身来谈论克服技术异化现象,而是强调应从技术本体及其背后的社會条件相联系来探究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根源,由此探讨技术克服异化、转向生态的途径。这为我国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调整传统的技术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的生态化发展提供了多样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生态道德观、适度消费观等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发展新型技术类型的主张,对于审视现有价值观念以及技术的生态,进而推动生态文明宣传、构建绿色社会,实现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思想的局限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并倡导构建生态道德观、适度消费观,这对于当前生态文明理念的塑造、驱动技术转向具有启发意义,但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影响,这些主张蕴含着浪漫主义的空想色彩。首先,莱斯认为要改变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关键在于伦理道德的重塑,将变革“控制自然观”寄希望于通过伦理道德教化,期望以此来规范技术活动。这样的观点虽然对于重新审视当前的工具理性,进而实现技术的生态重构具有启示意义,但对于如何进行这种伦理道德教化以达到他所提出的道德理想状态,莱斯并未论及。而阿格尔对资本主义的消费价值观的批判值得肯定,但在论及如何建立适度消费观时,则将变革的希望寄托于人自身对资本异化的消费方式的觉醒和对自身真实需求的自觉认识,这无疑是对人类自觉力量的理想化设想,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难以实践的乌托邦色彩。
在对技术生态转向的设想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明确了技术异化是资本增殖的必然要求,但在他们所提倡的克服技术非理性运用的路径中,仍然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过分倚重小规模技术,漠视了技术发展的现实和客观规律。从当前的技术发展来看,技术规模化是必然趋势,而且成为处理生态问题的有力手段。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小规模技术的片面呼吁,违背了客观现实,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技术异化问题时,笼统地将缘由归咎于现代文明的整个科技体系,因而主张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实行统一的生态技术类型。这一提倡既漠视了各民族利益的差异性,也没有看到各国在技术水平发展上的差异,因而这样的解决之法同样是难以实践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浪漫的空想性。
参考文献
[1]王雨辰.技术批判与自然的解放——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04):96-102.
[2]威廉·莱斯著,岳长龄,李建华译.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107-108.
[3]秦龙,祝玲玲.生态马克思主义技术生态转向的四维辨识[J].国外社会科学,2019(06):36-47.
[4]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5]赵志强.生态批判与绿色解放: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探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03):11-14+20.
[6] 穆艳杰,廖婧.论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在逻辑[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60-66.
[7]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徐琴.技术:全球生态的灾星抑或救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与局限[J].哲学研究,2013(06):31-37.
[9]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0]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威廉·莱斯著,岳长龄、李建华译.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2]本·阿格尔著,慎之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4]舒马赫著,虞鸿钧、郑关林译.小的是美好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5]朱波.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