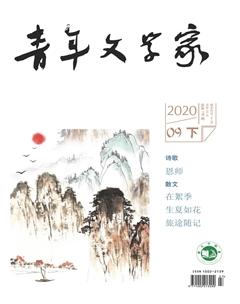古代诗词文学互文性意境对现代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
摘 要:古代诗词文学作品中具有互文性意境,为了进一步分析互文性的意义及作用,本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实践分析过程中,本文立足古代诗词文学互文性意境对现代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结合进一步探索,旨在全面提高古代诗词文学互文性的研究效率,从而进一步推进古代诗词文学艺术的有效发展及对现代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古代诗词;互文性意境;审美价值
作者简介:郑昕(1987-),女,汉族,陕西咸阳市人,西安工业大学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美学、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7-0-02
引言:
现代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多方面,从文化传承与发展角度分析,现代文化艺术中包含了一定的古代诗词文学互文性意境。在有效分析古代诗词文学互文性意境过程中,应该重视结合文化艺术的现代化发展,并有效进行具体研究,从而提升古代诗词文学艺术的分析能力。
一、古代诗词文学互文性意境分析
“互文性”又可称为“文本间性”,最早由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提出。他认为,任何文本的构建均来自于引言组合,都是对其他文本的理解和转化。此后索莱尔斯又对互文性进行再次定义:每个文本均与其他文本具有内在联系,并对上述文本产生强调、转移和深化等方面的作用。互文性理论包含作品间相互交叉又依存的关系,突出基于文际关系对作品意义的挖掘和理解。这一理論的阐释更为丰富,也引起了业内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被多数流派吸收和运用,并在文学、语言学及文化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广泛推广,成为当代影响力较广的批评理论之一[1]。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互文理论,并引起学术界较大反响,围绕互文开展的学术研究不断被挖掘,该理论也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各高校也纷纷围绕互文性开展学术讲座、学术论坛等活动。我国古代对文本的理解更具灵活性,且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体系,相比而言,西方在文本理解和解读方面的发展并未达到理论层面和深度。
我国诗词中极为讲究意境的创造。理想的意境能够将现实的生活与作者的情感进行有机交融,从而形成更具艺术水平的境界。在古代诗词中,意境能够表现出作者的灵感和思想,从广义层面分析,古诗词的意境能够体现作者与读者两方面的意图,前者由作者的审美观念和评价能力决定,而后者则由读者的审美水平决定。古诗词中的意境具有两个更为突出的特征,即情境交融与虚实结合。前者是对诗词意境的具体表现,作者通过对真实而具体的人、物与事件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情感。而后者则是意境的结构体现,作者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构建更为深刻的意境,从而实现对诗词内涵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3]。
二、古代诗词文学互文性意境对现代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
(一)古代诗词文学中自然美对现代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
对诗词的重要品评标准之一便是其审美和思想境界的自然性。我国历代诗词作者大多追求作品自然天成,能够更为真实地刻画与反应自然事物,自然表达心境和思想。自然的美感能够给人以最舒适的心里享受,也是古诗词最高的审美境界。
首先,自然美并不是单纯指自然生态中的美感,同时也指真情实感带来的美感。我国的传统审美思维更为崇尚自然之美,主张万物均能够从自然的思想和情绪出发去描摹和创造,这更符合老庄的无为思想。庄子在《天道》便极为推崇“朴素”之美,认为没有雕饰的美更为自然和纯粹,也更具有艺术水平。而王充将其中的“朴”也解释为自然形态的树木,具有未经雕琢的自然美感。自然朴实便能够流露出难得的美感,这也是我国历代文人所追求和向往的艺术境界。
其次,与自然无雕琢的美感相对应的是人类的生存理念。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应为和谐共融,而不是单方面的征服和占有。因此文学创作的最初思想也是将自然作为情感的亲近对象,将较高的审美追求和诗意的创作融于生存方式中。无论哪种思想主张,均认为生存的意义为现实环境,是具有真实的审美性的真实生活,并将这种无雕饰的思想和情感体现于诗词中,通过写景状物表达出作者对自然美的追求和展现,营造出具有自然之美的互文性意境。
再次,诗词中的自然与人类情感的和谐之美。人类生活的世界是富有情感的环境,广袤的世界具有自身的生存规律和法则,但人们并不将其作为无情的容器,而是一个充满丰富情感的真实的世界。人与环境相互依存共生,人作为天地的产物一方面迎合世界的发展规律生存,另一方面也在生存的过程中表现出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为世界增添属于人的情感,让生活更有意义[4]。这种情感与自然共生,符合自然的规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欣赏,共同形成具有自然之美感的创造。但这里所谓的自然之美并不完全是对自然形态的移植,而是经过人工创造和修饰的艺术境界,人们将自己对自然的理解融于作品中,通过思想和情感的表现展示平淡、朴实的审美意境。从这个层面讲,自然之美是巧妙装饰后的朴素,是去掉修饰的自然,也是通过最为原始和朴素方式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审美技艺。其中蕴含了更细致的推敲,最后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又不会表现出拙劣的修饰痕迹,是古诗词最高的艺术形式。
综上所述,自然之美于当今人类看来过于简朴,过于陈旧,现代人一味追求丰富性和现代性,但却忽视了人最本真的初衷。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过程中,人们获得的是疲惫的身心,无趣的生活,此时再反观简朴的自然之美,不正是古代人大智慧的体现吗?因此这种将自然融于情感和生活的艺术形式,是更值得现代人研究和思索的。
(二)互文性意境中含蓄美对现代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
首先,我国的汉语言文学之所以博大精深,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其表达意义的含蓄性。这种含蓄指的是以委婉的方式进行表意,不将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更具有思考性和更加耐人寻味,因而也衍生了后期的研究价值。艺术领域中的含蓄更加委婉具有耐人琢磨的情愫,故而我国古诗词中含蓄的表达增添了诗词的审美效果。在诗词创作中运用含蓄的表达方式,对于作者来说是其高雅艺术修养的体现[2]。含蓄表达营造的审美意蕴能够营造出更为美好的世界,无论作品流传多久,都会让后人通过字面意义无限遐想其背后的丰富内涵,让人百读不厌,是后人的精神向往。
其次,含蓄的表现手法即是艺术表现风格的一种形式,也是人类普遍掌握的艺术规律。如王安石的诗句:浓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从枝头的一点红便可窥见春天盎然的升级,引起人们对春色的无限遐想,营造出具有含蓄之美的互文性意境。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含蓄之美便是要求作品中不完全通过字面来传达所有的内涵和意义,而将其中一部分信息保留,非直白的表述能够为读者预留出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空间,使读者产生更大的探索欲望,通过每个受众主体对作品的不同解读,来进一步丰富作品的思想内涵,从而获得审美过程中的快感。
再次,表达的含蓄之美主要体现于言外之意,象外之象。老子的“大象无形”和庄子的“至乐无乐”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家更为推重无言之美营造的审美意境,主张在文学中不能仅通过有限的言辞表达思想,更需表现出作品的内在意境,这种意境的营造往往比文字对信息的传播更为深远。文学艺术所带给人的美感体验并不完全依赖文字,语言表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无限的是意境的传达,这便能够实现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
含蓄并不体现于作品的表达形式方面,更直接關系到作者的思想深度。如陈子昂在创作《登幽州台歌》时,读者并不能判断作者的思想是悲观还是乐观,如果在文辞中明确表示出来,便不会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作品具有的含蓄之美正是作者思想深度的体现。所以,后人在诵读这篇经典诗作时,也会产生更多的遐想,通过对艺术的再体验和再创造,获得新的美感和艺术审美感受。
(三)互文性意境中营造的新奇之美在现代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
杜甫曾评价自己的诗作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表现出诗人对诗词新奇美的推崇和追求。我国历代文豪均意识到创新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因此便格外推崇新奇之美,不断尝试以创新或独特的方式实现文学表达和意境创造的高峰。
对新奇美的追求可追溯到远古神话。人类在早期生活繁衍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自然现象的客观认识和理解,便编制了美好的神话,将人类对自然的新奇表现于神话中,营造出具有新奇之美的意境,从而体现古人的审美情趣。新奇美主要通过创新来实现,文学创作历来不推崇复制和模仿,而主张将个人的新意融于作品中,表现出作品的独创水平。杨万里主张“文章必自名一家”,这样才能作为传世佳作,值得后人不断品评赏析。其中的自名一家,便是指不能一味模仿他人,而需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文章中体现出创新精神,并将这种风格发扬和传承。
但需注意的是,我国的文化和思想受儒家的影响颇深,因此在追求新奇之美的过程中,主要表现的是“不奇之奇”,从真实的意境中发现新奇,使新奇更具有正向的积极意义,而不是怪力乱神。人们通过对生活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发现未知、体验新奇,并将这种体验总结到作品中,通过互文性意境的营造传递出新奇之美,让读者感受到作品的独特魅力,这也是作者创造力的集中体现[5]。我国诗词作品种类众多,且各具特色,如果不具有新奇之美,也便失去了其文学和审美价值,因此新奇之美可作为诗词的灵魂和核心,表现出古诗词的艺术创造和审美价值。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古代诗词文学互文性意境在诸多方面对现代文化艺术的形成和创造具有较为深刻的意义,探索古代诗词文学互文性意境应该结合实际,要体会古代诗词所表达的深刻意境,并对其进行有效探索。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现代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需要加强对于文学作品互文性的理解能力,尤其是重视分析古代诗词文学中的互文性意境,掌握文中互文处的意境及其发展脉络,将更有利于理解和把握现代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庞伟.从诗歌的音乐美探究古诗词朗诵的技巧[J].传播力研究,2019,3(12):165-166.
[2]席云舒.从诗与音乐的关系及诗歌功能的转变看诗体流变[J].文艺评论,2019(02):46-50.
[3]王毅.缘情与尊体: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历史演变[J].河北学刊,2018,38(06):106-111+125.
[4]陈琳琳.论中国古代诗词的图像诠释——以明代《诗馀画谱》为中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04):6-13+209.
[5]郭诗宇.互文性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翻译[J].绿色科技,2017,(17):206-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