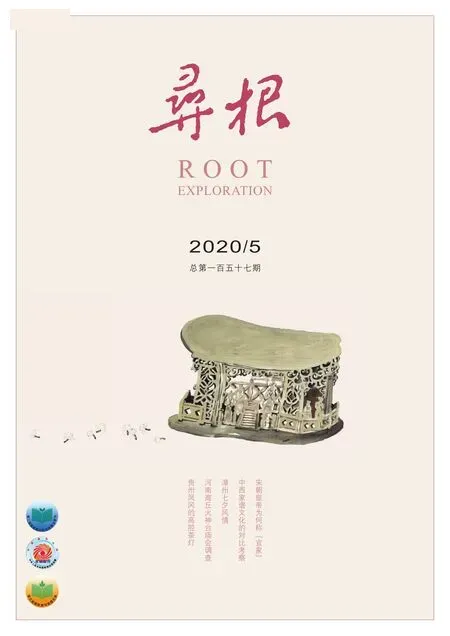宋代的开封府
□任崇岳
赵匡胤禅代后周,建国号为宋,都城仍旧设在东京。但在立国之初,有人主张设在洛阳,赵匡胤也犹豫不决。朝廷之间曾展开过一番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主张定都东京者占了上风。原因很简单,谁拥有了开封,谁就掌控了隋唐大运河,也就有了交通和漕运优势。一个叫李怀忠的官员献言说:
东京有汴梁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
宋代东京人口众多,在百万左右。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说“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如此庞大的人口,养活几十万军队,粮秣供应是一个棘手问题,倘不是江淮之米漕运至京城,北宋政权便无法运转,在当时具备漕运优势的城市只有东京开封,因此北宋定都开封,乃是历史的必然。
京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首善之区,地位自然重于其他城市,曾权知开封府,后又任过参知政事的张方平说:“臣闻王都者,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枢会,譬一人之身,则京畿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腹心宜泰,支末处劳,养身之道也。先安京畿,后康四方,理国之体也。”
既然京城如此重要,遴选京城的长官当然也非常严格,既要求对朝廷忠贞不贰,又要求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敏捷干练的办事能力。但是,要求归要求,知开封府者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鞠躬尽瘁、为民请命者固然不少,如包拯、范仲淹、寇准、欧阳修、蔡襄、张方平等人,但茸无能、随波逐流者也大有人在,真可谓是良莠并存,贤愚互见。
开封府长官的官称
同是开封府长官,但官衔并不完全相同。如宋太宗赵光义在即位前封晋王,因他是赵匡胤胞弟,身份自与别人不同,建隆二年(961年)以泰宁节度使兼殿前都虞侯再兼开封尹、同平章事。同平章事或称同平章军国事,位在宰相之上,不常设。赵匡胤、赵光义之异母弟廷美以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又任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中书令,侍中品阶极高,不常授,只是荣誉衔。太宗次子元僖封陈王,为开封府尹兼侍中。宋真宗为皇太子时封寿王,判开封府。宋钦宗以皇太子为开封牧。宋代制度,凡以亲王为开封尹者为“判南衙”。所谓“判”是指二品以上的京官或带有中书省、枢密院的职衔担任官职较低的知州、知府者。以上几人均官居一品,他们兼职开封府尹,故称“判”。因为他们是亲王,出行时威风凛凛,侍从甚众,填满街衢。《清异录》中说,每当他们出行,“羽仪散从,灿如图画,京师人叹曰:好一条软绣天街”。除亲王之外,宋初只有昝居润、吴廷祚、沈伦3人判过开封府,他们都是以宰相身份管理开封府的,时间是在宋朝初年。太宗以后,便没有人判开封府了。还有亲王为开封府尹时皆在南衙视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权知开封府事周起上奏说,陛下即位前常在南衙办公,为臣不敢居此,于是南衙不再成为府尹办公之地。
除了判开封府,还有知开封府、权知开封府、权发遣开封府等名称。所谓“知”是主持之意,知开封府就是主持开封府的事务。宋代的政治制度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官大多是由中央派人以朝内官的名义担任,故称“知某府事”“知某县事”。也有一些地方官不是派朝廷内官担任,而是由其他渠道担任者,叫府尹、县令。所谓“权”是指暂代职务而非正式官职,经正式任命后,再根据寄禄官的官品确定是行、守、试。担任比本职级别低的职务叫行,级别低而官职高者叫守,试是指官员试用期为1年,合格后转为正式官员。又因为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在即位前任过开封府尹,后世主政开封府者均不再称开封府尹,而称权知开封府了。所谓“权发遣”也是宋太祖赵匡胤定的名目,把资序低、隔两级而委以重任的官员叫权发遣。明乎此,可知同是主持开封府政务,称呼却不相同,《宋史》中欧阳修、李穆、吕夷简、钱若水、吕嘉问、蔡襄、王存等人是“知开封府”,包拯、寇准、范仲淹、陈尧咨等大多数人是“权知开封府”,傅求等几个人则是“权发遣开封府”。
调动频繁的开封府长官
开封市博物馆庋藏一通《开封府题名记》石刻,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二月,下迄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闰二月八日,主政开封府的共有183人次,可见人事更迭之频繁。各人的任职情况也不尽相同。大部分人是正常调动,也有因受排挤而任职开封府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范仲淹。他从贬谪之地回到朝廷,职务是天章阁待制、吏部员外郎。天章阁是收藏宋真宗御制文集、御书之地,长官称待制,员外郎是吏部下属机构司一级的副长官,长官称郎中。范仲淹遇事敢言,每论国事,便慷慨陈词,不吐不快。宰相吕夷简恐怕他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派人对他说,你的官职是待制,议论国家大事,不是你的职责所在,请勿多管闲事。范仲淹说,待制虽然不是纠察邪恶的官员,但关乎国家大事,不能闭口不言。吕夷简见没法阻止他,便调他权知开封府,那里事务繁忙,范便不暇他顾了,一旦办事有疏漏,便可将其免职,逐出京城。范仲淹于是走马上任开封府。不过开封府的任命也有随意性。宋仁宗时唐介知谏院,诤谏不避权贵,因与右丞相不合,请求去地方任职,被任命为知荆州。但敕命经过门下省时,被掌管银台司的何郯退回,他认为唐介并未失职,不应贬出京城。但他谏官的职务已免,于是朝廷便命他“留权开封府”,即留在京城权知开封府。还有毛遂自荐者。真宗朝毕士安知开封府时因事请求辞职,翰林学士宋白跃跃欲试,真宗便让他权知开封府。还有因吏治清明而擢升为知开封府者,如宋真宗时薛田,原为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未几,擢知开封府”。天雄军所在地的大名府是宋代的北京,地位虽然重要,但不如东京开封显赫,由地方官员调任京城行政长官,当然是升官了。

◇开封府题名记碑
走马灯似的官员更迭,不利于京城的长治久安。任职长者有1年多的,也有几个月的,甚至十几天的,要想在任上大有作为,真是戛戛其难。唐介刚刚权知开封府,“旋因论罪陈升之,亦出知洪州(今江西南昌)”;范仲淹在开封府任上,处之弥月,京师肃然称治;韩绛知开封府,“浃日又迁详省”,浃日者,10天也;宋白知开封府,“自倦于听断,不半岁亦罢去”,他嫌断案麻烦,任职不到半年,便挂冠而去。还有虽获任命却称病不到职者,如宋真宗时盛度“迁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以疾不拜,改会灵观判官”;还有刚获任命又遭罢职者,如宋神宗时李师中“权知开封府,既而以师中不允人望,罢之”。所谓“不允人望”,是说他在众人眼中,不具备知开封府的才干,因而刚上任又被免职。官员任职时间短暂,不可能有效治理京师。除此之外,任职官员中有两度权知开封府者,宋仁宗时的王素、宋神宗时的吴居厚;有3次执掌开封府,如英宗时的傅求;有父子先后任职的,如真宗时的李若谷、李淑父子,吕夷简及其子吕公绰、吕公弼、吕公孺、曾孙吕嘉问均曾任职开封府。徽宗时权知开封府梁子美上奏说,臣曾祖梁颢、祖父梁适曾领开封府事,臣今又任此职,恐怕德薄能鲜,不堪负此重任。徽宗夸奖他说:“卿三世尹京,缙绅盛事也。”
名士治理开封府
执掌开封府的官员贤愚不一,良莠不齐,政绩自然不能同日而语,后世的评价也就大异其趣。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一书记载:
开封府有府尹题名,起建隆元年昝居润,而晋王、荆王以下皆在焉,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
凡是来开封游览的人,都来摩挲刻有任职官员姓名的《开封府题名记碑》,包拯的名字被人摩挲的次数最多,石头凹陷了,因此指痕甚深,这表明人们对清官的敬重与仰慕。包拯也确实是享誉千秋、妇孺皆知的人物,他刚正不阿,恪守官箴,戚畹贵族不敢以私事相求。他办事稳重,不苟言笑,让他开怀畅笑一次,比让黄河浑浊的河水变清还难。但他又待人谦和,儿童妇女皆知其名,称呼他为“包待制”。这是因为他曾任过天章阁待制。因他清正无私,不接受请托,京城里有谚语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按照惯例,凡有诉讼之事,不能直接来到包拯问案的堂前,得先到大堂门口登记,有人收了讼牒再转给开封府尹,这样一来,收讼牒的人就可上下其手,收受贿赂。包拯到任之后,下令告状人可径直走到堂前陈述曲直,那些想从告状人手中渔利的官吏也不敢为非作歹了。京城中的权贵之家在惠民河旁建筑园林台榭,侵占了河道,以致河道淤塞不通,一旦下雨,京城中一片汪洋,成了水乡泽国。包拯下令悉数拆除那些侵占河道的园林台榭,权贵们为之敛手,谁也不敢找包拯求情。还有权贵伪造地券,想继续侵占河堤上的土地,包拯审验清楚,戳穿他们的骗局,并一一弹劾,使他们受到了惩处。
开封府尹中两袖清风、为民请命者甚多,只是没有包拯的声名显赫而已。范仲淹上任后,京城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倚仗权势,依旧恣行不法。范仲淹铁面无私,依法行事,一些蝇营狗苟之徒想乘范仲淹刚刚上任之际兴风作浪,都被绳之以法,其他人受到震慑,不敢再以身试法了。范仲淹上任只一个月,偌大的京城便“肃然称治”,秩序井然了。京城中有谚语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一时范仲淹声名鹊起,誉满京城。欧阳修继包拯之后,掌管开封府,治理办法与包拯不同,一切都循规蹈矩,按规章行事。有人建议他应效法包拯,欧阳修说人的才能性格各有短长,不能让人舍所长取所短,欧阳修治理京城同样得到了人们的称赞。李穆在太宗时知开封府,他“剖判精敏,奸猾无所假贷,由是豪右屏迹,权贵无敢干以私。”他死后,太宗叹息说:“穆国之良臣,朕方倚用,遽兹沦没,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神宗元丰年间,王安礼(王安石弟)知开封府,判案果断,雷厉风行。在他之前开封府案件堆积如山,久滞不决,已经拘系下狱而未结案者有几万人。王安礼不惮辛劳,对案卷爬梳剔抉,处理得当,不到三个月,牵连几万人的案子全部结案,无一错案,“三狱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系皆空”。一些棘手案件,他都一一剖析停当,不冤枉一人,京师之人称他为“神明”。神宗皇帝有几个儿子接连夭殇,掌天文历法的太史上奏说,庶民百姓家的坟墓离京城太近,因而不利于皇嗣,神宗马上下诏,让百姓改迁坟墓,这牵涉到数十万家的坟墓,百姓怨怼不已。王安礼进谏说,周文王当政,把掩埋百姓家的死者当作大事,以此来维系人心,没有听说过迁别人家之坟以利自己子孙者。神宗听了,连忙取消了这道诏令。
有一次,巡逻探事的人收到了匿名信,信上控告京城有一百多家图谋不轨,打算造反。神宗把此事交给王安礼处理,要他从严惩治。王安礼查验谋反事由,情节基本相同,最后一封控告信上加了3个人,其中有个姓薛的。王安礼把那人找来问,你得罪过什么人吗?姓薛的说,前天有人来抛售毛笔,被我拒绝了,那人怏怏而去,面露怨恨之色,匿名信可能是此人所写。王安礼把那人拘捕审讯,果然是他所为,当即枭首于市。京城人物都啧啧称赞。有个叫赵令的皇室成员,花了数十万买来一个小妾,此人是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把小妾玩腻了,便把她撵回了娘家,又诉诸开封府,索要当初买人的钱。这分明是恃势讹诈,那妇人只是掩面啼哭,一言不发。王安礼看那妇人,脸上伤痕斑斑,花憔柳悴,甚为妇人不平。他当即上奏神宗说,妇人之所以售价数十万者,是因有花容月貌,如今她脸已破相,不会再有人娶为小妾,这与炮烙之刑何异?该女子不应偿还其值,赵令应受到处理。神宗见王安礼说得有理,下诏停止给赵令发放俸禄,以示惩罚。京城百姓莫不拍手称快。
后宫从商家购得覆盖杂物的油箔,双方商定,如果在三年内油箔损坏,商家必须照价赔偿。结果不到一年,油箔便有损坏者,后宫派人拿着油箔来到开封府要求赔偿,宫人仗着自己来自宫廷,说话时声色俱厉。王安礼不为所动,对宫人说,油箔应放在干燥通风之处,宫中的油箔是否放在阴暗潮湿之地,被风雨淋坏所致?如果真的如此,商家便无利可图,赔偿的约定便不具备法律效力了。王安礼不再受理此案,宫人只得空手而还。从此以后,京城中的皇室国戚都对王安礼忌惮三分。
仁宗天圣年间,程琳权知开封府。上任不久,蜀中大姓真宗刘皇后的姻亲王蒙正之子王齐雄在京城居官,他打死了家中仆人,却威胁死者妻子以病故上报给开封府。程琳仔细察看报案者的脸色,见她悲悲切切,痛不欲生,知道她有难言之隐,便命人重新勘验死者尸首,得知是捶楚致死,人命关天,便上报给了朝廷。刘皇后自然袒护王齐雄,对程琳说,王齐雄非杀人者,杀人者是王齐雄家的另一仆人。程琳说,奴才无独断自专之理,他必然是得到主人的授权,才敢行凶杀人的。王齐雄虽不亲手杀人,但下令杀人应与杀人者同罪。刘皇后无言以对,指使仁宗把王齐雄调往他处继续为官。御史中丞蔡齐挺身而出上奏说,王齐雄杀人一案,程琳已审理清楚,只因他是皇太后姻亲,犯了杀人之罪,未受惩治,只是改调官职,这是以恩废法,臣期期以为不可。仁宗说,降他一级官职,可以吗?蔡齐说,如此一来,朝廷之法如同儿戏,朝廷还会有威信吗?仁宗默然不语,只得依法治王齐雄的罪。
同样在仁宗时期,王臻知开封府时,奸邪之人伪装成皇城司的探听消息的人,编造谎言,恐吓百姓,敲诈钱财,京城庶民苦不堪言。王臻经过缜密调查,打听清楚了这些人的姓名,先是拘捕,然后在脸上刺字,流放远方30余人,京城恢复了正常秩序。针对京城诸衙门办事拖沓的弊端,王臻又上奏说,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合称三司,统筹国家财政)和开封府诸曹参军(各州县长官的僚属,如南朝文学家鲍照就当过参军,人称鲍参军)、赤县(宋代把县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赤县是京城所管的县)的县丞、县尉都是戚畹贵族子弟,骄惰成性,不懂得如何办理政事,请求更换成孤寒之家出身,熟悉政事且品德端正之人担任。仁宗答应了他的请求。王素也是在仁宗至和年间执掌开封府的,有一年淫雨连绵,蔡河决堤,浊水灌入城中,仁宗慌忙下诏堵塞朱雀门,把水堵在城外。王素上奏说,城外居民庐舍甚多,倘若堵塞河道,水流不畅,岂不淹没更多百姓?不待仁宗批准,便下令不再封堵朱雀门,河水也未造成危害。
像包拯、范仲淹、程琳、王臻、王素这样的官员还有不少。如仁宗朝蔡襄知开封府,他“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英宗朝吕溱知开封府,他“精识过人,辨讼立断,豪恶敛迹”;吴奎在仁宗朝知开封府,他“达于从政,应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孙氏经商赢利,凡欠他钱的人,孙氏都巧取豪夺,低价弄走其财物,甚至抢掠妇女作抵押。吴奎得知后,把孙氏兄弟贬往淮、闽服劳役,其他豪猾之人再也不敢敲诈百姓了。3个月之后,京城肃然称治。沈遘在英宗朝执掌开封府,他“敏于政事,号称严明”。在他之前任职开封府的官员,早晨剖决政务,到黄昏时还未办完,甚者连饭都顾不上吃。沈遘在任时,上午处理政务,到日中(中午)时便已处理完毕,下午“出谢宾客,从容谈燕”,京城翕然称治,士大夫交口称誉,赞他为才能卓越之人。
治理开封多风险
东京开封作为京城,是皇亲国戚、高官勋贵、豪绅富商聚集之地,执掌开封府要做到公正公平,使权贵们满意,委实不易。徽宗时李伦掌管开封府,刚正无私,人称“李铁面”。一次,朝廷中一位官员犯法,应当追究责任,但那位官员有权贵撑腰,竟不肯到案,李伦甚为愤怒,略施小计,把那人骗到了开封府。那人到案后,又大放厥词,不肯认罪,李伦大怒,依律惩治。几天之后,李伦忽然接到通知,说是奉圣旨推勘几起案件,其中一案牵连到开封府,须李伦前去御史台作证。当时御史台大门朝北,开封府大门朝南,两个衙门只有一路之隔,只消片刻便可到达。但有人引着李伦绕道而走,曲曲弯弯,竟由巳时走到酉时,到达御史台时,已是暮色苍茫的黄昏时分了。李伦看到了那里审讯犯人的骇人场面,又被领到另一处听狱卒拷打犯人的号哭之声。李伦惊魂未定之际,又有官吏问他审判朝廷官员是根据祖宗的哪条法规。折腾一夜,至次日凌晨方才放出,李伦已是疲惫不堪,步履蹒跚了。隔了数日,李伦不明不白,又被罢了官。宋代官场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
开封府尹中也有人品差池、能力不逮之人。吕夷简曾孙吕嘉问知开封府时,把祖父吕公弼议论王安石新法不当的奏疏稿子拿给王安石看,导致吕公弼被贬谪出朝,吕氏族人称吕嘉问为“家贼”,不让他入族谱。
程琳初知开封府时有胆有识,审判刘皇后姻亲王齐雄杀死奴仆一案,赢得了许多人称赞。但后来因心生杂念铸成大错,被降职贬出京城。原来已故的枢密副使张逊有宅第在武成坊,他的曾孙张偕年方7岁,乃赵宋皇帝宗室之女所生。此时张家已沦落贫窭,无米可炊,他家的乳母拿出房契打算卖房,程琳见宅第宽敞,又在城市中心,打算购为己有,便心生一计,派人晓谕乳母,说张偕年幼,须得宫廷同意,才可卖房。张偕的乳母便去宫中求见太后,太后给她盖上了御宝。程琳见手续完备,知道万无一失,这才买下了房子。又让手下人买来木材装修房屋,又买来婢女伺候。不巧的是,那个替程琳买木材、买婢女的手下因贪赃被捕,御史台审理案件时查出了程琳设计买房的内幕,被降职,贬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去了。
还有一个叫傅求的人,英宗朝执掌开封府,他性格平恕,胸无城府,操守纯正,判案公正,所至之处,均有可称道之处。但是到了老年,精力不济,判事往往出纰漏。开封府内有一个叫钱吉的官员,因与妹妹发生口角,一时失手,竟将妹妹打死,被邻居告发。这本是一桩明明白白的杀人案,昏聩的傅求却断不清楚,反将告发者责打一顿,京城人惊诧不已。另有几件案子,也断得不公。御史台的官员弹劾他不能胜任知开封府之职,于是被贬往外地任职。还有自己清白而被儿子辈搅坏者。真宗朝咸平年间慎从吉权知开封府,受命之日,真宗告诫他说,京城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凡办事要三思而后行。办事太速则容易误判,办事太缓问题便会迟迟得不到解决,须仔细斟酌,寻找适中可行之策。还有一条,不要接受别人的请托,这样你办事才能鉴空衡平。慎从吉叩头唯唯听命。上任几个月后,咸平县(今河南通许县)民张斌妻子卢氏,控告侄子张质醉酒骂人,从而引起纠纷。张姓是咸平县豪族,张质是张家养子,他自知理亏,忙向县中官吏行贿。慎从吉之子任大理寺丞的慎锐正督运石塘河,经常往来咸平,因大理寺是审判决狱的机构,他也留意这个案件,与咸平县令商议之后,判张质恢复原姓,改名刘质,仍与养母卢氏生活在一起。张质与卢氏均不服这一判决。因咸平是开封府的属县,县令无法决断,便把此案上报给了开封府,慎从吉命户曹参军吕楷到咸平县推问。卢氏的本家叔父卢昭一贿赂吕楷白金(银子)300两,希望判卢氏胜诉,吕楷犹豫不决。卢氏的哥哥卢文质又贿赂慎从吉长子、大理寺丞慎钧70万缗,慎钧把此事告知父亲慎从吉,求他偏袒卢氏,但隐瞒了自己受贿之事。卢氏仗着本家叔父和兄长均已行过贿,官司胜券在握,便到开封府催促尽快结案。卢昭一的兄长卢澄曾给慎从吉的妻兄钱惟演写信,让他转告从吉,此案牵连到从吉的两个儿子慎钧、慎锐,处理此案要缓一缓。那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之子,随父归宋后颇受重用,曾官拜枢密使,是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因此卢澄才给钱惟演写信。慎从吉见事情发展成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麻团,便将此案上报给了御史台。御史台很快查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慎从吉被削职勒停,钱惟演罢翰林学士,从吉之子慎钧与户曹参军吕楷免官刺配郢州(今湖北江陵县)、衡州(今湖南衡阳),慎从吉另一子慎锐与卢氏之兄卢文质降一级,卢氏本家叔父卢昭一与卢氏之兄文质被决杖发配远方服劳役。《宋史·慎从吉传》称他“临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务察。多请对陈事,上谓其无隐”。这样一位能干的官员,却被儿子、亲戚害得丢了官。
东京作为都城,政务繁剧,远远超过其他州郡,不少人不胜其扰,要求去职。真宗咸平年间,知开封府温仲舒“以京府务剧求罢,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真宗朝毕士安知开封府时,一官员恃势强娶民家女子为小妾,毕士安判民家女返还其父母。那位官员是皇亲,天天在天子面前哭诉,毕士安“因求解府事,上许之,复入翰林为学士”。英宗朝知开封府冯京请求辞职,英宗问大臣韩琦,冯京因何要求辞职?韩琦回答说:“京领府事颇久,必以繁剧故求去尔。”又问京为人何?琦曰:“京在开封府岁余,处事无过,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英宗问冯京人品如何,韩琦说,他知开封府一年有余,处事公平,没有过错,在朝廷高官中值得嘉奖。韩琦并未言过其实,冯京的确是位清官。
北宋时期东京开封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也是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与知开封府诸多人的经营擘画密不可分,开封城的繁盛也浸润着他们的心血!
——包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