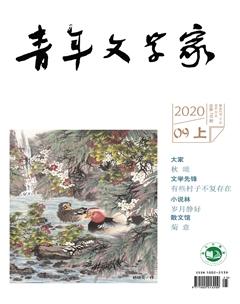铁匠父亲
贾维中
父亲过世已经三年多了,可我至今还没有悟透父亲,不知道该怎样为他界定。
父亲十八岁就随师父打铁,学徒三年,半作三年,而后才收徒开炉。父亲对手艺精益求精,即使自己做了师父,也不断向人拜师学艺。因此,父亲的手艺日益提升,只要一开炉,生意总是源源不断,以至有些乡亲认定只买父亲打的铁具。
父亲打的菜刀,削铁如泥;父亲打的锄头,铲泥如豆腐……父亲特别讲究嵌钢和淬火两道工序,父亲说,刀锄好不好用,关键就在这里。尤其是淬火,火候很要紧,刀锄烧到多少温度淬火,淬多久,都要恰到好处。但那个时代没有温度表,全凭父亲自己的经验。我想,他师父肯定教过,但更多的是他自己反复摸索。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父亲淬火,红红的铁块刺啦一下插入水里,冒出很多水泡,升起一股热气,让我感觉很新奇。
父亲的脾气很坏。他打的铁具好用,定价比别人要高,四邻乡亲慕名来买,不免要还还价。可他三言两语就会发火:去去去,这价我不卖,你们去别家买!我的印象中,父亲从不肯让价,人们因此送他一个绰号,叫“精头鸟”。但我依稀记得,也有过一次例外,有位姓袁的邻居,大家都知道他家很穷,他要买一把锄头,父亲不仅让他赊账,还主动给他降价。
不该赚的钱,父亲不会去赚。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人半夜敲门进来,要父亲打一批小尖刀(即匕首),父亲当即回绝说,这种杀人凶器,师父没教过,我不会打。
我八岁时,和母亲妹妹们回永康老家居住,记得过了新年我就去村里小学上学了。从那以后,父亲就没给我留过什么好印象。
父亲每年只在年底回家过年,过了年没几天,便又回福建去,渐渐地很少给家里寄钱了。小学三年级,我学会写信,但每次写信,除了通常的问候,就是向父亲要钱。父亲每次都是五元十元的汇,好像怕我们乱花钱。这年的冬天,母亲生下我第三个妹妹后做结扎手术,结果做完手术,就落下了病根。可父亲还是老样子,没有寄更多的钱回来,家里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
父亲的吝啬也是远近出名的,人家给的他都要,让他给人家却怎么也舍不得。就连母亲买件紧要的农具或家具,他都不想掏钱,说话也很难听:你就知道要钱!父亲打的铁具,母亲一辈子也只用到过两件:一把火钳,一把大柴刀。
父亲总在腊月最后两天回家,一到家就诉苦:怎么晕车,怎么冒雪从金华步行回家,打铁又怎么辛苦。母亲总是忙不迭杀鸡炖汤给他补,鸡肉的香气弥漫小小的屋子,我们兄妹几个眼巴巴瞪着鸡肉看,喉咙里不断地咽着口水。可父亲只管吃他的,不会夹一块给我们解解馋。我们几个孩子给他端汤递水,动作稍微慢点,一个凿栗就会落下来。一次我很生气,摸黑出门躲进一个大门洞里,被他找到好一顿毒打,至今额头留下一個斑痕。父亲还美其名曰:棒头出孝子,当时我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了绝不赡养他!
可我没有践行小时候的誓言。69岁时,父亲得了肺结核,服用一个月的免费药,结果肝也吃坏了——肝炎阳性。住在传染病房里,别的人怕传染,都不敢去探望,是我和母亲一直照顾。出院后继续吃药,换成自费的,一直吃了一整年。每个月都要验血检查,无论在外多远,我都赶回乡下送他去医院。毕竟他是父亲,生了我养了我。父亲最后几年,是活得很痛苦的,肺结核留下后遗症——肺气肿。最后一次住院,父亲的肺里痰淤积太多,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一直打着呼吸机,到咽气的时候也没给我们什么交代。
整理父亲遗物,有两张定期存单,连利息不过3万元,另有百元面额的旧纸币一百张,还有叮当作响的一袋硬币,五百多元。父亲视钱如命,吝啬一生,给我留下了乡下的一栋旧房子,还有就是这些钱了。当母亲和妹妹把这4万多元钱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五味杂陈,泪水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