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的边界
陈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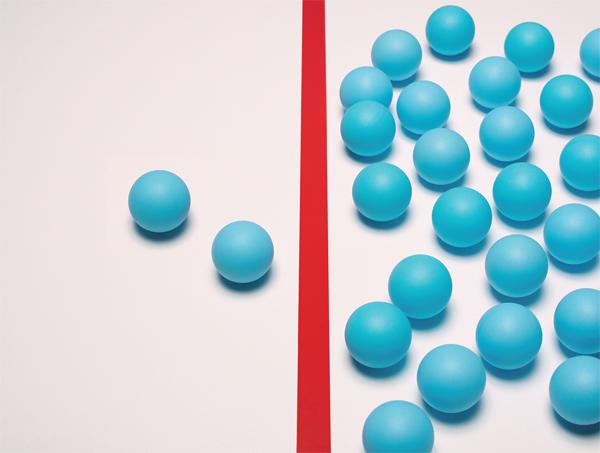
刑法的任务是保护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秩序。
——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新类型的案件也层出不穷。对于这些案件,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是否需要动用刑法来进行规制往往也会引起不少争论,比如先前的南京一女子利用航班延误骗保300余万元究竟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等。在关于罪与非罪的众多辩护理由当中,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往往是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条,甚至大有动辄以“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来为每个案件辩护之势。事实上,刑法的确应当具有谦抑性,但是刑法的谦抑性也并非就可以适用于每一个个案,更不能在刑事辩护中被滥用。
对惩罚主义的批评
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概言之,便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还涵盖了几大子原则,包括法律主义、禁止溯及既往、禁止类推解释、处罚的明确性以及处罚的适正性。其中,处罚的适正性要求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亦即刑罚法规只能将具有处罚根据,或者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以限制立法权,进而限制司法权。
所谓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被称为最后手段原则,指的是刑法应当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及程度,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其实,作为一个舶来品,刑法的谦抑性在国外的刑法学界也存在非常热烈的讨论。比如,德国的刑法学者就认为,刑事法律若要有效,也必须满足一般法律的生效条件。对于刑事法科学来说,还存在其他关于“良性的”或“正当的”刑事法律的要求,其中一项便是刑法必须满足“最后手段原则”。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民事或者行政的法律手段不能很好地实现立法者的目标的情况下,国家才可以将刑法作为最后的手段加以运用。
另一方面,近年来,人们开始对过度的惩罚主义给予谴责。这种谴责间或用于揭示刑法法规、刑罚裁量或刑罚执行体系中某一特定的趋势:若是指向人的情形,批判者主要责难的是人们对于刑罚的过度需求,尤其是过多不必要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创设;而遭受非难的若是刑法法规、刑罚裁量或者刑罚执行中的趋势,则意指刑法条文过多或者刑法过于严厉的倾向。
伴随着对惩罚主义批评的,是关于“现代刑法”的讨论。一些批评者不无尖锐地指出,现代刑法愈发脱离法治国思想的限制,转而向“安全刑法”发展,从而跻身范围广大、以预防为导向的安全法之列。他们据此进一步指出,这种所谓的“现代刑法”具备了持续向各种领域扩张,相较出罪的情形,有更多新的犯罪化形式不断涌现;设立扩张的或可被诠释的新法益,尤其是普遍法益;大范围的犯罪前置化,包括处罚未遂和预备行为,以及引入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长足跃进;一味强调刑法的预防目的等特点。显然,站在批评者的立场来看,如果立法者在动用刑法手段的时候,不曾事先确定其他法益保护的可能性效果已然不佳,便会违背最后手段原则,从而招致惩罚性立法的非难。
不论采取何种立场都不能否認的是,刑法是法律领域中,国家对公民最严厉的侵犯形式,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只有在其他所有手段都无可指望之时方可动用。而现在,批评者在许多地方都看到了违背最后手段原则的现象,谴责立法者并未将刑法作为最后手段,反而作为优先选项,甚至在有些场合下是作为唯一的手段进行使用的,这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
刑法的美德是宽容
法律不理琐细之事,这是一句古老的西方法律格言。指望依靠刑法来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并不现实,犯罪的治理亦属同理。德国著名刑法学者冯·李斯特曾经指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很多情况下,相比于使用刑罚,除去会成为犯罪诱因的社会原因才是有效防止犯罪的手段。同时,针对违反规范的制裁也是同样的,法律制裁之外还有社会制裁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意思的是,有观点认为,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日本的刑罚显得相对宽缓得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社会制裁更加强有力。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该国对于禁止乱扔烟蒂的规定。东京都的许多辖区都有禁止丢弃烟蒂的条例,对违规者采取的措施大致分为四类。其一,对违规者规定了罚金。比如《新宿区防止乱扔空易拉罐及道路上吸烟危害的相关条例》第14条就规定,在环境美化重点建设区域内的公共场所乱扔空易拉罐和烟蒂的,处以2万日元以下罚金。其二,对违规者规定了行政罚款。比如制定于2002年的《安全、舒适的千代田区整备生活环境相关条例》,该条例不仅禁止在道路上禁烟区域内丢弃烟蒂,也禁止在道路上吸烟。其三,是对违规者下达矫正命令。比如《目黑区无烟蒂街道共建条例》就规定,劝告违规者采取必要措施改正违规行为,对不遵从劝告者,命令其遵从劝告。其四,没有特别规定。比如2005年修改前的《中野区防止乱扔烟蒂、空罐的条例》,其主旨在于,乱扔烟蒂的行为是道德问题,不宜对其进行制裁。
我们很难想象,警察会满大街地追查随地乱扔烟蒂的行为,也无法想象公诉机关会就乱扔烟蒂的行为积极地进行起诉。从这一点来说,以刑法规制乱扔烟蒂的行为效果显然不佳,甚至可能会存在因此成为闲置条款的可能性。对此,有学者甚至打趣道,怕被虎吃掉,才心生畏惧;而如果知道是假老虎,无非就是感觉被戏弄了。因此,尽管行政罚款等手段属于相对来说较轻的制裁手段,但实际结果却可能更为有效。因为对于行为人来说,这样的制裁更能让行为人感觉到痛。
由此可见,保护法益的手段多数存在,而刑罚是所有制裁手段中最为严厉的,但是另一方面,其社会成本也大,故而常常被比作副作用强的药剂。因此,使用刑罚应该限于其他制裁手段不充分的场合。
谦抑的边界
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但是问题在于,也绝不能就此认为刑法的处罚范围越窄越好。相信不会有人反对,不论刑法如何谦抑,也不可能对故意杀人的行为谦抑,不可能对强奸、猥亵之类的罪行谦抑。因此,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法治国家而言,盲目实行“非犯罪化”,同样不具有合理性。
前文提及的南京女子“薅羊毛”一案中,就有不少学者结合刑法谦抑性原则进行辩护,进而指出该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但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在于:首先,尽管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但并不意味着对于每一起个案都要优先考虑是否能够适用其他法律,换言之,它不属于处理个案的具体规则。我们应当承认,一般的违法行为,比如民事、行政方面的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并不是对立关系,很多时候是存在竞合关系的。比如,经常会有学者论及的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的关系问题,民事欺诈固然并不都是刑事诈骗犯罪,但是刑事诈骗犯罪难道就不会包含民事欺诈的要素?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既然大多数的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案件,可以说都能在民法上找到相关法律依据,如果处处都要考虑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否就意味着所有这些案件都必须优先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纠纷?恐怕这在实践中并不可行。因此,具体要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最合适的方法,还是要对其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对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进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分析,从而得出犯罪与否的结论,而不是仅仅以刑法的谦抑性否认犯罪的构成。
其次,即便每一起案件都应当优先考虑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处处都应当考虑运用民事、行政手段是否能够解决争端,那么就會出现任何案件都先采用民事诉讼程序,而只有当民事诉讼程序的处理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时才适用刑法,这同样也不具有合理性。举例来说,就许多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案件而言,赔偿义务总是能够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法益保护,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赔偿义务并非总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法益保护。国家构架下的社会共同体要求维护它的基本价值和保障它的团体内部法制安定的利益,往往还只能是通过法律秩序对一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举止方式用刑法予以禁止的途径才能得到满足。那些因为自恃有经济上的能力而对什么都可以满不在乎,进而对赔偿义务不足够认真对待之人,至少是因慑于限制自由的威吓而不敢侵犯法律。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认为,只要司法办案人员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做出了合理的解释,那么对于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就应当以犯罪论处。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刑法谦抑性的边界,即便是在德国,主流观点也认为,实体刑法在过去几年时间的扩张不能因其具有“惩罚性”就武断地谴责其不合法。相反,当新型危害社会的行为对和平的共同生活构成威胁之时,存在许多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理由,最终的做法是在议会制民主的政体下通过民主制度制定有效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