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历史包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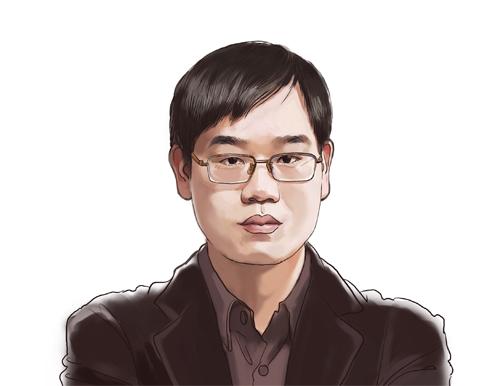
雷墨
特朗普入主白宮后,美国就有了“另类”的形象,即便是在西方国家眼中。所以我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这位特立独行的总统,是如何让美国如此“另类”的?
最近阅读了一些著作文献后,有了些许感想:一方面,如今的美国变得让人觉得陌生,有“特朗普因素”的作用,但实在也因美国的“历史包袱”使然。
把特朗普的执政与美国的乱象联系在一起并不难。但乱象在他入主白宫前就已出现,特朗普的角色只是催化剂,加速了这一进程。就像新冠危机加速了国际秩序变迁一样。设想一下,如果2016年赢得大选的是希拉里,美国的形象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扎眼。
美国建国者们的制度设计里的“约束总统权力”,与特朗普个人的权力欲,形成了完美对撞,结果就是美国频现宪政危机。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政府功能失调、治理失序,在新冠危机冲击下,甚至呈现无政府状态。对此,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就做了预言式的解释:“政治衰败在许多方面是政治发展的条件:破旧才能立新。但这种过渡可能是非常混乱和暴力的,不能保证政治制度会持续、和平且充分地适应新条件。”
福山做出这个分析时,不可能预言到特朗普当选,更不可能预言到新冠危机和种族骚乱。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因素,美国的“破旧立新”也会让人有如履薄冰之感。有了特朗普总统,如履薄冰似乎就没有必要了。
在当今主要世界大国中,美国算得上是非常年轻的国家,至今只有244年的历史。所以,很难把美国这个国家与历史包袱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建国之初的制度设计,有理念先进的一面(比如制度化约束最高权力,当时世界还停留在君权神授时代),也有思想复古的一面。这种复古,在一定的时间内与美国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能和谐共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设计复古的特点越来越成为制度革新、体制转型的掣肘。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说:“美国的政治现代化势头极弱又不彻底。在制度方面,美国整体上虽不是落后的,但也绝非彻底的现代化。”“在当今世界,美国的政治制度仅因其古老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十分独特了。”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建国之初的制度设计,带有明显的英国都铎王朝特性(1485年至1603年)。他是这么说的:“17世纪定居北美的英国人,带来都铎王朝时期或中世纪后期的政治实践。这些古老制度在美国本土盘踞下来,犹如冻结不变的古老社会的一部分,最终被写入美国宪法。”
都铎王朝特性指的是什么呢,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有个总结:“普通法作为权威来源;普通法高于行政部门;法院在治理中发挥相应的重大作用;地方自治的传统;主权由多个机构分享,并不集中于中央政府;政府权力分隔,而不是功能分隔。”
这些如何理解呢?以法院发挥行政功能为例,特朗普的“禁穆令”被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否决,后来又被最高法裁定合法。在其他西方民主制国家,尤其是议会制国家,禁止某个特定群体入境,完全是行政部门的事务。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因财政预算不通过而导致的联邦政府关门。我们只听说过某些欧洲国家组阁困难、政府难产,但从未听说过政府部门因预算问题而关门。因为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编制预算都是行政部门的权力。
美国的权力游戏与政治算计,南风窗新书《重新认识美国》中有详细的论述。美国建国者们的制度设计里的“约束总统权力”,与特朗普个人的权力欲,形成了完美对撞,结果就是美国频现宪政危机。特朗普执政的乱象,能不与美国的“历史包袱”有关?
——电影《郭福山》主题歌(男中音独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