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军中肉食供给初探
刘啸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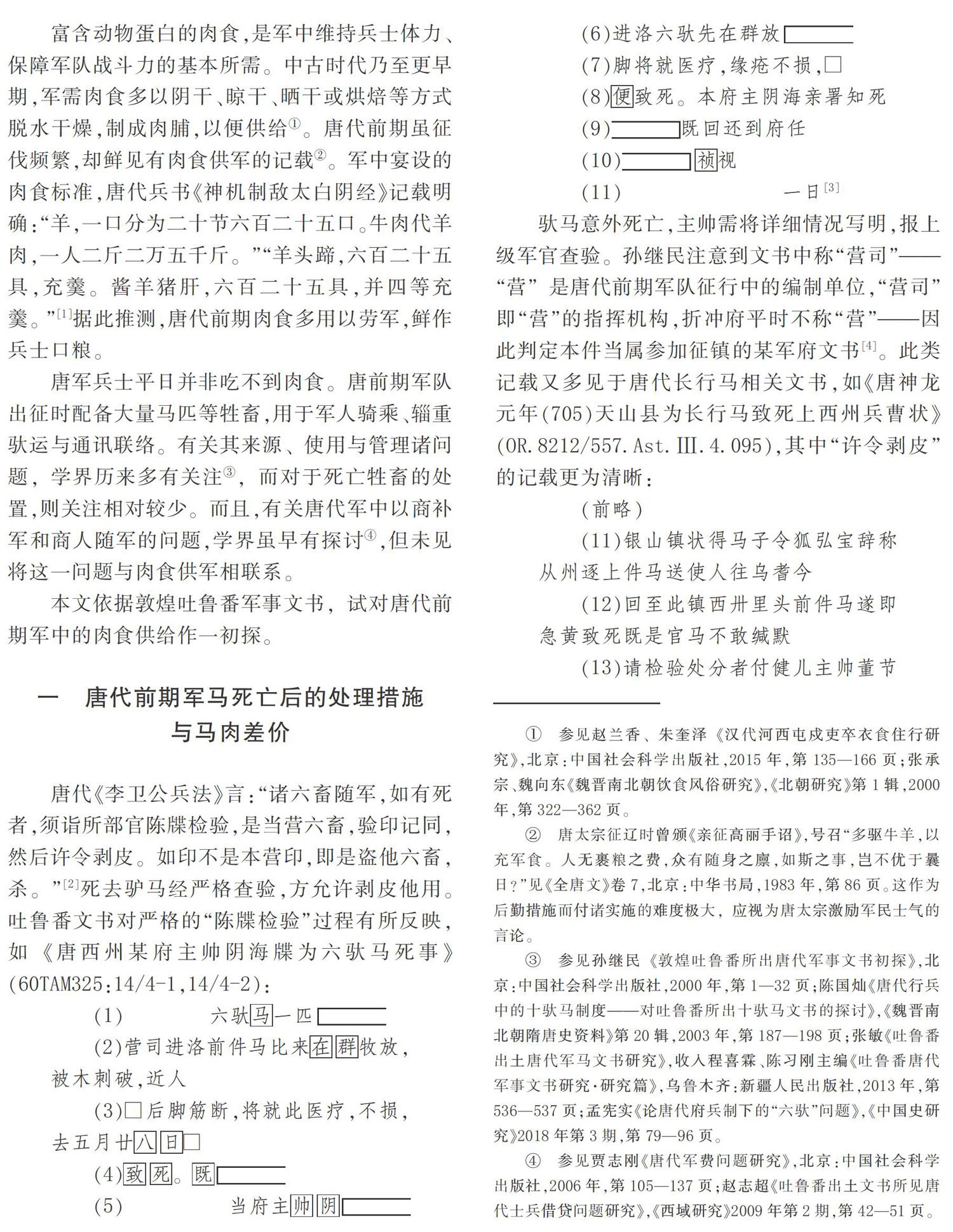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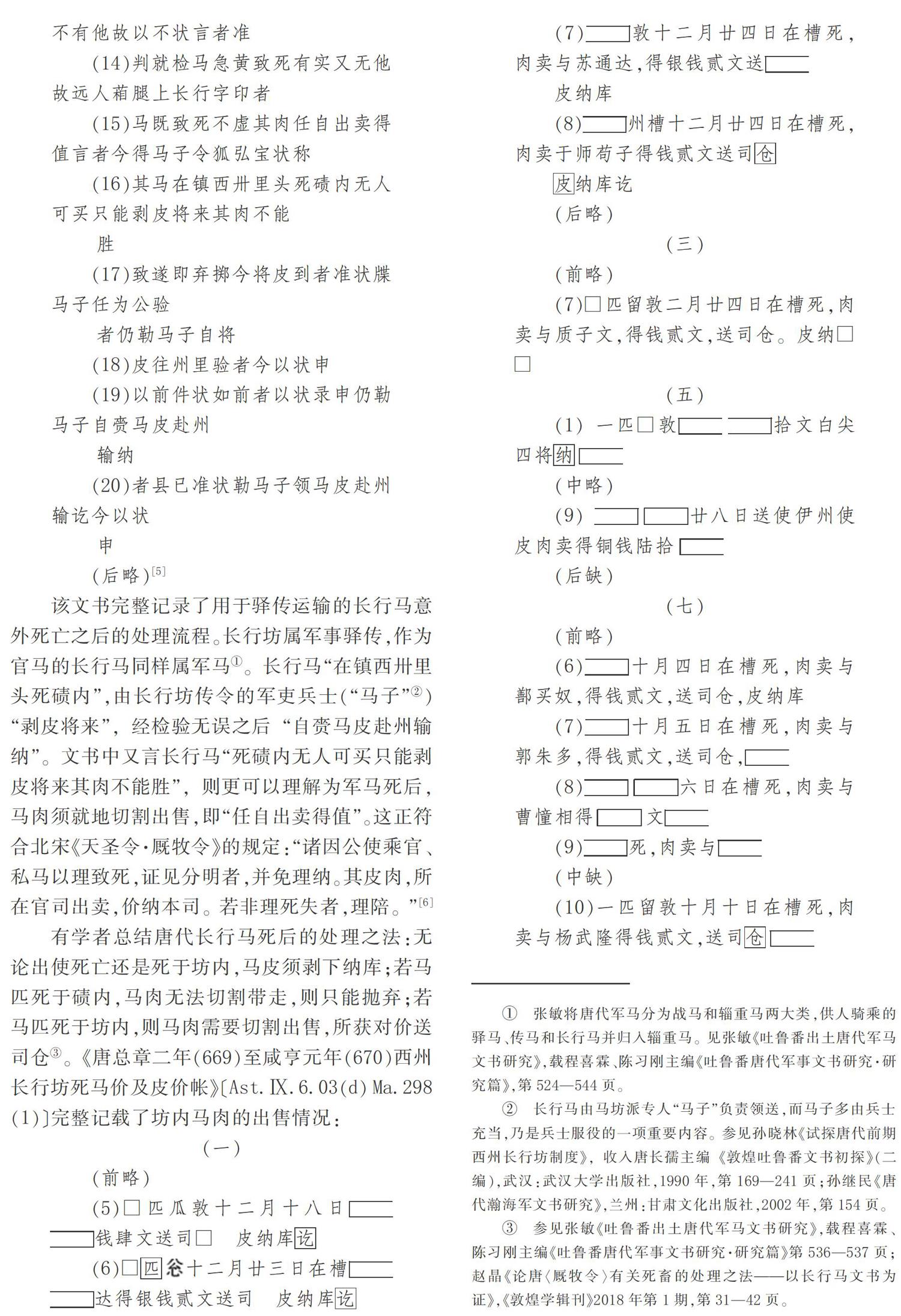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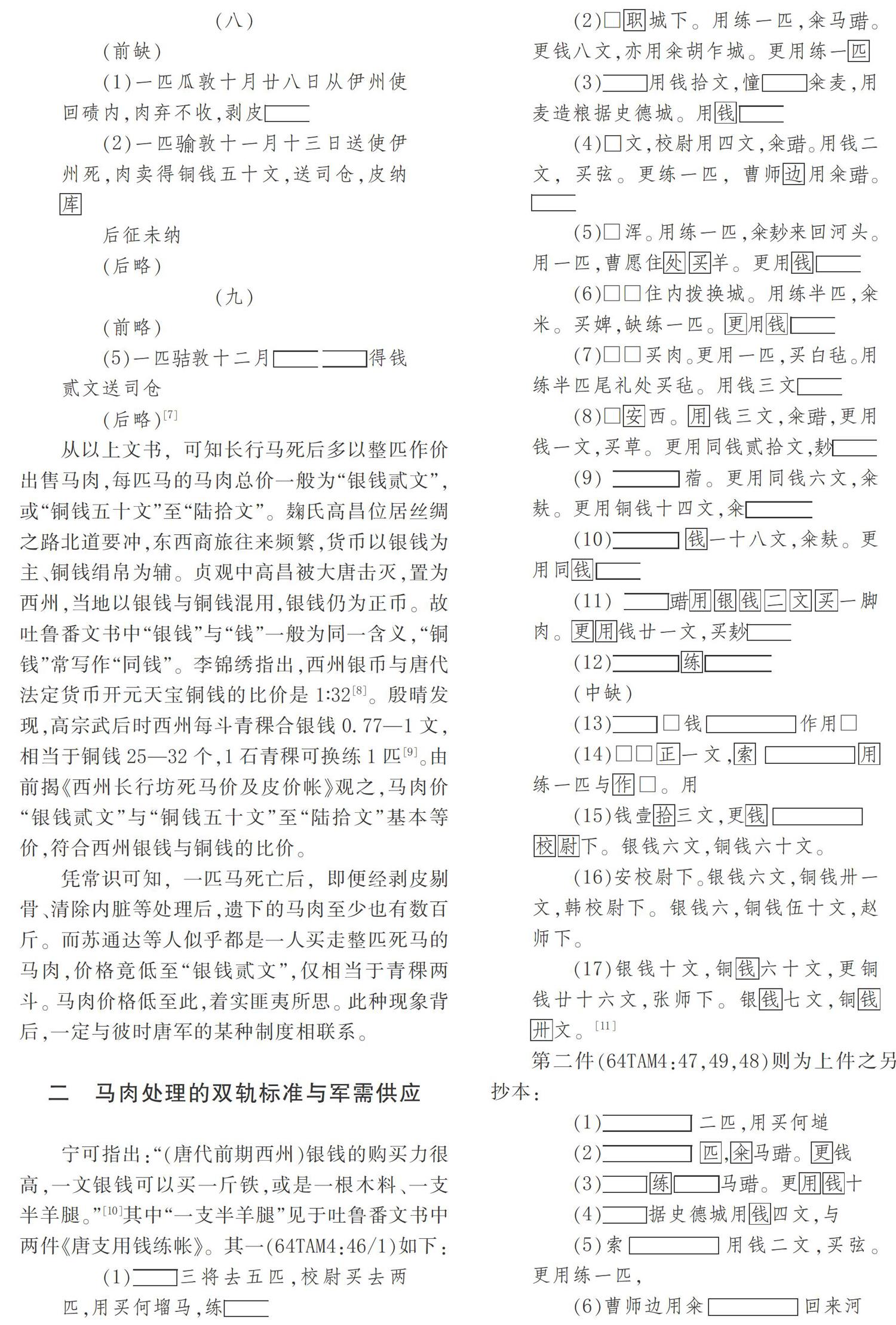
内容摘要:唐前期军中马匹等牲畜死亡后的处置,为剥皮纳库、畜肉出售。出售环节中,军人以象征性低价购买,军外平民则按市价交易。唐代行军中设置临时账房,统兵军官将兵士钱财集中存入,随时支取,向随军商人购买肉食等军需品,军中向士兵放贷的制度亦随之产生。这反映出彼时西州地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唐代;唐军;马肉;左憧憙;敦煌吐鲁番文书
中图分类号:K242;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3-0107-10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of Meat
in the Military Communitie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ocusing on Dunhuang and Turpan Military Documents
LIU Xiaohu
(Biquan Academy, College of Philosophy,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0)
Abstrac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dead animals and livestock used for consumption by the army would be skinned, following which the skins would be kept in a warehouse for further repurposing while the meat was sold at a market. Meat provided by the military supplier could be bought by soldiers at a discount, while civilians outside the army had to trade at market prices. Furthermore, temporary accounts were set up in the military communitie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order to procure supplies en masse for particular garrisons. Military commanders would collect the soldiersmoney together in a single account and draw from it at any time for the purchase of meat and other military supplies from merchants accompanying the army. This became a widespread system of finance and purchasing between soldiers and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study use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n military trading and finance to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al status of the commodity and currency economy of Xi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Tang dynasty; Tang army; horsemeat; Zuo Chongxi; Dunhuang and Turpan documents
富含動物蛋白的肉食,是军中维持兵士体力、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基本所需。中古时代乃至更早期,军需肉食多以阴干、晾干、晒干或烘焙等方式脱水干燥,制成肉脯,以便供给{1}。唐代前期虽征伐频繁,却鲜见有肉食供军的记载{2}。军中宴设的肉食标准,唐代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记载明确:“羊,一口分为二十节六百二十五口。牛肉代羊肉,一人二斤二万五千斤。”“羊头蹄,六百二十五具,充羹。酱羊猪肝,六百二十五具,并四等充羹。”[1]据此推测,唐代前期肉食多用以劳军,鲜作兵士口粮。
唐军兵士平日并非吃不到肉食。唐前期军队出征时配备大量马匹等牲畜,用于军人骑乘、辎重驮运与通讯联络。有关其来源、使用与管理诸问题,学界历来多有关注{3},而对于死亡牲畜的处置,则关注相对较少。而且,有关唐代军中以商补军和商人随军的问题,学界虽早有探讨{4},但未见将这一问题与肉食供军相联系。
本文依据敦煌吐鲁番军事文书,试对唐代前期军中的肉食供给作一初探。
一 唐代前期军马死亡后的处理措施
与马肉差价
唐代《李卫公兵法》言:“诸六畜随军,如有死者,须诣所部官陈牒检验,是当营六畜,验印记同,然后许令剥皮。如印不是本营印,即是盗他六畜,杀。”[2]死去驴马经严格查验,方允许剥皮他用。吐鲁番文书对严格的“陈牒检验”过程有所反映,如《唐西州某府主帅阴海牒为六驮马死事》(60TAM325:14/4-1,14/4-2):
驮马意外死亡,主帅需将详细情况写明,报上级军官查验。孙继民注意到文书中称“营司”——“营”是唐代前期军队征行中的编制单位,“营司”即“营”的指挥机构,折冲府平时不称“营”——因此判定本件当属参加征镇的某军府文书[4]。此类记载又多见于唐代长行马相关文书,如《唐神龙元年(705)天山县为长行马致死上西州兵曹状》(OR.8212/557.Ast.Ⅲ.4.095),其中“许令剥皮”的记载更为清晰:
(前略)
(11)银山镇状得马子令狐弘宝辞称从州逐上件马送使人往乌耆今
(12)回至此镇西卅里头前件马遂即急黄致死既是官马不敢缄默
(13)请检验处分者付健儿主帅董节不有他故以不状言者准
(14)判就检马急黄致死有实又无他故远人葙腿上长行字印者
(15)马既致死不虚其肉任自出卖得值言者今得马子令狐弘宝状称
(16)其马在镇西卅里头死碛内无人可买只能剥皮将来其肉不能
胜
(17)致遂即弃掷今将皮到者准状牒马子任为公验
者仍勒马子自将
(18)皮往州里验者今以状申
(19)以前件状如前者以状录申仍勒马子自赍马皮赴州
输纳
(20)者县已准状勒马子领马皮赴州输讫今以状
申
(后略)[5]
该文书完整记录了用于驿传运输的长行马意外死亡之后的处理流程。长行坊属军事驿传,作为官马的长行马同样属军马{1}。长行马“在镇西卅里头死碛内”,由长行坊传令的军吏兵士(“马子”{2})“剥皮将来”,经检验无误之后“自赍马皮赴州输纳”。文书中又言长行马“死碛内无人可买只能剥皮将来其肉不能胜”,则更可以理解为军马死后,马肉须就地切割出售,即“任自出卖得值”。这正符合北宋《天圣令·厩牧令》的规定:“诸因公使乘官、私马以理致死,证见分明者,并免理纳。其皮肉,所在官司出卖,价纳本司。若非理死失者,理陪。”[6]
有学者总结唐代长行马死后的处理之法:无论出使死亡还是死于坊内,马皮须剥下纳库;若马匹死于碛内,马肉无法切割带走,则只能抛弃;若马匹死于坊内,则马肉需要切割出售,所获对价送司仓{3}。《唐总章二年(669)至咸亨元年(670)西州长行坊死马价及皮价帐》〔Ast.Ⅸ.6.03(d) Ma.298
(1)〕完整记载了坊内马肉的出售情况:
(一)
(前略)
(后略)[7]
从以上文书,可知长行马死后多以整匹作价出售马肉,每匹马的马肉总价一般为“银钱贰文”,或“铜钱五十文”至“陆拾文”。麹氏高昌位居丝绸之路北道要冲,东西商旅往来频繁,货币以银钱为主、铜钱绢帛为辅。贞观中高昌被大唐击灭,置为西州,当地以银钱与铜钱混用,银钱仍为正币。故吐鲁番文书中“银钱”与“钱”一般为同一含义,“铜钱”常写作“同钱”。李锦绣指出,西州银币与唐代法定货币开元天宝铜钱的比价是1∶32[8]。殷晴发现,高宗武后时西州每斗青稞合银钱0.77—1文,相当于铜钱25—32个,1石青稞可换练1匹[9]。由前揭《西州长行坊死马价及皮价帐》观之,马肉价“银钱贰文”与“铜钱五十文”至“陆拾文”基本等价,符合西州银钱与铜钱的比价。
凭常识可知,一匹马死亡后,即便经剥皮剔骨、清除内脏等处理后,遗下的马肉至少也有数百斤。而苏通达等人似乎都是一人买走整匹死马的马肉,价格竟低至“银钱贰文”,仅相当于青稞两斗。马肉价格低至此,着实匪夷所思。此种现象背后,一定与彼时唐军的某种制度相联系。
二 马肉处理的双轨标准与军需供应
宁可指出:“(唐代前期西州)银钱的购买力很高,一文银钱可以买一斤铁,或是一根木料、一支半羊腿。”[10]其中“一支半羊腿”见于吐鲁番文书中两件《唐支用钱练帐》。其一(64TAM4:46/1)如下:
两件对读,可知全貌。文书中频见“买肉”“买一脚肉”,又有“曹愿住处买羊”和“愿住处买肉”。汉代许慎《说文》曰:“脚,胫也。”又曰:“胫,胻也。膝下踝上。”[12]所谓“脚”即小腿,在吐鲁番文书中属名词转量词,“一脚肉”可理解为“一条腿的羊肉”[13]。其价格,乃“银钱二文”。
据荣新江、陈国灿考证,这两件文书写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西域道行军解于阗之围得胜后的班師途中[14,15]。麟德二年,与总章二年(669)至咸亨元年(670)几无相隔。彼时西州地区一条重量至多不过几十斤的羊腿,与一整匹长行马的数百斤马肉,价钱居然同为“银钱二文”。
若说肉价贵贱悬殊是因羊马有别,又可参见《唐典高信贞申报供使人食料帐历牒》(73TAM208:26.31/1)。文书记年已缺,同墓中另有《唐永徽四年(653)张元峻墓志》,该牒是自墓主尸身纸鞋上拆出的。这说明该该牒写于永徽四年之前不久。唐长孺认为,这应是彼时某馆的供食帐历。其中有载:“驴脚一节,用钱叁文伍分。”[11]186
吐鲁番文书中,“节”作为量词,是用来表示肉块的单位。“驴脚”即驴腿肉[13]85。“驴脚一节”的具体重量虽不得而知,但显然是驴腿肉的一部分,可与“一脚羊肉”相比较。前揭1斗青稞银钱1文,1石青稞价值1匹练,即1匹练相当于银钱10文。《唐支用钱练帐》中有“用练一匹,曹愿住处买羊”。以此观之,“一脚羊肉”值“银钱二文”,“驴脚一节”值“(银)钱叁文伍分”,1只羊价值银钱10文,这应为肉类的正常价格。而数百斤马肉竟仅值“银钱二文”,该如何理解?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应与唐代前期军中的肉食供给相联系。以“银钱贰文”之低价买走整匹死马肉的苏通达等人是何身份,不得而知。但如长行坊这类具有重要军事性质的官方交通通讯机构,是否允许平民百姓前来购买马肉,尚存疑。再与前揭“牒为六驮马死事”相联系,笔者试作如下猜测:死去的长行马为军马,马肉实际是由军队内部处理,出售给征镇西州的军人。苏通达等人是服役地点在长行坊附近、代表整队兵士前来购买马肉的军吏。其运回整匹死马的肉,供同袍分食。马肉仅值“银钱贰文”,则是对军人的一种福利。毕竟,死马的真正价值在于纳库之皮,而非容易腐烂、无法储存的马肉。这种福利同样是唐代前期军中的一种补充肉食供给措施{1}。
出征作战时随军马匹意外死亡,经过上级军官查验,“许令剥皮”,然后马肉同样是在军中内部处理的。各队各火士兵以象征性低价购得马肉,改善生活。就目前所见史料,这自当是唐代兵士在军中获取新鲜肉食、补充动物蛋白的又一途径{2}。
唐代军队对于军马死亡后马肉的出卖,实际执行的是一种双轨标准:对军内的军吏兵士,允许以“贰文”低价买走整匹死马肉;对于军外的平民,则按照市价,在市场上将马肉分割出售。可见《唐军府文书为卖死马得价直事》(72TAM209:72—76):
(前缺)
(后缺)[16] 62-63
两件文书出自同一墓,记年已缺。该墓出有《唐显庆三年(658)张善和墓志》,自墓主男尸身上发现的文书年代多为武周时期。这两件文书都是从男尸纸鞋中拆出的[16]34。因此,其年代当在显庆三年前不久。唐长孺又按,两件文书内容相关,笔迹墨色相同,很可能属同一案卷。军中出卖马肉,军府文书特意写明是“出卖市司”“付市相监”,即拿到市场上向军队外的平民百姓公开出售。由“当马主帅相监卖”“勘尾还付主帅”便知,某位军官麾下的军马死亡后,经行文报备,由其亲自负责在市场上将马肉分割出售,所得肉钱上交州曹。类似情况又见《死马(官马)处置文书》(大谷一〇一六号):
(1)□□称上件马死请裁者
(2)□□团出卖仍限今月廿
(3)□日替状上十一月十四日史张
(4)□ 帖
(5) 司马纪衣
(后缺)[17]
市场上对外售卖的是“瘦马肉两腔”,并特意写明“瘦弱”,符合军马病死的情况{1}。这两腔马肉显然不是以“银钱贰文”的低价整腔出卖,而是切割称重分块出售,每块分别卖得“银钱陆文”“银钱肆文”和“银钱壹拾文”等,即是“随贵贱卖”。若非向军内外出售马肉存在巨大价格差别,很难对此做出合理解释。
又见《唐贞观廿三年(649)赵延济送死官马皮肉价练抄》(59TAM302:35/2):
(1)廿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赵延济送死官马皮
(2)肉价练叁匹典张德颍领[18]
太宗贞观后期一匹死马“肉价练叁匹”,以高宗武后时比价合银钱30文。笔者认为,此为彼时一腔马肉的正常市场价格。
另外,唐代军队出征时以“诸六畜随军”,如死驴的处理方法即与死马一样,吐鲁番文书中有《唐开元十年(722)三月牒西州长行坊为西州驴死事》(有邻22号)[19]。所以,有观点认为唐代兵士唯有在出师劳军、班师庆功或粮食紧张时作为紧急替代等特殊情况下才能吃到牛肉等肉食[20],此论当不确。军中凡有马、驴、牛等“六畜”死亡,军吏兵士即有机会食肉。
三 随军商人的羊肉供应
与左憧憙的计会司帐
唐代军中的肉食供给,并不仅限于死畜肉。前揭两件支用帐中出现的“羊肉”,同属供军范畴。两件文书出自同一墓,该墓共出土社会经济文书23件,并《唐咸亨四年左憧憙墓志》一方,均与墓主左憧憙有关。学界对此已有充分研究:左憧憙生于隋炀帝大業十三年(617),死于唐高宗咸亨四年(673),西州高昌县祟化乡人,身份是前庭府卫士、地主兼高利贷者,一生于西州各地放贷敛财,并多次参加征行,还在军中从事放贷{1}。
钱伯泉认为,凡吐鲁番出土的公文书皆钤有印信,而这两份支用帐未钤任何印信,故应为左憧憙本人的个人收支流水账[21]。如此,“一脚肉”是左憧憙本人购买,属于个人消费。卢向前也认为左憧憙购买“一脚肉”的目的是“改善生活”,但同时提醒,左憧憙恐兼有军人和随军商人的双重身份[22]。赵志超赞同左憧憙既是士兵又是商人,并指出据文中所见其买卖的物品,有丝织品、粮食、弓弦、毡、草等,可说除武器以外士兵的一切军需用品都在这清单之内,因此左憧憙个人的商业行为乃是未来军市的雏形,其商业行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唐代军需供应中的矛盾,是唐代军事后勤体系的有益补充[23]。换言之,“一脚肉”是左憧憙在军中买卖的商品。陈国灿则坚持,文书中所称“曹师”“赵师”“张师”,是“曹帅”“赵帅”“张帅”之讹写,应均为旅帅;如此多的军官支用银、铜钱,说明该文书应是军府支用帐{2}。所以,左憧憙支钱购买羊肉,是给部队采办军需,羊肉归军中食用。
首先需要明确左憧憙本人的身份。唐长孺曾研究左憧憙在西州高昌县祟化乡兼并土地的行为,认为左憧憙乃无官爵的富裕之家,身份不过是一个“普通卫士”[24]。赵志超亦言,左憧憙是以“出征士兵”身份进行商业交易活动。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军中经营放贷,还是在军中记录内容如此丰富、收支额度巨大的账目,都非一个普通的“出征士兵”所能做到的。高宗麟德二年时,左憧憙已49岁。陈国灿指出,左憧憙属年长者,有一定社会阅历,能文又善理财,所以很可能会在军中临时担任职务。他推测,左憧憙在此次征行中担任西州前庭府的计会司帐人员[15]。钱伯泉认为,左憧憙是高昌县的豪富,参军后不会是普通士兵,一定是担任了统率同府卫士的中下级军官,所以才能借机向士兵放贷;而文书中的三名“校尉”因此才将钱财存入他的帐房,左憧憙如同在军中开设了自己的钱庄[21]。按照上述理解,左憧憙其实是行军中临时被委任的一名专职军吏,而其职责是计会司帐还是统兵带兵,决定着这两件支用帐的性质。
笔者更倾向于陈国灿的观点。钱伯泉承认,从两份帐目来看左憧憙的开支很大[21]。正因为开支太大,购买商品的数量显然超出了左憧憙本人所能消费的能力。屡屡“买肉”乃至“买弦”,本身即不像是个人消费。最不合理处,是一次“用练一匹”购买马料。彼时西州一匹练可购得一石青稞,能购得多少“马?”可想而知。吐鲁番文书中的《唐天宝十三——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交卷》{3},详细记录了交河郡长行坊及所属诸馆向来往人员提供马匹、消耗马料的情况,其中《唐天宝十三载(754)礌石馆具七至闰十一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73TAM506:4/32-3)多有记载,如“同日郡坊帖马十六匹,从银山送刘大夫到,内六匹全料,共食麦一石一斗”“同日郡坊帖马十四匹送赵都护家口,从银山到,便腾向天山。食麦一石四斗”“同日马都督乘郡坊帖马十匹便腾过,食麦一石”[25]。十几匹长行马消耗的马料不过一石有余,“用练一匹”购买的马料恐非左憧憙一人所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详细规定了唐代前期行军状态下军马每天的马料消耗配额:
一马日支粟一斗,一月三石,六个月一十八石。计一军马一日支粟一千二百五十石,一月三万七千五百石,六个月二十二万五千石。
马盐,一马日支盐三合,一月九升,六个月五斗四升。一军马支盐三十七石五斗,一月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个月六千七百五十石。
茭草,一马一日支茭草二围,一月六十围,六个月三百六十围。计一军马六个月九十围。[1]101
每匹军马每日消耗粟1斗、盐3合及茭草2围,与十几匹长行马总共消耗马料一石多基本符合。李锦绣又指出,驮马冬春季节每日食料消耗为粟3升、草1围{1}。卢向前更将两件支用帐与《唐总章元年(668)左憧憙买草契》(64TAM4:32) [11] 424-425中左憧憙“用银钱肆拾”购得“草玖拾围”的交易相联系,猜测左憧憙可能拥有一支商队,承包了此次行军的一些军队给养和经济事务。
然而,如果左憧憙真是随军商人,为何两份账目所记全是支出钱练、购买商品,却没有收入钱练、销售商品?“三将去五匹,校尉买去两匹,用买何塯马”,同样不像商品销售,更像是钱练兑换。笔者认为,“校尉”拿银钱跟担任军中计会司帐人员的左憧憙兑换绢帛匹练,“用买何塯马”。唐代前期西州军人用绢帛匹练买马的交易常见,吐鲁番文书中有《唐贞观二十三年(649)西州高昌县范欢进买马契》(60TAM337:11/8,11/5)[18]105-106、《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73TAM509:8/10)[18]48-49,所用皆为“练”。
“校尉”向谁“买何塯马”?卖马之人身份不明,但卖羊之人有确切姓名:曹愿住。如前所述,彼时军队由西向东经拨换城、安西等地一路行军。左憧憙一路支钱买肉,曹愿住则一路相随提供肉食。据钱伯泉考释,第一份支用帐中中的“住内拨换城”录文有误,“住内”为“买肉”的误释,后一句应为“拨换城用练半匹,籴米”,前一句为“用一匹,曹愿住处买羊。更用钱……买肉”[21]。此句在“河头”之后,说明左憧憙之军于河头向曹愿住买羊买肉。行军至拨换城之后,依然是到“愿住处买肉”。曹愿住应是驱赶活羊从河头随唐军来到拨换城,继续向军队提供肉食。笔者猜测,曹愿住很可能是一位随军的粟特商人。唐军又向安西开拔,曹愿住有无继续驱羊随军,在安西将“一脚肉”卖与唐军之人是不是曹愿住,无法证实。不过,有两点应该可以明确:
其一,唐代前期军中的确存在随军商人,如曹愿住随军卖羊卖肉这样的商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需供应中的矛盾,是唐代军事后勤体系的有益补充(校尉买马应同属此类)。
其二,唐代前期军中供给的肉食,一定程度上确实需要向随军商人或民间采买,而且是以“银钱二文买一脚肉”“一匹练买一只羊”的市场价格支给。
笔者认为,左憧憙并非随军商人,而是在本次行军中临时任职的计会司帐人员。左憧憙支钱购买羊肉,乃是军官从随军商人处购得羊肉给麾下兵士们改善生活,如此也符合一次“一只羊”或“一脚肉”的购买量。从随军商人手中购买,则正是唐代军队获取肉食的又一种方式{2}。
笔者推测,第一份支用帐所附的“安校尉”“韩校尉”“赵师”“张师”等人铜、银钱帐,实际是一份支出结余账目,显示的是本次行军结束后西州前庭府诸校尉、旅帅军官名下所余款项。这些款项很可能并非军官们的钱财,而是他们将麾下兵士的钱财集中存入行军临时账房,由左憧憙负责管理支给,随时用于向随军商人购买军需物资。
这即是说,支用帐中列出军官的姓名,其实代表这些军官麾下兵士们的集体账户。一如李泌作《议复府兵》言:“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于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26]这种“利其死而没入其财”的情况自非常态,但将兵士们的随身财物集中起来“寄于府库”确是一种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旧唐书·鲁炅传》载:“裨将岭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军,多怀金银为资粮。”[27]士兵的钱财统一上交给统兵军官,由军官存入行军账房。行军账房为临时设立,其支用帐属非正式文书,所以不像正式公文书一样钤有印信。而且这两件支用帐应是行军结束后左憧憙对支出状况的核算统计,确有私人文书性质,故更不可能钤印。
同时,笔者另有推测:正因为一切都是在“临时”和“非正式”的状态之下,所以左憧憙很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将行军账房中士兵们的集体钱财作为资本,反过来向士兵放贷。此方符合钱伯泉有关左憧憙在军中“开设钱庄”的推论。而且,左憧憙用公款“开设钱庄”的行为,或在军中得到默许乃至鼓励。因为从放贷文书中可见,左憧憙向士兵放贷并不收取利息。这种借行军临时账房向士兵放贷的行为,甚至有可能正是唐代军中一种财务互助制度。从这一角度来看,咸亨四年左憧憙过世后,墓志中言其“鸿源发于戎卫,令誉显于鲁朝”[28]{1},或非谀之辞。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唐代前期的军队中,军马(包括驴、牛等牲畜)死亡后的处理措施是剥皮纳库、马肉出售,并实际执行一种双轨标准,即对军内的军吏兵士,允许以象征性低价买走整匹死马的马肉;对军外的平民,則按照市价,在市场上将马肉分割出售。军人以象征性低价购得马肉,以肉食改善生活,这既是一种军内福利,又是军需供应的补充。
另一方面,唐代确有商人随军从事商业活动。行军中各军府临时委任计会司帐人员,掌管行军临时账房。统兵军官将麾下兵士的钱财集中存入,随时支取,用来向随军商人购买肉类等军需品。可以说,商人随军是唐代军需供应的有益补充。这种行军临时账房的设置,很可能又在唐代前期军中形成了一种向士兵放贷的财务互助制度。
对于唐代前期的军队后勤体系,《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制度卷》评价为:“卓有成效,堪称楷模……为其军事上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提供了充分而可靠的后勤保障。”[29]在宏观的研究和评价之外,也应看到其间仍有许多问题待厘清。如军队内部处理马肉、向随军商人购买肉食等日常举措,或许并不见于传世典章,却切实对军需供应的补充和军人战斗力的维系产生了作用。
我们更应该看到,唐代前期西州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货币与商品,在从征兵士、行军账房和随军商人三者之间实现了顺畅的流通。这种流通不仅打破了军队内外的藩篱,甚至通过向军人出售马肉和放贷,在军队内部形成了一种自我运转的循环。有关这一问题,更值得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4-126.
[2]李靖.卫公兵法辑本[M].汪宗沂,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3.
[3]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04.
[4]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
[5]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16.
[6]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293.
[7]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368,371-372,374-377.
[8]李锦绣.唐与波斯:以西安出土波斯胡伊娑郝银铤为中心[C]//苏智良.程应镠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511-512.
[9]殷晴.唐代西州的市场交易与管理法规[M]//探索与求真:西域史地理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225-226.
[10]宁可.唐及五代的货币结构[M]//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333.
[11]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434-435.
[12]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70.
[13]廖名春.吐鲁番出土文书新兴量词考[J].敦煌研究,1990(2):82-95.
[14]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G]//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45-351.
[15]陈国灿.唐麟德二年西域道行军的救于阗之役: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四号墓文书的研究[G]//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2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27-36.
[16]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60-61.
[17]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第1卷[M].京都:法藏馆,1984:3-4.
[18]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33.
[19]陈国灿,刘安志.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598.
[20]李谋娜.唐代士兵生活相关问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22.
[21]钱伯泉.从《唐支用钱练帐》考察唐初西域的政治经济状况[J].新疆社会科学,2005(5):99-106.
[22]卢向前.金钥匙漂流记:古代中西交通猜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3-124.
[23]赵志超.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士兵借贷问题研究[J].西域研究,2009(2):42-51.
[2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會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264.
[25]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93-94.
[26]李泌.议复府兵[G]//全唐文:卷378.北京:中华书局,1983:3839.
[27]刘昫,等.旧唐书:卷114 [M].北京:中华书局,1975:3362.
[28]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71.
[29]童超.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制度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