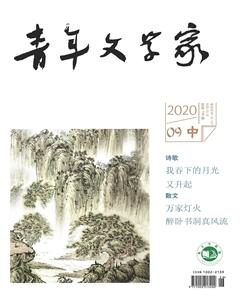以《情人》谈杜拉斯的文化跨越
摘 要:20世纪90年代,杜拉斯这个独特的女性写作者开始进入中国女性作家们的视野。东西方文化混合交错的成长背景,使得杜拉斯的创作中总是带有一种激烈的在东、西方文化上的内在冲突。她的书写既体现着西方文化中对肉欲的欢娱、“随意的性”的追求,又有着对东、西文化交错的身份焦虑。
关键词:杜拉斯;欲望书写;流散;文化混合
作者简介:陈琢,女,汉族,湖北黄石人,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學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2
自传体小说《情人》这部作品的发表,使玛格丽特·杜拉斯荣获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为一个被遗弃在印度支那殖民地这片土地上的法兰西后裔,作家身份上的矛盾、家庭的重重变故激发着她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和想要向既定命运抗争的强大欲望,也展现出跨越文化的生命力。
一、被肯定的欲望:追求肉体的欢娱
(一)“随意的性”
在现代社会文明中,关于性爱的话语主要两类:浪漫性话语、随意性话语。浪漫性话语:爱是婚姻的实质,也是性爱活动唯一合法的理由。这一类浪漫性话语,在性文化更佳保守、压抑和严肃的东方文化中体现更甚。另一种性爱话语是:随意的性。“随意的性”是指把性和性爱的欢娱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更具动物天性地将性视为个人化的行为,而不看中世俗首肯的伴侣关系。随意的性话语,一方面与二十世纪西方一系列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变有关,另一方面,与杜拉斯在矛盾交杂的东、西方文化中生长起来的叛逆天性有关:以打破贞操的方式打破命运的束缚。《情人》中十五岁的少女“我”,在欲念的牵引下一次次随着那个中国情人去到人声鼎沸的中国人生活区,进到那个充满暧昧情调的、拉着纯洁百叶窗的房间。在每一段性爱描写中,少女“我”从来不是被动的,而是和“他”一样“处在肉欲的狂热”中,她被自然的野性指引,自愿而主动地奉献自己的身体。显然,“我”已将性爱比做一门技艺。性爱话语的严肃性、封闭性和私密性因此而被消解。当“贞操”不再是传统东方文化中女性命运转折的致命关键点,女性的幸福归属也从“是否处女”中被解救了出来。
(二)“无爱的性”
《情人》对性的“浪漫话语”的消解使我们发现,在西方文化中(以法国女性属性为代表),性的意义是多元的。当性不再是“爱情”必然的结局时,性的意义便可以是“无爱的”。杜拉斯肯定了无爱的性,亦是为女性自身赋权。在《情人》中,我与中国情人之间的性不是买卖的要求,也不是爱情华丽的副歌。这里的性只是性:没有是非,只是纯粹的快乐。和而不同的是,西方女性的生理成熟往往比东方女性早8-10年。东方女性对自身生理欲望的自觉意识多在二十五岁以后(多数在成婚以后),而西方女性往往在十三、四岁便会呈现出生理上的成熟与完备:生理欲望也更早地自然萌动。作为流淌着法兰西血液的西方后裔,即使在保守、传统和性意识封闭的东方土地上,杜拉斯自身的生理成熟期显然比东方女性更早。作家也因此在《情人》中将少女“我”对性爱的渴望描写成为一种不容蔑视的、理直气壮的美丽和纯洁的力量。除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爱,杜拉斯诸多作品中都涉及到了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之间的精神之爱。如《情人》、《乌发碧眼》、《恒河女子》。“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决定了他的社会特征和异性恋的欲望”观点已经被很多后现代性学理论家认为是一种在性别认可上的文化霸权。《情人》中的“我”,就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酷儿”。正如波伏娃所言:“女人之间的爱是沉思的,抚摸的目的不在于占有对方,而是通过她逐渐再创造自我”。
二、东、西方的成长经历:混合的身份
(一)童年经验理论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曾指出:人的童年经历或者说是早期经验会对他的一生构成影响深刻的潜意识。而杜拉斯在印度支那生活的童年经历也成为她的作品中深刻的文化潜意识。无论是文字排版中对法语规范语法的刻意背弃,还是其作品语音语调中绵长无尽地带着伤感音调的韵律,都使得杜拉斯文学作品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绝望的欲望硝烟的味道。在1987年创作的《物质生活》中,杜拉斯就曾经提到她的故乡是水乡、是湖和湍流、是平原上充满了泥土的味道的故乡。童年在印度生长的杜拉斯,虽然具有法兰西民族的肤色和血统,但是她心灵上真正的归属是东方文明中的印度,是一块被热带季风常光顾的热土。
(二)印度生活的凸透镜
虽然杜拉斯的生命旅程经历了东、西文化的混合,但是在她文学创作中起到最决定性作用的,是在法属印度生活的那一段童年时光。杜拉斯毕竟是一个具有合法法国国籍、纯正法国血统的西方人,无论在印度生活时她的家庭有多么贫穷和艰难,她和自己的家人也一直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作为殖民地国家公民的优越感。在《情人》的开篇中作者写到,即使在搭乘公交车时,司机也会把所有前排座椅空出来给具有殖民者身份的“我”们去坐。印度支那联盟包括老挝、柬埔寨、东京、安南、交趾支那五个地区,其中东京、交趾支那、安南三个地区成为了法属印度支那。杜拉斯的童年便是在西贡、河内、金边这些地区度过。《情人》中不断被强化的“我”哥哥的粗暴、“我”母亲的疯狂混乱、“我”的无病呻吟都反映了印度支那地区法国白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杜拉斯的作品像是一副凸透镜,以真实贴近的角度描绘了一个充满着黑暗与贫困、满目疮痍的支那土地上的法国白人生长图。印度支那地区的自然风景:《情人》中一次次被提到的湄公河、塞纳河、印度恒河,以及热带地区特有的阳光与季风,都被作家一一汲取进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三)流散身份中的边缘文化
“流散”这一词,在阿什克洛夫特的《后殖民关键词研究》中被定义为“人们从他们的家乡自愿地或被迫地迁移——是殖民过程中的一个中心历史事实”。二战后,大量要求重返宗主国的原被殖民者和由经济、文化等带来的殖民主义之外的原因,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些多元文化中的“流散者”在东方、及交杂的文化环境中反而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因为对世界文化的改造与传承产生了更大的主动性。杜拉斯与印度支那地区不是神交,她和家人一起“像越南人一样讲越南语、和越南孩子一起玩游戏”。在《杜拉斯的领地》中,杜拉斯甚至强调自己是越南人。这样一来,文化层面上的杜拉斯就处于一种“无家”的流散状态,她的心灵就会充满焦虑与矛盾。事实上,当今世界人口正是经历着越界大流动:移民、难民、流散社群、留学者,这些人处于不同文化之间感受到文化边界的不稳定状态。一方面,杜拉斯在《情人》中想要创造一个“欲望正义”的白人情人形象;而另一方面,她的越南性又使她作品中不断表露着东方文化的真实。
三、“征服那个中国情人”——身份焦虑的投射
(一)中国情人性格上的“软弱无力”
《情人》中,那个中国男人本是帅气的巨商之子,但是在“我”的面前却是这样羸弱、被动。十五岁的、貧穷的“我”被杜拉斯塑造成了一个勇敢的、强悍的“男权”形象。在“我”对那个中国情人的情欲征服背后,其实也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欲望征服。尽管那个中国情人已经在法国留学过,并且风流倜傥、家财万贯。但是在贫穷的白人女学生面前,他依然有一种令人震动的“自卑”:第一次搭讪少女时,他由于胆怯整个人的声音和手指都在颤抖着。此时的中国情人,虽然是生理上的男人,但是在文化特征上显然已经被塑造成了具有东方文明色彩的“女人”。少女“我”更像一个刚毅勇敢的“男人”。那个中国男情人的身体那样单薄,他的性格像殖民地的本地女人一样娇柔,他在“我”的面前不止一次地哭。中国情人像一个羸弱的怨女,在“我”面前哭诉:从文化层面上看,东方文明此时是被弱化、丑化的。如果说,杜拉斯在《情人》中为少女“我”所赋予的这份自信是代表了一种西方文化的自信与强势的话,那个脆弱的中国情人形象无疑被当成了“低劣的、奴性的”东方文明的代表。男女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性爱关系,在创作者的潜意识里,特别是像杜拉斯这样的作家,她们是在复杂的东西文化杂糅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男女关系体现出东、西方之间经济地位和种族身份之间的较量。而中国情人软弱无力的形象则无疑透露了作家在殖民时期的文化态度:西方文明正在强暴东方文明。
(二)中国情人的形象与法国社会的集体想象
殖民时期欧洲人对东方人的想象是否真的符合现实呢?“他们酷爱抽大烟和一夫多妻”是当时欧洲人对东方人极具代表性的集体想象。在《情人》中,少女总是很清楚自己与中国情人这份爱情最终的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对“我”表露出无限深情的那个中国情人,却没有违抗父亲的命令:他害怕失去父亲财富的继承权。于是作品中她的中国情人总是哭。在人物形象上,少女的情人也没有男性符号的胡须、肌肉,而总是被描绘为瘦弱的、“经不起使人受苦的力量”、只有生殖器是旺盛的。对于当时的世界局势,处于殖民者的西方国家一种集体自信的心理状态,也在杜拉斯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结语:
总之,“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之中”,而作家生命经历中的文化交融会更加深刻地体现在文学创作的深处,成为其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众多作品,无疑都是20世纪里东西文明交融的代表产物。在那段世界局势风云诡谲的时空里,杜拉斯以其独特的文学语言发声,将交融的生命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1]瓦里尔. 这就是杜拉斯 卢思社译. 作家出版社,2010.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玛格丽特·杜拉斯. 情人王道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弗洛伊德著. 梦的解析 赖其万译. 九州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