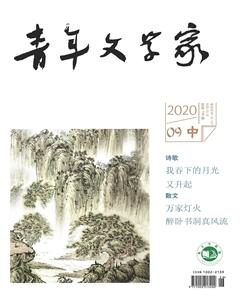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蕴
摘 要:本文着眼于萧红的几部小说,对其作品中的悲剧意蕴进行探究。笔者分别以萧红小说的悲剧意味源于何处,它是如何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又是涵括了怎样的审美意蕴为核心来书写的。
关键词:萧红;悲剧意蕴;审美意义
作者简介:杨紫薇(1996-),女,辽宁辽阳人,硕士,研究方向: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2
引言:
萧红小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那悲凉的意蕴。这一抹灰色基调,体现在她的笔下便是“人生何如,为什么如此悲凉?”萧红小说中这种悲凉感是有深度和厚度的,是人生本质的悲凉。这种悲哀的感情基调来源于她成长的地域,家庭,性别,更是源于她真实的生活经验。在小说中,她以一种诗意的,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写出人生的悲剧意蕴,反而让人阅读时更能接近书中人物所讲述的悲欢离合。人生的悲剧意味在萧红的笔下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表达,即使阅读过程中读者往往能体会到抱石投海的悲怆压抑,但也能从她孩童的天真视角里,如诗如画的语言之中,得到一种美的体验和享受。
一、悲剧意蕴的来源
从心理学上来看,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塑造了一个人最根本的人格和性情,更是对人的发展有着深远持久的作用。萧红的人生经历也实在地印证了这一点,童年时期她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爱的匮乏影响了她的感情生活。萧红人生的悲剧意味源于她童年的家庭不幸和成年后的婚姻不幸。而寻根溯源,家庭中位置的缺失是其悲情人生的根本。
从《呼兰河传》我们可以看到,萧红不被这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族所宠爱。她所感知的世界是冷的,苦的。原本东北就是一片荒凉地,自然環境就先天的缺少了江南水乡的温柔情义,天地总是肃杀的景象,人们也多是穷困潦倒。萧红便是这遗忘土地之子,也是大家族中被有意忽略的一个孩子,她的寂寞是双倍的。家中长辈不喜欢萧红,祖母因着她年幼好奇总捅破纸窗而在窗外等候萧红,当她再次伸手的时候拿了针扎她的手指,小小的心由此留下了阴影。而对祖母的离去,小小的萧红自然没有那样的悲恸。她写道:“祖母已经死了,人们都到龙王庙上去报过庙回来了。而我还在后园里边玩着。……不料除了后花园之外,还有更大的地方……除了我家的后院儿,还有街道,除了街道,还有大河,除了大河,还有柳条林,除了柳条林,还有更远的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什么声音也听不见的地方,究竟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我越想越不知道了……可见我不知道的一定还有,所以祖母死了,我竟聪明了。”[1]祖母的离去竟然成了一件意外的让萧红开了眼界的“好”事。与这个不接纳她的家庭斩断的每一丝联系,都促成了未来萧红离家千里,漂泊不定的人生走向。而当萧红尝遍人生百味后,转用一种童稚的口吻,讲述孩童时候的故事时,她的心底该是怎样的悲凉啊。而这一次出走,似乎也预言了萧红颠沛流离的一生。小小孩童的一个念头,似乎是一语成谶了。
除了缺少父母的关爱,遭受祖母的嫌恶,他人的冷眼,萧红的童年也有温情存在,这温情就来自于她的祖父。两个人在这个大家庭中都是边缘化的地位,这亲近便有了同病相怜的意味。祖父是萧红回忆往事中一抹少见的暖色。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受到祖父和萧红之间深厚的亲情。“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孩子似的。……我想,不掉井的鸭子抓都抓不住,可怎么能规规矩矩贴起黄泥来让我烧呢?于是我从祖父的身上往下挣扎着,喊着,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祖父几乎抱不住我了。”[2]前一段对祖父的描写中,让读者看了心生暖意,因在萧红的小说中难得有这样轻快的语调,也鲜有这样形象健康而性格开朗的人物。而后半段是写萧红喜欢吃掉入井里的鸭子,没有鸭子掉进去,萧红便撵着鸭子想它们落井,她恶作剧一般的天真行径被祖父制止了。这样带有童趣的回忆,因着末了的一句“祖父几乎抱不住我了。”转向了伤感。祖父年岁已大,而小萧红却是一天天飞快地长大了,长大了就意味着“少小离家老大回。”就意味着和祖父的分离,意味着祖父一旦离开了,在这个世界上就再没有可以疼她爱她可以让她依赖的人了。只是一句“抱不住了。”道尽了多少童年缺失爱的遗憾,未来人事不可知的悲哀。
二、悲剧意蕴在小说中的体现
作为一位女性,萧红看世界的视角是带有性别色彩的,而她的不幸是由在家庭中备受歧视的女性性别开始,所以悲剧意蕴体现在她笔下首先便是女性的悲剧。
萧红在小时候就因为“是个女孩”而失去了应有的宠爱,这无疑塑成了她性格中脆弱的一节,使她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多了一层悲哀和悲悯,更为之后她不幸的婚姻埋下了伏笔。作家笔下的世界正是其内心世界的映射,所以看萧红小说中人物的悲惨命运,先要了解她本人都承受了什么样的遭遇。萧红曾两次怀孕与生育。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时,由于萧红身体极度虚弱和经济上毫无保证,以及考虑到萧军的感受,便把这个前夫的孩子送给了别人。初为人母,就要经受骨肉分离的大不幸,难以想象萧红内心是怎样的煎熬。而萧红第二次与端木结婚,却怀上了萧军的孩子,生下来是一个死婴。从此萧红也再没有体会过孕育新生命的喜悦了。同时婚姻和爱情的不幸也剥夺了她对爱的渴求,体现在其笔下则是女性的悲剧,生育的苦难,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性对同性的排挤。这些故事透露出女性在男权制度下遭受歧视的性别悲剧,人生命运多舛的无奈。
在《生死场》中,月英的丈夫,对待快要病死的妻子,不但不给她饭吃,连水都懒得端一碗。竟然因为对生活的种种不满一气之下把一个月的女儿活活摔死。《马伯乐》中的马伯乐,已经为人父为人夫了,却不能在经济上自立,动不动就是“省钱第一,逃难第二”,没有一点责任与担当,哪有身为男性的傲骨和气节。
萧红忠实于人生经验与生活事实,表达了对制造女性悲剧的男性霸权的愤怒与攻击,体现了萧红的女权思想。[3]萧红的笔下,被刻画得最有些有肉的,是那些命运悲惨的弱女子。她们对生活也有过无尽的遐想和期许,只是终于在冷酷无情的历史和男权制度的压榨下,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在《五云嫂》中,丈夫因为逃跑而被杀。五云嫂成了寡妇,只有艰难地支撑着活下去。《小城三月》那个凄楚、动人的翠姨,被剥夺了选择情爱的权利,含恨而死。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那个折磨而死的团圆媳妇。这些女性都活在男权的阴影下,她们一直在设法逃离这个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但是“娜拉出走”之后,也是无处可逃,无所寄托。她们的悲惨结局是个人的,但说到底也是所有这类女性的悲惨遭遇的缩影,是人性的悲剧。
三、悲剧意蕴的审美表达
萧红的小说以悲凉为底色,但是其中也透露对于生的欲求和与之带来的美的意蕴。这种审美意味更多的是从她孩童单纯的看世界的眼光中得以表达,更是从她对自然景物的热爱中得到体现。成人世界的冷漠和人性的复杂在孩童天真的语言中起到了消解的作用。
在萧红的回忆型小说,如《呼兰河传》《家族以外的人》《小城三月》《手》等作品中,作家是以雙重的身份和视角来叙说故事。儿童的幼稚与成人的理性形成两种理解,这种距离直接造成了文本中悲剧、喜剧的交融。儿童视角是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新鲜与好奇来写的,语言简短明快,从而为整个故事铺上了一层鲜明的色彩。《呼兰河传》的第三章,写的是萧红对祖父的回忆。她是这样写景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接一个黄瓜就接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接,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天上去,也没有人管。”[4]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句子短促有节奏感,读起来十分轻快。而其中又能体会到长大以后的萧红对这段和祖父在一起,在花园里的时光,是那样的轻松愉快,拟人,比喻,各种修辞打破了写作的陈规,陌生化的语言使人细细品味其中的情感。这像诗句又像散文的写法使小说增添了可读性和审美意味。让读者在荒凉的土地上,冷漠的人性中,读出了一丝暖意,感受到生的希望和灵魂的洗涤。
景色的描写也不仅表达了萧红对自然的爱,也是烘托了萧红对书中人物命运的感情,情景交融或是以境衬情,都使故事更进一步填补了读者的审美感受。如《小城三月》一文以春天始,以春天终。春天里,翠姨恋爱了。作者将翠姨纯粹青涩的爱情和“我”对翠姨的祝福系于笔下的春天,因此春天显得可期可待,给人以特别的温暖和希望。然而三年以后,春天的原野上己经有了翠姨的新坟。作者感叹春天的短暂:“春来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地到另外的一个城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多住一些日子。但那是不可能的了,春天的生命就是这么短。”[5]其实,年年春天都相似,只是因为渗透了作者对翠姨爱情和命运的惋惜伤悼之情,春天也变得黯然失色,短促无情了。这里,自然景色和人物的命运、作者的情感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结语:
萧红的小说并不那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不像同时期其他的女作家,她们大多是从男女情爱之中发起对自我价值的追问,或是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宏大课题。而萧红是实在的关注着底层人民的苦难,关注那微小的个体命运,体现了她经受生活的种种苦难后,对人生深入的思考与对他人的悲悯情感。或许只把目光投注在这样的小人物的悲欢而忽略整体文坛的话语是她写作的一种缺失,但是这也是她的作品能打动人的特点所在。我们在她的作品中能实在地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体味到生命的“不能承受之轻”。
参考文献:
[1]萧红:《小城三月》[M].小说林,2007.07.10.
[2]萧红:《小城三月》[M].小说林,2007.07.10.
[3]姜一:《萧红悲剧意识论》[D].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06.05.30.
[4]萧红:《小城三月》[M].小说林,2007.07.10.
[5]萧红:《小城三月》[M].小说林,2007.07.10.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