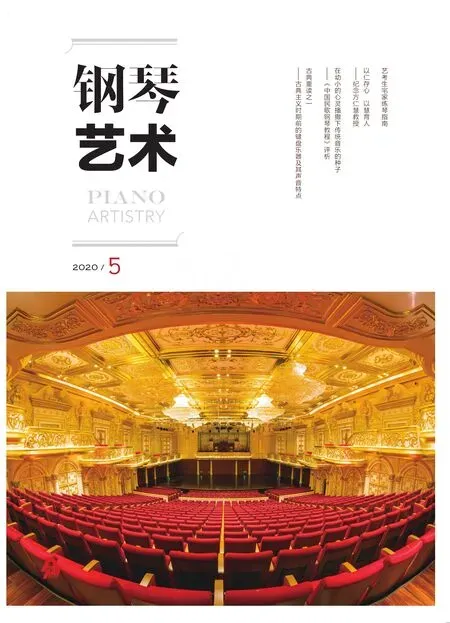八年纽约行,留学茱莉亚(下)
文/ 孙麒麟
茱莉亚的同学情
在茱莉亚这个人才聚集之地,每个人每天都在努力,忙碌自己的事。在这里能交到的朋友一定都是志同道合者。记得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第一个农历新年也是我离开家的第一个没有年味儿的新年,我和同班的几个中国同学一起坐地铁去中国城吃火锅、唱KTV,但一路上的欢声笑语掩盖不了我们在大洋彼岸的孤独和对家乡的思念。记得除夕夜,我们在中国超市买东西,一走进去,超市就在播放中国传统的新年音乐,一个女同学望着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说她想家了,想爸爸妈妈做的年夜饭。我一把把她抱过来:“没事,还有我们呢。”我也是在那一刻,真正懂得了海外游子对家和祖国的深深情意。
“出门靠朋友”这句老话的确不假,在平日忙碌和紧张的学习生活中,能有几个交心的好朋友分享喜怒哀乐绝对是莫大的福气。茱莉亚的圈子小,加上音乐系的同学一般都在四楼,大家的情谊多多少少也都是因为音乐而结缘的。记得有一次刚开学,我在卡普林斯基的课上弹了一首李斯特的作品,弹完下来我正要走,一个人从身后拍了拍我:“嘿,弹得不错!”我转头一看,是Kate Liu。没错,就是中国观众非常喜欢的“肖邦比赛”第三名获得者刘凯特(她的中文名字其实叫刘珒)。我一下愣住了,随后感谢了她的好意。那一次,是我们第一次说话。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琴房苦练斯科里亚宾《第二钢琴奏鸣曲》,准备过几天的音乐会。练着练着就有人敲门,我一看是Kate!她进来告诉我她好喜欢这首作品,能否听我弹一弹,我又一次愣住了,心想我怎么好意思“班门弄斧”呢,只好借故说我还没练好,而且正准备要去吃饭。没想到,她说:“既然你都要开音乐会了,就弹一点点嘛。”我想,那就豁出去了,本来只想弹一点儿,看她一直没打断,便一曲弹完了。曲终,我们俩都沉默了好久,终于等到Kate开口了:“麒麟,我觉得你可以弹得更有意思一些,曲目开头的节奏动机可以把时机把握得再好一些,我听你一直也在琢磨这个地方,要不要尝试把延长音收得慢一点儿?”说完,她便自己开始在琴上琢磨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为了一个小小的三连音揣摩了一个半小时。直到最后,她说:“对了!现在听起来对了!我觉得这才是你是想要的!”我一看时间,已是晚上九点,我们俩早已饿得不行了,我起身从琴凳上站起来拉着她的手说:“走,我们去吃晚饭吧。”那一刻,我知道,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熟知Kate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之所以她的演奏那么深入人心、极具浪漫色彩,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位思想独到、内心丰富敏感的女孩子。听她弹琴是有视觉享受的,看到她把手提起来,我就几乎能想象到那个纯美的声音。Kate的音乐张力极其宽广,给人一种荡气回肠的空间感。上回听她弹普罗科菲耶夫《第八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我跟她开玩笑说,这线条长得我都要喘不过气了。到如今,Kate已成了我家里的常客,到了周末的晚上,我们就时不时约在一起,品尝红酒、美食,欣赏音乐。就这样,最初的一次偶然,使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挚友。
自从在茱莉亚读博以后,我的圈子更小了,朋友之间的相处时间也变得更加稀少而珍贵。每天除了练琴,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博士班的同事们一起度过的,这样一来,身边的同事变成了亲人一般的存在。我们博士班一共有八名成员,其中有五个美国人,两个欧洲人,我是唯一的亚洲人,也算是给班里增加了点儿“东方气息”吧。开学第一节课,大家还略带生涩地互相自我介绍,结果第一学期下来,每天除了回家睡觉,其余时间大家几乎都是在图书馆一起度过的,这样的朝夕相处把我们八个人紧紧连在了一起。
我最好的朋友麦克尔是希腊裔法国人,长得跟阿波罗神似,而他本人也的确像是一位归隐于人间的“大神”。他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学院,并立即被留校任教,在工作了七年之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巴黎,来茱莉亚读博。我还记得当他平静地告诉我这个经历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并深深地为他的勇气惊叹。一位已经在世界知名的音乐学校任教的老师,竟能如此淡然地放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做回学生,只为向更高的目标发起挑战,这实在是难得的高人啊!能与这样优秀的人每日为伍,再苦、再累我也实属幸运!
作为两位读博的国际学生,我和麦克尔免不了要花费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在英文的阅读和写作上。可是,会五门语言的麦克尔,总是可以轻松找到对应的原文版本—很多都是希腊文和法文的著作。好几次,在我抓头挠腮、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麦克尔总能发挥他的语言优势,从原文的角度给我讲解,他还时不时解释说,有些词其实并不应该如此翻译成英文,因为很多古希腊文的含义和现在的希腊文不一样。前不久,我的第一场博士音乐会,麦克尔像一位良师益友一般,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从曲目的安排,到演奏风格的揣摩,他都诚心地向我提出建议。记得有一晚在演奏厅走台试音,结束后我转身发现观众席居然有一个人,是麦克尔!原来他想进来帮我听听声音效果,坐了好久却一直没有打扰我。
博士班里的另一位“大神”名叫西蒙,他是一位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的作曲家。说来还真是巧,我在茱莉亚读大三的时候,西蒙便是我的乐理助教,那时我有很多不懂的问题总会向他请教。后来只知道他研究生毕业了,也逐渐没了消息。没想到,几年过去,我们居然又成了同班同学!在开学典礼上,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彼此,他还开玩笑地说:“以前你是我的学生,现在我们可是同学了!”话虽如此,西蒙是一个功力极其深厚的音乐家,延续在大学时对他的崇拜,读博期间一有疑惑我总会求助于他。西蒙的父亲也是音乐界著名的学者,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音乐系任教,其关于舒伯特、勃拉姆斯、舒曼的著作堪称经典。上学期我选修勃拉姆斯相关课程的时候,找来的厚厚的书籍全是他父亲写的,我开玩笑似的跟他抱怨,没想到他说:“你要不要周末来我家?还能跟我爸聊聊,这样这些书也不需要全看了。”于是,在上一个感恩节,西蒙邀请我去他家,我第一次和他父亲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像一名小粉丝,看着这位声名大噪的音乐学家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来忙去,热情地招待着我们,而一旁客厅的书架上则堆满了他出版的书籍,那一刻我真是觉得这世界太美妙、太神奇了。西蒙目前热衷于研究14世纪以前的早期音乐的记谱法,他告诉我们,希望有一天他能开一堂课,指导大家把早期的纽姆记谱法转换成现代的五线谱,这样更多的早期音乐就会被世人所熟知并演奏。上学期,我和麦克尔就充当了一次他的“学生”,我们定了间教室,西蒙站在讲台前用他准备的教案给我们模拟上了一节课。一堂课讲完下来,我和麦克尔都坚信,他未来一定会是一位优秀的老师。
在茱莉亚读博需要一颗坚强不屈的心,其间所有的心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忙起来连正常的吃饭、睡觉都是奢侈的。记得最忙的时候,我有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有见到过太阳,每天早出晚归地学习上课,就凭着一口气吊着在坚持。每个深夜,我们博士班总是在图书管理员三番五次地催促清场之后才离开。好几次出校门,看着灯火通明的林肯中心,心中不免有些惆怅。有一个晚上,大家实在熬不动了,有人提议一起去吃饭放松一下。于是,我们一群人来到学校旁边一家墨西哥餐厅,一天都没有好好吃饭的我们,已经饿得“眼冒金星”。两杯小酒下肚,每个人都开始了互吐苦水的环节,可是那晚,所有心酸的故事都转变成了幽默的谈资,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全然忘却了一天的疲劳。也是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喝了两杯玛格利特鸡尾酒,第二天上课,他们都逗趣地问我:“怎么样,头疼吧?”
多么庆幸我们博士班是一个如此温暖的大家庭,每个人都为了大家共同的成长无私地给予帮助和关爱,成长中有他们的陪伴,回忆起来将是无比幸福的。
考大学,升研究生,冲博士
时至今日,已经在茱莉亚读博士的我,回想起第一次“撬开”这座音乐神殿的大门,仿佛就在昨天,一切都还历历在目。2012年3月,纽约的初春还没到,没有融化的积雪四处堆积在纽约的街头。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林肯中心,看到茱莉亚这所著名的艺术学校。校园里,每个人的脸上所洋溢的青春与活力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在想,我可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吗?
本科的入学考试,我被安排在早上十点半,因为时差的关系,那几天总是醒得很早,我心想能早点儿弹完也是好的,免得一天都心神不宁。那天一早起来,我不断跟自己对话,为自己加油。一个人来纽约考试,难免内心忐忑,看着其他考生都有父母陪着,我只有乐观地告诉自己:我可以!换好衣服,我来到学校四楼的琴房“热身”,极力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一切。当我来到309考场的时候,一个当志愿者的学生告诉我,前面晚了十几分钟,让我再耐心等一等。记得当时,我一个人坐在考场外,闭上双眼,那一刻我思绪万千,脑子里闪现了好多过去的场景。我想到了我在川音的王老师,我想到了我的父母,我想到了我3岁时第一次看到电子琴的情景。我再一次告诉自己,我准备好了,我什么也不怕,我就是要勇敢地去弹给他们听。309考场的大门打开了,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心想:哇,这么大的排练厅啊!一排评委坐在离钢琴十米开外的地方,他们都是钢琴系的老师,看起来很友善的样子。我刚一坐下,就有人问我想先弹什么,我说我想先弹李斯特的《梅菲斯托圆舞曲》,评委们点头示意我可以开始了。演奏时,我什么也没想,脑子里只有音乐,以及要如何表现我自己的音乐。记得那天我的状态非常好,虽然只是考试,我却似乎感到是在音乐厅演奏,整个人的身心都完全沉浸在了音乐中。

大学毕业典礼上和前校长Polisi合影

博士班全体合影
当天,除了《梅菲斯托圆舞曲》,我还被要求弹了贝多芬的《“黎明”奏鸣曲》和李斯特的《“鬼火”练习曲》。当我从头到尾弹完“鬼火”,正在想下一首是会被要求弹巴赫还是德彪西的《意象集》,评委说:“好了,今天我们就听到这里。”我站起来行了一个礼,便大步走出了排练厅。走出门的那一刻,我懵了:什么?这就结束了吗?我已经考完了吗?我居然如此顺利、完美地完成了这次考试!我开心得不能自已,就连门前的志愿者都说:“恭喜你,看得出来你很满意。”之后,我立即给远在中国的父母打了个电话,当时国内已是深夜,他们听到我无比兴奋的声音,也着实为我感到高兴,只记得他们说:“结果不重要,你自己满意就已经成功了。”那一夜,我是伴着热泪入睡的,觉得自己离梦想好近。
在从纽约飞回成都的飞机上,我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自己已经发挥出了很好的水平,忐忑的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我会被录取吗?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俯瞰这座繁华的纽约城,期望我还可以回到这座城市。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在一个清晨,我急性子的母亲把我从熟睡中摇醒:“麒麟,今天是放榜的日子,快看看到底通过了没有?”我打开邮件,便看到“Congratulations(祝贺)……” 更让我惊喜的是,学校还授予了我全额奖学金!自此,我的茱莉亚之旅在那一刻开启了。
大学四年期间,我每天的目标就是兢兢业业完成学业,尽力把每个科目都学好、学扎实。考研究生在当时似乎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打算,考试当天虽然没有考大学那般的彷徨和焦虑,但着实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虽然我那时已经是本校的学生,但是茱莉亚一向秉承着公平、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考生,也就是说我们本校的学生其实是和外校的考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没有任何区别对待,依然是秉承择优录取的原则。相信每一个考过茱莉亚的人都对这所学校有一种望而却步的胆怯,不管平日里准备得如何,上考场的那一刻,心中总有一种不安。
考研究生的那天下午,我候场的时候正逢考官们的十分钟休息时间,虽然里面的评审都是学校的钢琴教授,四年的时间我们也都彼此熟知,但是这依旧无法缓解我即将上场的不安心情。休息时间一到,我正准备进去,发现我们系的马丁教授走过来,他异常轻松地对我说:“走吧,麒麟,一起进去。”说着便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了309考场。说实话,那一刻我的心真的安稳了不少,我站在钢琴前,看着评委们温暖的微笑,仿佛在说:“放轻松,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听了你那么多次的专业考试了。”不知为何,那一次的考试,的确是我人生中最惬意、最安稳的一次现场演奏,就像是没有束缚的一种表现,自由又真实。从考场出来,我笑了,想起四年前的心境,和这一次完全不同,同时也真切体会到自己的成长。打开手机,卡普林斯基的短信跳了出来:“弹得太棒了,我为你骄傲!” 我开心极了,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那一年,我们茱莉亚在读的本科钢琴学生共十二人,有九个人决定考研,在激烈的竞争角逐后,只有五个人被录取。可喜的是,我的现场演奏得到了考官们的一致认可,我又一次收到了茱莉亚全额奖学金的录取书,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
要说真正令我回想起来仍然“毛骨悚然”的一次升学考试,那就是考博士的经历了。博士学位是茱莉亚整个学校最高最难的一个学位,每年招生人数寥寥可数。茱莉亚的博士学位对于专业演奏和学术研究两者都有极高的要求,要求考生通过录音初选、现场专业考试、学术面试和笔试等几轮的严格考核,而且所有考生不分专业,不分院系,统一竞争。也就是说,钢琴的考生不仅仅是和同专业的人竞争,还要跟报考所有专业的考生一同竞争。这也是为何某一年可能会有一个钢琴专业博士都没有录取的情况(说明其他专业的考生更强);或者另外一年,招了好几个作曲专业的博士,却没有任何弦乐专业的博士等。所以,每一年的博士班情况各不相同,竞争可谓是十分激烈。近几年,来自中国的茱莉亚博士生屈指可数,其中有我的大师哥孙嘉言,他如今已经博士毕业了。此外,还有我的好朋友郝端端和徐起,我们仨加起来就是茱莉亚目前在读的中国博士生。
茱莉亚的博士招生,除了竞争激烈的专业考试之外,最难也是最不可预料的就是学术面试那一关。面试的考官全部由茱莉亚博士委员会的成员组成,他们都是音乐界各个领域的专家。想在这些人面前卖弄学问,没两把刷子,只能被他们礼貌地请出去。我亲眼看见好几个考生信心十足地走进去,垂头丧气地溜出来。因此,我们都深知,茱莉亚的博士就是一座超高难度的高峰,狭路相逢勇者胜,最后能被录取的一定都是勇士。
我是在晚上十点左右才收到第二天的面试通知的。当时,考完专业筋疲力尽地倚在家中沙发上的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心想,这么晚还没给我发面试通知,估计是没戏了。十点的时候,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她没接到面试通知,问我收到没有,我顺口说我也没有吧,还没看到邮件呢。说着,我打开电脑刷新了邮箱,结果发现两小时前我的面试通知就到了!挂了电话,我赶紧洗了个澡就准备入睡,因为我的面试时间就是第二天的上午十一点!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一晚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里都在猜测考官们明天会问我哪些问题,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音乐的变革?还是近现代音乐的几个发展阶段?是巴赫与亨德尔的不同之处?还是关于德彪西和拉威尔的赏析?虽然我是钢琴的考生,但并不排除考官们会对交响乐、歌剧甚至芭蕾舞剧进行提问和考核。那一晚,我的大脑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把我之前所复习的音乐史从头到尾像过电影一般梳理了一遍。第二天一早起来,一夜没睡的我站在镜子前,那一刻我不断重复告诉自己:要勇敢、要乐观、不要怕,相信自己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
面试的地方在茱莉亚五楼的一间大教室,我到的时候前面的考生正在里面面试。我深吸一口气,只希望自己不要被这场面给吓倒。我进去的时候感觉还算轻松,可是坐下后一开口就发现自己的声音居然在颤抖—还是紧张啊!我拼命告诉自己要冷静,不要慌,还好,之后我的心情终于稍微平复了一些。本来规定的十五至二十分钟的面试,我感觉好像一整天那样漫长。那天的面试我回答了好多问题,考官们抛出来的一个个问题令我“应接不暇”,其中包括对调式音乐和无调式音乐的分析、对贝多芬奏鸣曲标题的讨论,还有对古典音乐不同曲式的分析,等等。
就在我自我感觉慢慢变好,没有在任何问题上卡住、发愁的时候,一位历史教授冷不丁地问了我一个关于1950年之后近现代音乐的风格问题。本来我以为他想让我列举近现代音乐各个派系之间的区别与特点,正当我说得起劲的时候,那位考官说:“不,我想说的是,很多近现代作品是以之前的音乐传统为基础而创作的,不论是从曲式构架还有和声创作上,那么你在这一点上是怎么看的?”如此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似乎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了。我当时停顿了好久,脑子里一直在快速回想我所有学习过的近现代作品,可是哪些又是和过去的传统音乐有联系的呢?突然,我一下子想到不久前我在音乐会上演奏的约翰·科里利亚诺的《幻想练习曲》,这不就是以传统的幻想曲曲式加以现代和声手法而合成的一部钢琴作品吗?!它的创作跟李斯特的《b小调钢琴奏鸣曲》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有不同章节之说,可是全曲一气呵成,没有任何停顿。它的和声奇妙,但是很多都是在传统和声的基础上加以变化音而构成的。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那位考官脸上逐渐露出欣慰的笑容,我知道,这道题我过关了。
当走出面试考场时,我整个人真的完全懵了,有一种不真实的虚无感。之前高度紧张的二十分钟已经消耗了我全部的体力和精力,我拿起包,不知怎么走到了四楼靠窗的沙发上,一直在那里坐了好久好久。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我应该处于不断“回血”的状态,消耗过度可能就是麻木的感觉吧。当晚,稍作休息后,第二天我去接着考了对位法和历史的笔试。交卷那一刻,神经上的紧张已经到了临界点,就连我的导师也发来信息:“麒麟,虽然还是白天,可是你快去喝一杯吧,终于考完了。”
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正拉着我的好朋友站在林肯中心的喷泉前。我曾经在那里虔诚地许下心愿,也是在那里,我得知我的美梦成真了! 我和好友紧紧抱在一起,热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深知,那是一份以无数汗水和无数个难以入眠的夜晚所换来的收获。在那一刻,喜悦和满足替代了所有的苦和累,一切都值得!
纽约这座城市,华丽的背后是现实的残酷。来纽约的人们,都是为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而放手一搏。白天,庞大的城市总是充斥着为了梦想而忙碌奔波的身影。晚上,华灯初上,三五朋友相聚在某个小餐厅、小酒吧,互相吐诉平淡生活里的点滴,似乎一夜过去,一切都会重生。在这样一个绚丽多彩的国际大都市里,每个人似乎都在寻找一份自我的归属感。刚去纽约的时候,我时常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在如此人才济济的地方,渺小的我时常感到焦虑和不安。后来的日子,我不断成长,不断面临挑战并接受挑战。留学的岁月不仅让我收获了知识,更是磨炼了我的心智。现在的我,不仅要完成博士的学业和专业上的演奏,还兼任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乐理助教、钢琴视奏及钢琴副科老师的职位,忙碌的行程让我每天更加充实和自信。慢慢地,我发现我的归属感往往来源于很小的事情:当教授肯定我的论文报告的时候;当观众起身为我鼓掌的时候;当我帮助过的学生在期末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告诉我自己收获很大的时候;有时,甚至是清晨起来的一束温暖的阳光,或是夜深人静自我内心的那一份笃定,也能给我带来无穷的幸福感。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所有走过的路、尝过的心酸、收获的喜悦,都已经注入我的血液,成为我身体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我深知未来的路还很长,只愿自己不忘初心,勇敢前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