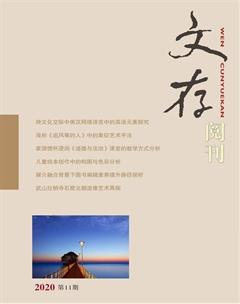武山拉梢寺石窟北朝造像艺术再探
杨宇辉
佛教造像艺术,是一个動态发展的、超越单纯宗教概念的开放性文化体系,其文化特质本身就具有地域、族群的多义性,吸纳与融合既是佛教造像艺术形成发展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而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作为中国的宗教艺术,它兼具了希腊印度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多重文化因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具备了从宏观到微观上对异文化进行自我调适和整合的能力,同时在文化特质的理解和阐释上,也就有了较大的弹性向度。拉梢寺石窟作为佛教向中原内地传播中途的一种改造形态,她既是早期佛教艺术的精神和审美载体,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梢寺石窟所在的甘肃省武山县,地处陇右之地,自古即归天水属辖,历史上无论是政区划分、民族分布、人口构成还是经济形态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均与天水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和众多相似之处,某种程度而言,两地同属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人文地域单元。这一区域在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方面是经营西域、辖制西北边防的前沿地带,而在文化交融方面而言则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与商贸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就其历史之久远、文化之复杂、内涵之丰富,特色之鲜明、作用之独特以及地位之重要而言,是中华文明地域文化中的一处典型代表。在这被厚重文化充分浸润土地上创造、传承的丰厚文化中,拉梢寺石窟虽长期隐于麦积山石窟的耀眼光芒间,但是作为融小佛龛、塑像、浮塑、悬塑和壁画于一体的石窟艺术综合体,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气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佛教艺术在西北地区的发展、演进与兴衰,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研究价值。
据拉梢寺石窟大佛的摩崖题记所载,该寺始建于北周明帝宇文毓武成元年(公元559年),这正是佛教自西汉末传入我国,在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并达到最为兴盛的时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加之佛教所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很容易安抚广大劳动人民。另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的提倡支持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作为一段激荡、动乱的大时代,长期的胡人入侵对中原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人民担惊受怕,希望有所寄托,而统治者则希望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了一个共同认可的精神家园,那就是“佛教”。也因为佛教,这群原本居住在北方的胡人,彻底的融入了汉人社会,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正常族群之一,这也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大时代,佛教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北朝在各个地方的统治者如建平公于义营建了莫高窟,大都督李允信修建了麦积山,泾州刺史奚康生开凿北石窟寺等,他们的开凿活动带动了当时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的大规模开凿,使我国石窟造像艺术得到了一次极大的繁荣和兴盛。正如拉梢寺造像题记所记的功德主尉迟迥本为北方来的中亚胡族,其姓氏原为西域于阗国(尉迟氏王朝)国姓。但据史称:“勋高效重,所在难方,崇善慕福,久而弥著,造妙像寺,四事无阂,法轮恒转,三学倍增” (《辩正论》卷四《周太师柱国蜀国公尉迟迥》),这正是北周时期中原内地与西域、中亚不断进行文化交流的客观反映。
“人不可能逃避他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他自己的生活状况。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化、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恩斯特.卡西尔) 依着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文化哲学”理论来关照拉梢寺石窟,我们看到这个居于中国西北一隅,地处陇右且处于丝绸之路文化传输节点上的文化遗迹,基于特殊的经济文化地理位置,其形态反映了多种文化符号系统的相互映射交错,这也造就了拉梢寺石窟丰富多元的文化特征。若仅从题材、技艺等浅层视角加以关照,会发现拉梢寺石窟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石窟造像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当转换视角, 关注多种文化的符号系统之间相互映射交错和反向辐射等现象,拉梢寺石窟作为中亚文化与东亚文化的集合体,表现出强烈的早期佛教造像特征,其背后所蕴含的更为内在的精神实质便呈现其独具的文化魅力,而其作为多文化的集合体也就有了深入考察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拉梢寺石窟最大的摩崖大佛造像,佛像通高34.75米,佛座高约17米,两旁的胁侍菩萨通高也有27米。充分反映出印度佛教造像艺术的风格特征,例如主体造像的体态丰圆适中、面部呈现深目高鼻、衣纹细薄贴身如“湿衣”,以及佛像身后的“佛光法式”等。特别是大佛底座处选取的造像题材为象、狮、鹿等神兽,风格形式上近于写实,尤其是中间一头大象头朝前的形式常见于中亚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的装饰手段,例如在我国新疆克孜尔石窟第224 窟的壁画中就有类似的大象画面,生动反映了早期佛教造像艺术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美国学者罗杰伟在《北周拉梢寺艺术中的中亚主题》一文对此有着较为详尽的论述,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拉梢寺北朝摩崖造像与古代中亚及西域的渊源和关系。
与国内其他地区石窟寺摩崖雕刻的浮雕造型观念相比,拉梢寺石窟在雕塑语言的运用方面要显得自由许多。由于摩崖造像所处崖面并未完全处理为平整光面而多有自然起伏,因此造像不过多受制于空间透视关系,浮雕的起位和层位的关系相对来讲更加服从于对画面整体效果的把握。如上部佛像的造型由于各层位起位较低而形体的压缩程度也较大所以呈现出强烈的平面特征。而下部的象、狮、鹿等动物造型则较为从容地处理了各层位的空间结构和形体特征,使其造型更趋立体写实。因此总观拉梢寺石窟会发现,各个位置和区域的浮雕在处理手法和空间构造上既有对空间立体形态的追求,同时又兼具着某种强烈的平面的、线性的审美形态。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如此巨大的崖面上建造所受材料技法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同时也反映出中原传统雕塑与绘画平面化造型的独特审美特征。
这种造像特点和手段,在西域地区和我国北方多有使用,如麦积山石窟以及炳灵寺石窟等都采用了这种技法。拉梢寺由于所在山岩属第三纪砂砾岩,其岩石结构松散且颗粒粗大,无法进行完整的雕刻制作,因此在修造时多利用自然洞窟中或者崖面上较为垂直平整的岩面对初坯进行大形的雕凿,在取得初步的整体形态后再对需要精细造型的部分打入木桩,然后进行悬塑或施泥彩绘。拉梢寺石窟摩崖造像的具体制作过程就是在崖面上先凿出一佛二菩萨的石胎大形,这个阶段的造型虽不及普通的石雕精细,但也需要将造像的大形、五官的形态、四肢的动态和衣纹雕出大概,同时为了泥层能够牢固,将佛和菩萨的袈裟和裙裾衣纹雕得比较突兀而细密,减轻了泥层压力,然后在其表面依序敷设几层泥,直至完成塑造并施以彩绘。
底层粗泥内加入了厚约2-3厘米的麦秸草秆,这层主要用作确定造像的形体、比例和动态等,同时做出大致的造型细节。粗泥的使用正是要利用其适度开裂并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同时将上下几层泥料的干燥收缩引向泥料内部,以此避免完成的造像出现表面开裂现象。这种做法对最怕泥料开裂的雕塑来说,真的可以称作是“以毒攻毒”了。在此基础上敷设的细泥,一般都要经过反复淘洗沉淀然后加入各种物质以提高胶结性能和强度,现代村龛小庙多用棉麻碎屑等,但据古代史料所载常用的辅料有“糯米、粳米、小油、黄蜡、桐油、硼砂、皂角、土布、生绢、瓦粉”等。拉梢寺石窟经历一千多年风雨侵蚀,但摩崖造像表面仍然坚如磐石且细腻如滑,足见其时匠作工艺之精湛,不由使人赞叹古人的聪明智慧。
拉梢寺石窟北朝摩崖造像,从艺术特征而言展现出某种强烈的平面、线性的审美意识,这与部分造像的对空间立体形态的追求形成了极为有意味的并置关系,呈现出我国早期佛教造像艺术民族化的文化交融图景,这也正是其独具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