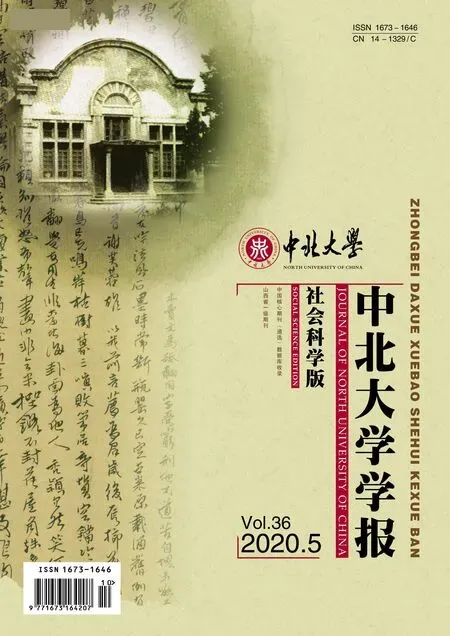《白色病》的危机主题*
智 丽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卡·恰佩克(1890~1938年)是世界上被翻译介绍最多的捷克作家之一, 被伏契克誉为“捷克文学最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家”。 作为小资产阶级作家, 恰佩克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色彩。 由于小资产阶级不占有独立的生产资料和金钱, 资本的集中与扩张使他们生活贫困。 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样都要为生计奔波, 但对私有资产的留恋又使他们畏惧无产阶级的主张。[1]因此, 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处于一种既憎恨又依赖的暧昧关系, 经济上的附属地位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故而, 在面对社会丑恶时, 恰佩克内心异常挣扎, 在相对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一直找不到改变现实的出路。 后期, 报社的工作使恰佩克得以深入接触社会, 他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残酷与黑暗, 逐渐坚定了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信念。 恰佩克公开参加反对法西斯的活动, 以“即使我终生沙着嗓子或变成哑巴, 现在我也要尽力地大声喊叫”的坚定态度, 创作了小说《鲵鱼之乱》 《第一救生队》、 剧本《白色病》和《母亲》等作品, 歌颂工人阶级的战斗, 抨击法西斯暴政, 成为为捷克人民呐喊的剧作家。 库兹涅佐娃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其他艺术体系的关系》中这样评价恰佩克:“对他来说, 重要的是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灭亡和它对付法西斯袭击和捍卫人的精神财富的软弱无力”。[2]328恰佩克善于运用现代派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 以一个个怪诞离奇而富于真实感的幻想世界揭示当今时代背景下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危机, 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恰佩克说:“当今的世界冲突可以被定义为经济和社会冲突……它最戏剧性的方面是两个对立理想的碰撞。 一方面是人类民主自由、 世界和平以及对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的尊重的道德理想。 另一方面是日益兴盛的反人类理想, 即权力, 它至高无上, 体现在国家在很多方面的扩张。”[3]描写这种特殊的冲突是恰佩克创作《白色病》的动因。 在作品中, 他以一个“灭亡”的故事预示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毁灭, 具体而言, 通过呈现生态危机、 信仰危机和伦理危机三大危机, 展现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之中的芸芸众生的境遇与选择, 表达了他对战争年代人类生存状况的忧虑。
1 战争背景下的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表现和表征。[4]作为一部反战戏剧, 恰佩克在《白色病》中极力声讨战争的残酷和不义, 谴责了以军火商克吕格男爵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以元帅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 侵犯他人权益、 危害社会的丑恶行径。 生态环境作为文明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承载场所, 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 克吕格男爵是兵工厂的负责人, 在患白色病后, 仍不放弃任何机会, 变本加厉地压榨工人, 并要在隔离白色病人政策下来之前抓紧生产铁丝网牟利; 对金钱的狂热似一张巨网, 他深陷其中, 无法抵抗发战争财的诱惑。 元帅是极端民族主义者, 巧立名目发动侵略战争; 他残酷冷血, 听到克吕格工厂毒气筒发生爆炸导致车间劳工全部死亡的消息后, 他表示“有点惨, 可是结果倒是令人满意的”[5]375。 作为一个冷漠的战争机器, 战场的血腥与惨烈没能激发元帅的恻隐之心, 只有战争的胜利才能带给他巨大的喜悦。 元帅与克吕格男爵相互勾结, 互相利用的关系, 加剧了底层人民生存的艰辛和痛苦, 暴露了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产阶级压迫工人和摄取最大利益的有效工具。 医生加伦博士则代表着正义, 他坚持原则, 不为金钱和权势所动, 在克吕格放弃生产军火之前拒绝对他施以救治。 最终克吕格男爵选择了自杀, 为专制暴政殉葬, 他的生命消散于对利益的贪婪追逐中, 他的结局揭示了施暴者终将走向自我毁灭的命运。 正如剧本中的第一患者说“在今天文明的条件下总不能让这么多人死去”[5]358, 剧本中的元帅隐喻希特勒, 具有毁灭性威力的“白色病”暗指法西斯主义是“白种人”道德的大崩溃。 像麦克尼尔所说:“在欧洲扩张的整个过程中……土著人口的减少以及欧洲人口能够占领如此广大而多样的土地, 无不得益于特殊的现代疫病模式。”[6]136恰佩克用疾病隐喻极权统治下的战争, 像古希腊英雄生来就与悲剧命运连结在一起一样, 疾病的到来像一次上帝对人间的“洗礼”, 在冥冥之中完成了对人类的警醒与教化。 战争则是人类欲望造成的悲剧, 是人为的恶果。 恰佩克采用象征手法表现了战争对生命的毁灭, 但是在剧本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扩张显得轻描淡写, 对疾病造成的灾难场面作了精心描绘, 这看似“顾左右而言他”的匠心独运使作品更具批判性。 法西斯主义是反人类的,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鼓吹日耳曼种族优越论, 并称“惟有地球上充分之空间, 能保证一民族之生存自由。 德意志民族亦惟有籍此种方法始能保障其为世界之强国”[7]327。 法西斯主义者美化侵占别国土地, 霸占弱小国家的恶行, 为暴力披上“合理”的外衣, 并鼓吹无知的民众为这场人间惨剧喝彩, 所以才有了一幕幕为战争欢呼的场景: 深受法西斯主义思想毒害的人们以“传播优秀文化”为借口麻痹自我, 享受着罪恶的“狂欢”。 希特勒在军工厂投入了大量资金, 大部分国家财富都被用来生产武器。 据希特勒自供, 1933~1939年间, 国家的总支出为1 502亿马克, 其中直接作为军费支出的有900亿马克, 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一半以上。[8]43战争对被侵略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 被炮弹摧毁的土地中所含的不可降解物威胁着人类的未来, 人们不得不忍着伤痛重建家园, 家与国、 国与国良好关系的建立都在考验着饱受战乱的人民。 加伦博士的发问引人深思“和平, 真的要花那么多钱吗”[5]372? 人类文明的未来应在和平的气氛中源源不断, 不应被炮弹硝烟遮蔽。 恰佩克正是通过作品揭示人类的生存危机和预示生态灾难; 在进行伦理批判的同时, 提醒人类达到与自然、 社会以及自我的和谐相处的必要性。
2 精神领域的信仰危机
理性与信仰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两大元素, 他们的关系问题一直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全过程。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宗教神学到中世纪基督教对信仰的推崇, 再到近代哲学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辨析, 理性逐渐为大众推崇。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描写, “在人类纯粹理性中, 上帝是不存在的, 而在人类实践理性领域, 上帝的存在是道德的一个必然要求”, 他指出上帝是纯粹理性的理想实体化。[9]上帝, 既是信仰的实体, 又是向善的安慰。 上帝仿佛一把标尺, 人类依信仰而行动, 行善可得到上帝的认可和庇佑, 作恶则会受到报应和惩罚。 因此, 人的道德行为与对上帝的信仰直接关联, 信仰上帝无疑会为人向更高的道德标准前进提供动力。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所说:“假如没有上帝, 人什么事情不能做啊!”[10]890近代科学理性的发展和壮大对宗教信仰造成一定冲击, 人类掌握了无所不能的科技,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加科学,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加强大。 尤其在19世纪末尼采提出: 科学的存在使“人变得不再那么需要一种彼岸结局来解他的存在之谜”[11]78, “上帝死了”, 随之而来的是上帝信仰及宗教的“神话”体系被质疑。 人类既不需要上帝的“守护”也放弃了对上帝的拥护, 信仰体系失去了牢固的精神支柱, 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意志及行为具有无限的超越性。 从前有一个惩恶赏善的上帝, “行善上天堂, 作恶下地狱”成为道德行为的基本前提; 如今上帝的存在受到质疑, 没有永生轮回之说, 同时也失去了惩罚罪恶的“效力”, 人类对道德信仰充满怀疑, 失去了行善的动力, 更遑论对行为的约束。 随之而来的便是道德崩塌, 欲念和邪恶大行其道。
当人类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运用到社会关系中时, 极端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变成“正义”, 侵略和谋杀则成为“正当手段”。 纳粹主义者大肆虚假宣传, 将充斥着利益和血腥的战争包装上“民族”与“胜利”的外衣, 不明就里的民众对祖国的热情就这样被利用作为对侵略战争的支持。 在《白色病》中, 陷入信仰危机的人们和加伦形成了鲜明对比。 加伦成功研制出解药, 说:“不要怕, 这儿有药啦—叫他们让本国政府的首脑许下持久和平的诺言……同各国订立永久永久性的条约吧……喏, 然后白色病就完蛋了, 不是吗?”[5]354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只医治穷人时, 他说“如果有钱人真心要和平, 他们起的作用更大”[5]345-455。 而这一切在研究院院长西格柳思看来是荒唐的。 西格柳思反问加伦:“什么是我们民族的义务和将来, 您加伦先生作为一个外国出身的人对这个还没有足够正确的认识。”[5]356他和所有受法西斯主义荼毒的民众一样, 都认为战争是国家获得发展和强大的途径, 加伦所渴望的持久和平只是荒谬的乌托邦。 为了控制疾病, 西格柳思甚至想到将所有患者运送到集中营的办法, 企图通过隔离病人阻止白色病蔓延, 以便稳定民心。 缺乏精神信仰, 医生不再救死扶伤, 舍己为人; 元帅不会因为对人类痛苦和恐怖的同情而停止战争; 患者大声呼喊“基督耶稣”, 祈求早日得到治疗白色病的药。 而上帝似乎故意在和人类开玩笑, 始终没有给绝望的人类带来生机。 加伦博士是战争世界中唯一一位顽强而执着的战士。 他始终以一己之力阻挡着屠杀机制, 默默忍受着冷落与谩骂, 乞求人们停止战争, 珍惜生命。 在第三幕, 元帅发现自己得了白色病, 只剩六个月的生命时, 慌张不已, 他为自己被造物主舍弃而惊慌、 绝望。 而那久久没有到来的拯救正是上帝对人类灵魂的教化: 生命不是冰冷的数字, 应该去鲜活地绽放, 去迎接更多的可能性和美好, 而不是被残忍地扼杀。 在生与死的挣扎中, 有人觉醒有人沉沦, 有人陷入绝望的狂欢, 有人感到清醒的痛苦。 在这场生存与权力的冲突中, 恰佩克揭露出人类灵魂所经历的绝望和重负, 更暴露了人类固有的生命权利惨遭践踏的真相。 作者通过一幕幕“悲惨世界”揭示: 失去道德和信仰的约束, 人类必然会陷入信仰危机, 人类文明也将面临消亡的命运。 同时也告诫人们, 在金钱至上和利己主义的诱惑下, 唯有坚定理想与信仰, 守住灵魂的净土, 人生才能有所附骊。
3 社会关系的伦理危机
《白色病》通过三个层次完成叙述, 以元帅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是具有最高权利的一级话语层, 以克吕格男爵为代表的资本家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二级话语层, 三级话语层则由父亲、 母亲等平民患者组成。 当叙述聚焦到普通民众身上时,恰佩克使用饱含同情的笔墨描绘他们平凡而凄苦的生活。 面包房的师傅, 工人或穷光蛋等, 他们是被压迫被愚弄的底层, 同时也是大灾难下家庭伦理危机的最直接感受者。 贫穷的生活暗无天日, 只依靠微薄收入的他们对白色病表现出的恐惧更令读者动容。 “在文学文本中, 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 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 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 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 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 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 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12]263-264第一幕第三场出场的是一家人, 剧中的“父亲”就具有多种伦理身份。 首先, 他时刻以丈夫的权威压制着妻子。 他内心鄙夷妻子, 因此, 与妻子沟通时总表现得不耐烦, 并一味否定妻子的观点。 妻子对白色病造成的死亡充满惧怕, 总是忧心忡忡, 同情他人被病魔夺走生命, 丈夫则沉浸在升职的喜悦中, 甚至说“我们应该为这个麻风病来感谢上帝呀”[5]360“假如我得在这白色病和持久和平里挑选的话, 那我情愿选白色病”[5]363。 就在他洋洋自得之时, 情节突转, 妻子不幸患病。 于是他们来到了加伦博士的麻风病诊所, 加伦博士只医治穷人的原则是世人皆知的, 但在加伦面前, 丈夫说自己是克吕格企业的会计主任, 并坚决不愿意放弃这份还没有被正式任命的工作来换取治疗妻子的机会。 加伦博士无可奈何, 这一家人就此下场, 其结局不得而知。 正如托马斯所说:“在男性沙文主义的影响下, 男人可以通过金钱和权力获得美感和性满足感, 而女人则被男人所消耗。”[13]。 其次, 父子矛盾重重, 没有丝毫亲情可言。 白色病导致很多中年人死亡, 子女认为这场灾难是为“年轻人开辟地盘的事情”, 甚至 “希望这个病再拖延一个时候。”[5]337他们无视疾病会降到父母身上并带走父母生命的可能性。 父亲所代表的中年人同子女所属的青年人在疾病面前成为完全对立的阵营, 父子血脉结成的亲密关系被生存的欲望扭曲, 对未来的渴望使父子产生了巨大鸿沟, 争夺生存权利的选择危及了父子的伦理关系。 最后, 丈夫的自私行为将全家置于一种孤岛型的处境。 妻子同情住在三楼得病的老太太, 想给孤零零的她送点汤水, 丈夫果断拒绝, 并说“走廊里那股臭味儿, 叫人都不敢回家来了”[5]335。 生命的消亡和惶惶的气氛使他们时刻处于崩溃的边缘。 人们被死亡牵扯着神经, 人人自危, 人们为了防止被感染, 都将自己封闭起来, 避免同他人来往, 更拒绝主动帮助患者。 世俗群体建构的意义世界在长期隔绝和孤独的个人生活中——这种隔绝和孤独甚至可能是一种主动的精神选择和对世界自觉理解的结果——必然会面临解体, 从而使人陷入意义缺失甚至无意义的孤独和焦虑中, 进而导致精神危机。[14]邻里关系的缺失造成了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割裂, 而白色病造成的无力感和不确定性等一系列困境必然会影响个人身份的构建, 从而导致个体化危机。 恰佩克通过一家人的矛盾与悲剧揭示了灾难面前的选择困境。 他们面对的一系列难题: 团结或孤立, 失去与拥有, 等待与争取……考验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丈夫受传统父权制和男性沙文主义的影响, 不能协调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又将家庭与外界隔绝, 因此, 丈夫注定会因为父子伦理危机和个体化危机而失去一切。
最终, 元帅下令停止战争, 等待着加伦医生对他的救治; 而加伦在赴元帅府途中被狂欢的人群殴而死。 加伦的意外死亡使人倍感震惊, 整个剧本也划上了句号, 故事似乎在尚未被讲完之时就戛然而止了。 恰佩克的开放式结局引人思考: 如何界定生与死, 如何理解人生的不确定性, 以及存在的意义。 生命是最脆弱的东西, 人们治愈白色病的希望随着加伦的死而消散, 所有人都被判了肉体的死刑; 人可以超越生命而存在?答案是肯定的。 加伦坚守着心中的正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以拯救更多的生命为己任, 发明药物救治疾病, 更期盼解药能够唤醒人的良知, 以一己之力拯救被战争裹挟的世界。 他代表了恰佩克的民主主义追求, 同时也引发了对战争创伤的反思: 精神的混乱和人的孤独感将伴随人的一生, 人类的自我救赎才是未来所在。
4 结 语
恰佩克对生存的关注, 对人性、 人类文明的思考体现着作家的入世情怀; 因而他在小说中对危机主题的呈现, 既不是故弄玄虚的预言游戏, 也不是危言耸听地制造紧张, 而是以文学关照现实, 以提升人的精神为己任, 以赋予作品以道德力量为目标的创作活动的必然结果。 他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作家关注人性的特点, 表达了对生命和人权的虔诚尊重, 对自由与和平的热爱, 对真理与正义的追求等美好理想。 库兹涅佐娃在对恰佩克和卡夫卡的创作风格进行比较时发现, 二人都采用抽象概念“具体化”的手法, 但“讽刺作家恰佩克的风格概念和他的作品题材的整体结构是相一致的, 完全没有失掉幻想情节和夸张手法的具体内容”[2],恰佩克采用写实与象征相结合的手法创作戏剧, 他笔下幻想性的情节都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 因而, 恰佩克创作中强烈的象征意味没有带来意义的不确定性。 他突破了戏剧创作中的一些旧的模式, 例如不写明剧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甚至对剧中人的国籍也不加说明, 借以强调他所写的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并不局限于捷克斯洛伐克一国, 从而使他的剧作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