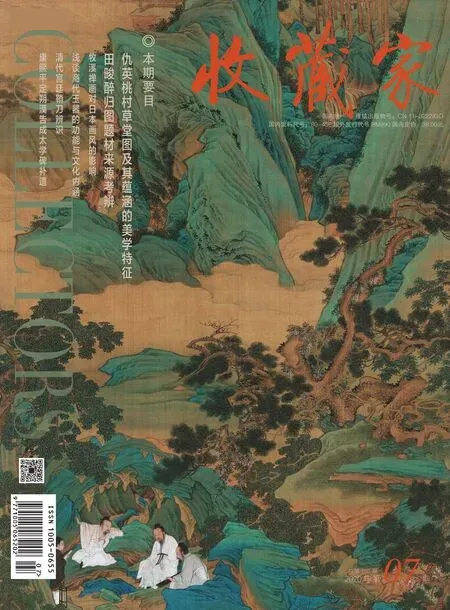古滇青铜贮贝器考
——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为例
□ 王志强
1955~1960 年,云南省博物馆在晋宁石寨山先后4 次发掘了50 座墓葬。晋宁县汉代为益州郡滇池县地,益州郡置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为滇王国故地。第6 号墓出土的滇王金印,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随着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羊甫头等同一文化类型的墓葬群和器物的发掘清理,大量辉煌的古滇国青铜艺术展露在世人面前,而贮贝器则是古滇国青铜艺术的典型代表。贮贝器约出现于战国早中期,经过秦、汉的发展,在西汉中期达到顶峰,后来随着古滇国的湮灭,古滇国所独有的青铜贮贝器也便烟消云散了。
据现有的资料统计,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贮贝器共42 件,且仅出土于滇池地区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呈贡天子庙三处墓葬中。其中晋宁石寨山出土了36 件,①江川李家山出土了5 件,②呈贡天子庙出土了1 件。③当然,也有少量流散于世,估计贮贝器总数不超过五六十件。④从贮贝器出土的墓葬情况可以看出,贮贝器仅见于大中型墓中,其拥有者是滇王及滇国贵族、功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古滇青铜贮贝器5 件,皆为一级品,它们是:束腰筒形立牛贮贝器(江川李家山M21:66),虎耳束腰筒形七牛虎耳贮贝器(晋宁石寨山M13:6),虎耳束腰筒形诅盟场面贮贝器(晋宁石寨山M12:26),鼓形纺织场面贮贝器(晋宁石寨山M1:3),叠鼓形贡纳场面贮贝器(晋宁石寨山M13:2)。
一、贮贝器的器形及与铜鼓的关系
贮贝器的器形大致可以分为束腰筒形贮贝器、虎耳束腰筒形贮贝器、鼓形贮贝器和叠鼓形贮贝器四种类型,现结合国博馆藏品分别介绍如下:
1. 立牛贮贝器(图1)

图1 西汉 立牛贮贝器
这件立牛贮贝器是束腰筒形贮贝器较早阶段的器型代表,出土于江川李家山第一类I 型墓(年代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以前,其上限或可早到战国时代末期)中。整体呈竹筒形,器盖上立一牛,套盖,器盖以子母口的样式与器身相扣合,器盖和器身各有两小耳相对,用以穿绳而联结。三扁足。器内有贮贝。
立牛、器盖和器身(不含足)高度的比例约为1:1:3。器盖上宽下窄,器身上窄下宽,整体外形像一节竹节。修长而流线型的设计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依然具有一定的审美。上下器耳的存在使得这件贮贝器在扣合时能保持在正确的位置,一头牛焊铸在器盖两耳连线正中的位置,牛头、牛角的朝向规定了贮贝器的正、侧位置,体现出滇国工匠对造型设计的审美追求。
2. 七牛虎耳贮贝器(图2)

图2 西汉 七牛虎耳贮贝器
这是一件虎耳束腰筒形贮贝器,器盖直径与器身底径大致相等,套盖,器盖与器身可以紧密扣合,不留缝隙。器盖的盖钮为一小铜鼓,一牛立其上,六牛围绕在器盖边缘,首尾相连,从上向下俯看时可以看到6 头牛的牛身呈六边形,立于铜鼓之上的牛把六边形切割成两个等腰梯形,极富几何美感。三兽爪型矮足。器身最细的腰线两侧分别焊铸两只向上攀爬的猛虎作为器耳。虎头朝上,虎口大张,其中一虎虎尾向下伸展,尾尖贴靠在器身靠下的器壁上,另一虎的虎尾向身体内卷缩,尾尖贴靠在器身中部略下的器壁上,虎耳流畅的线条与微缩的束腰筒形器身具有互补感。
虎耳束腰筒形贮贝器的造型出现于西汉中晚期,它相对于束腰筒形贮贝器要更复杂,简单来说,小耳发展为虎耳;器盖上焊铸的牛的数量由少变多,人物铸像开始出现,铸像内容趋向复杂;器盖由套盖变为平盖、套盖皆有,平盖居多;器身上下两端向外侈出,中间缩进,宛如一个细腰的美人;足底由一般的三扁足、矮足发展到三兽爪足、三踞坐人形足等,只有一件七牛虎耳贮贝器为四足;器身或光素无纹或浅刻图案。
3.诅盟场面贮贝器(图3)

图3 西汉 诅盟场面贮贝器
诅盟场面贮贝器的器身与七牛虎耳贮贝器形状相似,但器身壁比七牛虎耳贮贝器厚重,似乎是因为有了更多承重的需要。器身两侧的两虎耳形状相似,张口向上攀爬状,虎尾下垂,向外翻翘,两虎身上的纹饰不同,一为圆点纹,一为线纹(图4)。器盖为平盖,器盖上沿直径略大于器口直径,下沿直径基本等于器口直径,但是扣上器盖后与器身之间稍有缝隙,闭合不严,可能是器物有变形导致的。

图4 诅盟场面贮贝器身不同纹饰的虎耳
4.纺织场面贮贝器(图5)

图5 西汉 纺织场面贮贝器
纺织场面贮贝器属于单体鼓形贮贝器,它是用击破鼓面的废铜鼓改制而成的,其方法是将一铜鼓去掉鼓面,加一圆形器盖,再于铜鼓底部焊接一底。器型特征为收腰,足部向外侈出,胴部(鼓胸)与腰相接处有四绳纹耳(铜鼓原有的四耳),直径24.5 厘米的器盖上,焊铸有人物18 个,鸡、犬各1 只。另外在圈足处新焊接了圆雕飞鸟2 对。
5.贡纳场面贮贝器(图6)
贡纳场面贮贝器属于叠鼓形,此器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上鼓去掉鼓面,替换为器盖,下鼓再焊接上新的鼓底,两鼓接铸后合为一体(图7)。但是此鼓出土时上鼓已残,只余残高40 厘米的下鼓和鼓沿上的焊铸物,有立体人物、牛马等,其中人像17,牛、马各2,胴、腰间铸4 环耳,圈足处焊接4 卧牛。
随着虎耳束腰筒形贮贝器的流行,鼓形贮贝器开始出现,分为单体鼓形和叠鼓形两种。不论是单体鼓形还是叠鼓形贮贝器,其所使用的鼓体,从形制上来说,都属于石寨山型鼓。石寨山型鼓是中国南方八个标准式铜鼓的其中一种。⑤其形制特征是:鼓体如圆墩,束腰,中空无底,侧有四耳,可系绳索悬挂于木架上敲击,也可置于平地上敲击。铜鼓是从炊煮食物用的铜釜演化而来的,之后铜鼓用于敲击,成为独立乐器;其声穿透力强、响度大、传声远,被用于战争号令、祭祀活动等场合,既是实用器也兼具礼器的职能,故有“北鼎南鼓”的说法。但在鼓形贮贝器开始出现的西汉时代,铜鼓在古滇国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它用于节庆、歌舞、赛神、传递信息、指挥战阵等场合……以滇国出土文物为例,铜鼓虽然也在宗教祭祀时担任重要角色,但也经常以不同的材料变成滇人脖子上的饰品、臀下的坐垫,其早期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⑥并且铜鼓还做过贮贝器的替代物: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二次清理发掘20 座墓,共出土15 面铜鼓,其中有9 面却置,器内贮满贝壳,还有“一鼓却置,一鼓扣于其上,内置大量海贝”的情况。⑦肖明华研究认为:“这种现象属于一种功能上的借用,滇人把作为礼乐器的铜鼓直接用来装贝,体现出滇文化中权力和财富相统一的观念。”⑧
二、贮贝器的铸造工艺及装饰特征
古滇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显示出极高的水准,不仅门类齐全,而且铸造工艺十分精湛,青铜贮贝器的铸造更是因其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为世人所称道。
1.贮贝器的铸造工艺
贮贝器器身的铸造使用的是范模铸造法。先根据贮贝器的大小、器型制作出一个与之相同的泥制模型,再将需要的花纹图案刻在泥模的相应位置,最后用此泥模(内模) 翻制外范,外范一般为对称的两块或四块,内模、外范分别制成后,按照所需的厚度,均匀地刮去内模一层,所刮厚度即铸出贮贝器的壁厚;浇铸贮贝器这样的大件青铜器时,需要有大量的铜液,铜液炼出后,工匠们必须通力协作,配合默契地重新浇铸,使铜液不急不缓地注入范腔,直至饱满为止,等到浇铸冷却后,剥去外范,一件贮贝器便即形成。⑨贮贝器器盖上的立体装饰物以及虎耳束腰形贮贝器腰线上的虎耳、兽足等,应该是用失蜡法单个铸成后再接铸到器身上的(图8),相比于其他铸件,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表面非常光滑、美观,没有范线(图9)。⑩有些贮贝器器盖上的人物(如纺织场面贮贝器器盖上监督纺织劳动的贵夫人)采用了鎏金技术,即将金粉和水银的混合物涂抹在青铜器表面,经过烘烤,水银挥发,金粉就留在器物的外表,且不容易脱落。 当然除了这些基本的技艺之外,贮贝器的铸造还要配合锻打、套接、模压等其他方法及一些艺术加工才能制作完成。

图6 西汉 贡纳场面贮贝器

图7 贡纳场面贮贝器上下两鼓接铸痕迹

图8 贮贝器身虎耳的接铸痕迹

图9 贮贝器兽足的接铸痕迹
2.早期以牛为题材的立体装饰物
贮贝器的产生,首先是作为一种日常需用的容器,所以其造型也是从实际出发而设计的。但是即便是基本的造型,如果在盖、钮、把、耳、棱、足等部分稍加模仿或变化,就会使得原本单调的器皿变得丰富多彩,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装饰方面的特色。古滇青铜贮贝器立体装饰物主要是器耳、器足和器盖上的附饰物,其最富特色之处是器盖上的立体装饰物。
早期的贮贝器器盖上的立体装饰物只是动物,且以牛为主要表现对象。国博藏这件立牛贮贝器器盖上正是一只牛,巨大的角,雄健的身姿,作为盖钮用来开启器盖也颇为趁手、便宜,可谓既美观又实用,体现出古滇青铜器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立体装饰物,也称圆雕。作为器物装饰的附饰式圆雕产生于史前新石器时代,历经夏商周的不断发展,到战国时期达到高峰。 商周青铜器最早的附饰式动物圆雕是商早期扁兽足鼎,其足部为夔龙形;至商周,在青铜器的足、耳、、捉手、提梁等位置出现了立体的动物形体,有的仅头部、足部,有的是全身;附件性圆雕,主要是将盖钮或捉手、耳、足的支柱等用鸟兽的造型加以表现,既具真实性,又起到了强烈的装饰效果。商周时期附饰式动物圆雕是青铜器中最多最常见的装饰物,但以某种动物的整体形象作为盖钮附着在青铜器上的并不多见,有这样一些代表性铜器:四川彭县出土的西周时期蟠龙兽面纹,器盖上盘踞着一只挺立的蟠龙,龙身盘曲在器盖边沿,与器盖融为一体;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王,器盖上立一鸟;山西天马出土的西周铜,器盖上立一鸟;山西曲沃出土的立鸟人足筒形器,上有圆雕弯喙、振翅欲飞的立鸟为钮。西周时期的个别动物尊的器盖上也出现了动物形盖钮,如:湖南湘潭出土的商代豕尊,器盖上立一凤鸟,西周季凤鸟尊,器盖上立一凤鸟,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貘尊,器盖上立一虎,如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牛尊,背开方口盖,盖上有一立虎作为器钮(虎完整,但虎的造型稍显拘谨,不是活灵活现的)。到了春秋战国时,独立的圆雕鸟兽形青铜器的艺术水平更为高超,手法清新写实,附饰式动物雕刻主要以透雕和浮雕居多。以某种动物的整体形象作为盖钮附着在青铜器上的主要有: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时期莲鹤方壶,壶盖上的鹤仰首展翅,翩翩欲飞;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的战国时期立鸟镶嵌几何纹壶,盖钮上立一鸿雁,壶盖边缘蹲踞三只雏鸟。 战国时期北方的内蒙古等地多有马具、车具等青铜器上雕刻圆雕动物的,动物种类是北方游牧地区常见的熊、鹿、羊、驴等。杨华在《商周青铜器中的圆雕动物造型》中总结说,青铜器中的动物造型不论是初期还是后期,神秘色彩与动物纹饰相比稍逊一筹,并未充分表现出人们对动物的崇拜心理,只是照实摹写动物原形或添加一些想象力,表现人们无法实现的愿望。




图10 显微镜下的贮贝器身纹饰细节
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作为盖钮的动物圆雕以鸟类为主要动物形象,虎次之。北方青铜器的动物圆雕以熊、鹿、羊为主。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牛作为云南畜牧业最为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之一,它的形象在青铜器中反复出现,往往装饰于兵器、农具、生活用具的把手上。牛也是贮贝器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国博藏立牛贮贝器器盖上焊铸的正是一只独立的牛,其前额宽广,巨大的角向上弯曲,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身姿矫健有力,四肢粗大,肌肉饱满结实,长尾,甚至连生殖器都做了刻画。
此时的贮贝器造型还处于稚拙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装饰风格。但是就牛的写实性来说,确实是古滇贮贝器独有的特色。古滇青铜贮贝器上的立牛圆雕饰物,经历了由少到多、由简洁至繁缛的变化过程,立牛装饰由一牛发展到三牛、五牛、七牛和八牛,但是量多而有序。牛在古代滇国是财富的象征,对其占有的数量直接体现了占有者社会地位的高低。这个立牛逐渐增多的过程,反映了古代滇国上层贵族对财富占有的贪欲,贮贝器也因此渐渐成为有财富象征意义的青铜礼器。
3.以人物为主要题材的立体装饰物
早期贮贝器的器盖上尚没有人的形象出现。到了西汉,以人物活动为主要题材的立体装饰物出现在贮贝器的器盖上,这是贮贝器艺术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古滇青铜贮贝器最有特色之处。人物活动涉及生产、生活、宗教祭祀等题材,大大丰富了贮贝器的表现力。
贮贝器器盖上的立体装饰的典型艺术特征有三。一是“一器一事件”的主题表达。从动物到人物的题材转变标志着贮贝器艺术前进了一大步,从单一人物到场面雕塑又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贮贝器器盖上的场面雕塑完全脱离了实用范畴,它所着重的是“主题表达”, 如狩猎、纺织、纳贡或祭祀、战争等人物活动的场面。纵观古滇青铜贮贝器可知,每一件贮贝器器盖上的焊铸物皆手工制作,一式一件,对手工艺技术要求非常高,不能量产,每一件器盖上所表现的内容都是独一无二的。
二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李艾东在《青铜时代的云南滇青铜器艺术》中说到,古滇青铜器区别于我国中原地区青铜造型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青铜器附饰雕塑的写实性。 小至托盘里的鱼,大至数十厘米的屋宇具皆比例恰当;人物神态自然鲜活,身居高位者的踌躇满志,普通人物的谨小慎微,呈现出超强写实的人性色彩。与束腰筒形贮贝器器盖上大量立牛造型的圆雕不同的是,铜鼓形贮贝器器盖上的立体焊铸物主要是构建各种人物活动的场面。比如纺织场面贮贝器,在直径24.5 厘米的器盖上,焊铸有人物18 个,鸡、犬各一只。人物均为女性,主要表现一个家庭的奴隶从事纺织生产的场面。其中坐于矮榻上的,为滇国的上层人物,比其他人高大,身上鎏金,正在监督纺织者。此人周围有侍女数人,有持布者,有执伞者,有捧盘奉食(鱼2 尾)者,有向心踞坐的妇女数人,正在用踞织机织布。纺织作坊设在露天,女奴们箕踞而织。贡纳场面贮贝器则生动地展示了来向滇王纳贡的臣服诸族,跟据研究,在这些族中,可以明显区分出“椎髻”的滇人和编发的昆明人,同为“椎髻”滇人,其梳髻的位置和服饰又大不相同。背物牵牛这组人物的深目高鼻皆清晰可见。
三是繁而不乱的布局能力。虽然涉及人物众多、布局密集但秩序分明,那些身居高位者,往往置身醒目位置上,有的还加以鎏金修饰,着重刻画出统领者的权威。其他各类人物或提篮系筐,或踞坐织布,或牵马执辔,均各有其事,各负其责,且众多人物的五官、发饰、衣着、体型等刻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以诅盟场面贮贝器为例,束腰筒形贮贝器的器盖上一般以表现立牛为主要内容,而表现人物的只有3 件,分别是10 人纺织场面贮贝器,鎏金骑士4 牛贮贝器,还有一件就是这件诅盟场面贮贝器。这件贮贝器的盖径仅32 厘米,但是在如此狭小的盖径上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 人(残缺者未计入),还能繁而不乱,在所有青铜器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器器盖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台上置一高凳,凳上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着16 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下有从事杂役者多人,景象繁忙。右后方立一木架,横梁上悬挂铜鼓和于,一男子各执一锤以击之。其后置大铜鼓两具,鼓间立铜柱,柱后木牌束缚一待刑的裸体男子和多个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4.贮贝器的平面装饰艺术
贮贝器上的平面纹饰从铸造工艺上来讲,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范铸法,即在制范时直接在内模刻好花纹、图案然后浇铸而成;二是线刻法,即在已经铸好的贮贝器器表上刻纹图案。 用线刻法有利于表达更为复杂细腻的内容。
据学者研究,青铜器线刻工艺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从分布范围来看,早期中原地区发现线刻青铜器物较多,汉代线刻青铜器则是多出土于南方,如广西、贵州、江西、江苏等地,线刻工艺也比较成熟,并逐步流行起来。古滇国青铜器虽然在时代上相对较晚,但是冶铸水平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失蜡法的运用,线刻工具的出现,使得云南古滇青铜器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500 年左右)浓缩了中原1000 多年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精华。青铜器上的线刻纹饰,之所以到了春秋晚期才出现(古滇青铜线刻是战国中期才出现),并非作画水平不能,乃是镂刻工具的制约使然。我们知道,青铜的硬度是5~6 度,钢的硬度是6~7 度,硬玉是7 ~ 8 度。铁的冶炼,在中原地区是始于春秋晚期,古滇是在战国中晚期,这和各自线刻纹饰青铜器的出现时间是基本吻合的。之所以线刻青铜器最早在江苏发现,也是和那时吴越制铁工艺相对发达分不开的。
中原地区青铜器的纹饰风格,以抽象的几何纹样与变形的动物纹样为特征,最为浓烈地体现在饕餮纹饰。饕餮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经工匠们想象、分解、变形、组合而成的。古滇青铜器的纹饰特征,更多体现在线刻工艺所描绘出的具体而生动的形象上。艺术风格是写实的、灵动的。布局上,注意疏密有致,富有韵律感。线刻纹饰的艺术表现手法与中国画的线描接近,注重线条造型,不讲究焦点透视。
线刻青铜器是古滇青铜文化高度发达后出现的新兴艺术形式,它作为古滇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和形式上也留下了该地区传统文化与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交流的印记。七牛虎耳贮贝器和贡纳场面贮贝器都出土于晋宁石寨山第13 号墓,该墓共出土贮贝器5 件,和出土了滇王金印的第6 号墓数量相同,但该墓随葬器物无论数量、规格都超过了第6 号的滇王墓,所以很多学者认为第13 号墓也是一代滇王之墓。 这两件贮贝器虽然器形不同,一是束腰筒形,一是鼓形,但是器身都是线刻纹饰。因为线条纤细,只有近距离才能欣赏,所以线刻图案常常作为一种背景,起到烘托、补充主题的作用,从这几件贮贝器镂刻的图案看,线条都自然流畅,很少有断断续续的停顿感,也没有修改痕迹,这对工匠的技术水平、艺术修养都有很高要求,凡是由线刻工艺装饰的贮贝器,都精美异常 (图10)。
七牛虎耳贮贝器的器盖上线刻有两只鸟,鸟喙巨大而向下弯曲,鸟头上有鼓包,尾翼张开似羽扇。这种鸟纹,仅在石寨山叠鼓形贮贝器和鼓形飞鸟贮贝器上出现过。易学钟分析认为这是犀鸟,生活在云南西部和南部雨林中 (图11)。
贡纳场面贮贝器圈足靠上一点的位置,线刻了一对龙,两两相对,长长的龙身呈S 形蜷曲,龙首似马头前伸较长,无角,耳的形状竖长,龙的两只前爪像青蛙一样伸在头的两侧。从龙的形象的变形可以看出,古滇地区有汉文化的传入,但是这种传入是缓慢的,加上古滇特色纹饰固有的强大生命力,所以中原的龙纹饰在传入的过程中,古滇工匠进行了符合自己认知对龙的想象与刻画,这种刻画难免会有些不同程度的变形。龙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中并不多见,其时代始于西汉早中期,且龙纹始终只出现在滇国贵族的墓葬中,数量稀少,可见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图12)。
由于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集地,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制作的;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从贮贝器的立体装饰和平面装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商周以来青铜器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如器物与形象结合、立体雕饰与平面纹饰结合等。骑士狩猎、纺织、贡纳等生动形象的情节更是一种新的因素的表征,是以往的青铜器中不曾见到的,人物面部表情、衣着、体型的细致刻画,场面结构的构思也超越以往的同类作品,这些都使我们对古滇青铜贮贝器的装饰艺术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以贮贝器为代表的滇国青铜器充实了云南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线索,这一地区在战国至西汉时代就已存在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而且滇国的青铜文化并不是封闭的,它博采各家之长,且又不断创新,有自己的浓郁而强烈的艺术风格。
三、贮贝器的功能与价值
古滇青铜贮贝器不仅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艺术欣赏价值,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们是研究古滇国青铜铸造历史及古滇国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
1.贮贝器的功能

图11 贮贝器身的鸟纹

图12 贮贝器身的龙纹

图13 贮贝器内贝币的残留痕迹
一般认为贮贝器的首要功能是贮贝(图13)。古滇国出土的这些海贝经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鉴定,其产地是印度西太平洋暖水区,包括印度、菲律宾等地。这些海贝大量地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而滇国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安宁太极山滇墓等)和平民墓中不见一枚海贝, 学者推测,滇国的海贝有可能是通过并不广泛也不普遍的贸易和纳贡的方式获得的。
海贝作为珍稀货币,使得它的贮藏物贮贝器成为财富的象征。但并非所有的贮贝器中都装有贝壳。根据墓葬年代分析,年代最为久远(战国中期至末期)的贮贝器是呈贡天子庙第33 号墓中出土的一件五牛贮贝器,但内中未见贝;年代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以前、其上限或可早到战国末期的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发掘出的4 件贮贝器分别出土于第17 号墓、第18 号墓、第21 号墓、第22 号墓中,这四座墓贮贝器旁边都伴随着铜伞盖、铜枕、海贝,有的如束腰筒形立牛贮贝器内有贝,有的如第18 号墓中的贮贝器内并没有贝,而是有铜鱼钩2 枚、木纺轮2 个。 石寨山前四次发掘的50 座古墓中有18 座出土有贮贝器(均是大墓),有17 座(均是大墓)出土有海贝,重400 多千克,约14.9 万余枚,皆未磨孔。数量如此众多的海贝,大部分都是成堆地置放于墓中,有学者推测,可能这些贝原来放在竹筒中,几千年后的今天,竹筒腐朽后,就只剩海贝堆放于地上。 而盛放过贝的器物除了贮贝器之外,铜鼓、铜、铜洗、竹筒等也充当过盛器。此种现象提示我们,贮贝器初始的功能也许与贮贝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最开始的功能也许是陈设,或作容器,或作为祭祀品。
但是贮贝器作为财富象征的礼器这种功能却是无可置疑的,这种象征首先体现在器盖上的立体圆雕动物(牛、虎、鹿),牛作为古滇国财富的象征,其圆雕形象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戈、铜钺、铜戚、狼牙棒等青铜兵器上,铜壶、铜尊、铜杯、铜枕、铜案等青铜生活用具上反复出现。42 件贮贝器中以牛为主体雕塑的比例约为50%,牛的数量上具有由少变多的趋势, 石寨山虎耳细腰筒形贮贝器的器盖上雕塑的牛的数量多达8只,这个由少变多的过程也是财富象征意义逐渐加强的过程。如果说早期立牛圆雕是作为盖钮出现的,那么随着西汉时期人物圆雕在贮贝器器盖上的出现及各类复杂场景的逼真塑造,贮贝器器盖上的盖钮则完全脱离了实用范畴,贮贝器器盖的内容注重以写实性的手法雕刻出滇国生产、生活的重大事件,如前所述的祭祀、纺织、贡纳,还有畜牧、狩猎、播种等。滇国贵族把贮贝器当成夸耀自己成就与荣耀的器物,这是权力植入的重要过程,所以贮贝器在西汉早中期的滇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
李伟卿认为,贮贝器的兴盛、衰落,和滇王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联系。贮贝器的存在大约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它的存在与消失和滇国的命运密不可分。从政治上来分析,滇国是我国西南边疆古代民族建立的古王国,在汉武帝元丰二年(公元前109)之前,“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的滇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处于奴隶制阶段的氏族社会。元丰二年,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归附,“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在这之后,郡县制逐渐巩固,滇王的权势实际上被大大削弱了。到东汉中期,滇国完全销声匿迹了,贮贝器也从墓葬中消失。从经济上来分析,在西汉时期滇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冶铁技术,铁器实用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汉武帝时期开始了自制铁器的历史。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贮贝器也最终消亡。
2.贮贝器的价值
如同中原地区一样,商周时期铭文的产生使青铜器变成一种可以用来叙事的文本承载物,而古滇国西汉时期的贮贝器不仅也成为拥有着展示荣耀与成就的物证,同时也承担了记录历史的功能,被称为“无声的史书”。
比如诅盟场面贮贝器从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表现的是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此场景可以和典籍相对照,《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论当时的南中习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又《建宁郡·味县》条下云:“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都说明诅盟为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纺织场面贮贝器器盖上焊铸的踞织机,也称腰机,是斜织机(竖机)出现之前的一种较简单的织布工具,主要由经轴、分经杆、布轴等部件组成。战国至西汉时期,我国内地已普遍使用有机架的斜织机,踞织机的使用已经成为历史。云南地区的情况与内地不同,滇人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纺织工具和青铜器上的图像,都说明滇人的纺织技术比较落后。贡纳场面贮贝器为研究汉代滇人的手工艺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贡纳场面贮贝器还生动地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这对滇王来说是件十分可夸耀之事,故将其雕铸在十分精致的贮贝器上。纳贡者有滇人和昆明人,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滇西地区还有“身毒之民”和“越人”侨居,表明古代云南地区居民成分是相当复杂的。所以说,贮贝器为研究古滇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参考资料。
另外,贮贝器虽然是古滇国工匠制作的,但是器物所表现的内容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投影,夸富已经满足不了统治者欲望,他们还要炫耀、夸张自己的功绩。古滇国没有文字,不能像西周贵族一样每逢立下战功、得到赏赐后铸一件有铭文记载青铜器以作纪念,贮贝器上的场面雕塑无疑成了最好的载体。可以说青铜器上的每个雕塑场面都等同于西周铜器上的一篇洋洋百字的铭文。 于是贮贝器成为了后人了解古滇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的一部“无声史书”。
贮贝器虽然随着滇王权力的消失而销声匿迹了,但它的影响也许还没有结束,曾经被贮贝器取代过“国之重器”地位的石寨山铜鼓,作为一种发展成熟的器型,在滇国政权没落后仍能向外传播,播迁到滇、桂边境及两广一带,作为一种礼乐器,铜鼓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并延续了贮贝器的部分“史书职能”。包括现今贵州南部的开化鼓、云南广南县的广南鼓、广西西林县的普陀鼓、广西贵港出土的罗泊湾鼓,都属于石寨山型的代表性铜鼓。 东汉及其以后的铜鼓蛙饰、人骑、牛撬、立鸟,也是贮贝器立体饰物的“萎缩形态”,另外贮贝器自身所特有的平面装饰艺术也渗透到铜鼓的纹饰之中,汉代两广地区的铜鼓,其主晕上反映礼俗活动的“绘风图案”便是平面化的场面铸像。 作为财富、权力、政治地位象征的贮贝器消失了,但是作为古滇青铜文化代表的贮贝器的艺术生命力也许并未完全消失。
四、结语
古滇国青铜贮贝器有着浓厚的西南少数民族特点,同时也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贮贝器器身的铸造使用的是范模铸造法,器盖上的立体装饰物以及虎耳束腰形贮贝器腰线上的虎耳、兽足等,采用失蜡法单个铸成后再接铸到器身上,同时器物表面线刻技术的发展是古滇青铜文化高度发达后出现的新兴艺术形式,说明古滇国的青铜文化并不是封闭的,它博采各家之长,且又不断创新。古滇国青铜装饰多以写实的场景描述,“一器一事”的主题表达,其中包括祭祀、战争、农耕、纺织、乐舞、家畜驯养等各方面内容。在文字欠缺的古滇国时代,每一件精美的青铜贮贝器都记录了滇国的人文历史。贮贝器是古滇国特有的青铜器,功能上是贮藏海贝的容器,但更是古滇国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作为“国之重器”,他与铜鼓一起铸就了西汉时期古滇国的青铜文明,是古滇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
注释:
③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 第4 期。
④佟伟华《云南石寨山文化贮贝器研究》,《文物》1999 第9 期。
⑧肖明华《论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考古》2004 年第1 期。
⑨张增祺《晋宁石寨山》,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