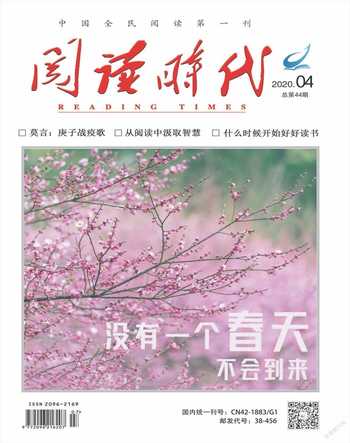文学与瘟疫
戴锦华
14世纪中叶,一场鼠疫的传播席卷了整个欧洲。这场持续了近七年的大瘟疫,夺去了2500万条生命,如同欧洲神话中身着带兜帽黑披风的死神,持续收割了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浩劫,作为欧洲现代史、也是世界现代史的序曲之一,为将临未临的全球化时代创造了一个黑色荒诞版的寓言和隐喻。
然而,文艺的流行与蔓延——经常是跨国蔓延,真正成为文学艺术普遍使用的被述故事、社会寓言或世界隐喻,却是20世纪的、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事实。究其因,不仅由于1918—1919年间的西班牙流感感染了全球10亿之众,造成了2500万到4000万人的死亡,更在于令其爆发、全球播散的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
20世纪前半叶,连续两场世界大战及继发的冷战中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威慑,频频牵动着欧美基督教文化中的末日情结,同时造就种种关于瘟疫时节寓言性或哲思性的书写。至少三位书写过瘟疫故事的作家先后登录诺贝尔奖“榜单”:加缪和他的《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也译作《爱在瘟疫蔓延时》)、萨拉马戈和他的《失明症漫游记》(也译作《盲》)。
随着冷战终结,20世纪的记忆在多重遗忘的政治间淡去,则是瘟疫作为形而下的全球事实的一再“上演”:先是艾滋病显影了曾由动物携带的病毒感染人类的威胁,继而是禽流感、口蹄疫造成一次次冲击,2003年SARS的爆發……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瘟疫作为灾难片类型中灾难之一种的份量。
然而,一个渐趋明显的变化已然发生。
20世纪后半叶,以瘟疫为主题的灾难片通常被设定为某种人祸:可怖的病毒来自某服务于生物战目的的军方实验室或大医药公司为牟取暴利的非法行径。影片中的孤胆/个人英雄(们)为了求生,必须以微末的血肉之躯对抗权力机器。在灾难成为人性恶的大曝光的背景上,同样为一己私欲而奔逃的主角,则因此获得了某个展露其利他、人性光辉的时刻。一如其筑型之作《卡桑德拉大桥》。这一灾难片的分支也就因此携带了特定的社会批判(当然也是抚慰)的功能。
而进入21世纪,此类型分支的先在设定,却大多转化为未知病毒、无名侵袭因而只能称其为不可抗力或天灾。因此,故事除了勾勒专业人士:前线医护、病毒、病理、流行病学家、世卫组织专家的职业伦理高度,便只能如日本ACGN“世界系”般地,将人类浩劫用作爱情故事的底景。其中,间或引入生态灾难的主题:人类的无穷开发和消费欲望,如何将密林深处的动物驱入了人类居处。但那与其说是文明反思的启动,不如说更多是举轻若重的叙事噱头,与其说预警,不如说是做诚恳状的犬儒,或无力感。
人们说,我们——人类社会一定能渡过这场灾难。灾难过后,一切将有所不同。什么将有所不同?为病毒所断裂、崩解的全球化链条及其灾难的修复?还是对全球化的追问和反思?是否可能由此开始,有所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想象路径,我们——你与我,人与人的连接,社会与世界的组织与运行方向?
我们亲历灾难,能从中学到点儿什么?
(源自“北京大学图书馆”)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