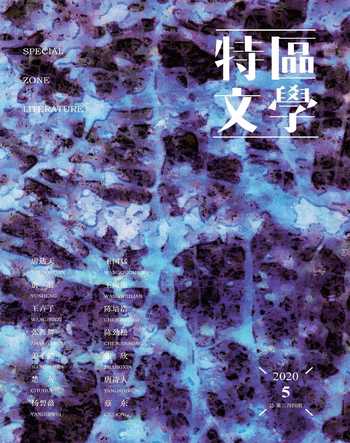塑造广州城市文学新形象
张欣 唐诗人
唐诗人:广州是“大湾区”的主要城市之一,广州的城市文学也可以算是大湾区城市文学的关键力量所在。要谈广州的城市文学,肯定绕不过张老师您,所以能采访到您是一件很难得也很有意义的事。首先我特别想请张老师从自己的创作经历,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创作,谈谈自己为何走向了都市文学写作?那个时候的城市文学是怎么一种状况?
张欣:城市文学的起源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尤其对于今天的城市文学研究热而言。但对于我这样的一路走过来的人而言,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我不是学者,没有对这些背景性的东西做专业的分析。我个人的感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对文学的热爱是一个历史时机。我们遇上了那个时机。那时候还没改革开放,刚打倒“四人帮”。那时候的氛围,跟今天这种文学这么边缘、这么少人关注的情况比较起来的话,最重要的差异其实读者问题。很多人喜欢回忆八十年代,但我对那个年代没什么特殊的感情,也没在任何场合谈过那个时代。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所谓文学热、文化热,不仅仅源于作家的热情,更主要的还是读者,是八十年代的读者赋予了那个时代以特别的文学土壤和文化节奏。那个时候看书的人特别多,刚结束“文革”,大家都很贫乏,都对知识充满了热情和向往。我感觉很少人从读者层面去谈八十年代,基本都是谈那时候的作家多么厉害,说作家应者如云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作家是一面,读者是更关键的一面。那时候大家都谈文学,就像今天大家都谈钱一样。你若不懂文学,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会觉得你什么都不懂。
在八十年代,我们这种都市文学写作,给人很飘的感觉。尤其跟乡村文学比较起来,肯定没有那么厚重。我们的文学观念里,历来都看重历史厚重感,如果没有深厚的底子,容易显得特别轻。那时候我们写都市文学,总是被人认为“写的什么鬼东西”。但我觉得,任何东西一开始都是轻的,都需要开始,然后经历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慢慢变得厚重。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不缺写城市的作家,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城市文学,全是农村的。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甚至一直生活在农村,偶尔去城市一趟,然后就写城市,场景虽然变了,但观念、视野什么的还是农村的,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城市文学。
说回八十年代写都市文学感觉“轻”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写都市,根本没有什么可借鉴的资源。但相对而言,生活在广州的作者其实会更好一点,因为离港澳近,容易受到港澳台文化的影响。八十年代,台湾和香港已经有了真正的城市文学。从地理上来讲,广州虽然不像北京、上海那样是文化中心,没有特别清晰的文化历史特征。但我们这样比较广州、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所依据的、参照的指标是否合理?这本身也需要我们去反思。比如放弃那种历史厚重感的东西,从现代都市的观念层面来理解的话,广州这座城市的现代观念还是很突出的。我觉得都市文学的核心就是观念问题。从观念来看,广州其实是有优势的。我们很多时候拍广州,一拍就是城中村什么的,非常潮湿,永远在下雨,你去拍高楼大厦什么的,就感觉很奇怪,它不是一个以繁华而引人注目的城市。但是从观念上来看,广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广州离香港近,它很容易被香港那种文化所感染。八九十年代,广州的电视收音机什么的,可以接受港澳地区的信号,比如收听到邓丽君的歌曲、看到香港的凤凰卫视等等电视节目。通过这些渠道,一些很城市很现代的文化元素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年头信息少,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电视上的那些东西很容易被我们接受。那时候生活在广州,比起其它内地城市而言,其实很容易找到城市的感觉的。因为这种地理上的便利性,来自港澳台的城市的、现代的流行文化、都市生活元素,对于塑造广州人的城市感觉、城市观念而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唐诗人:张老师您说的广州离港澳近,这是地理层面最直接的关联性。地理上的靠近,对于今天而言可能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言,地理上的相近所能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之前我跟陈崇正、陈培浩他们聊天,也提到过这种影响。他们小时候的记忆都是看凤凰台、是听港台歌曲,是看很多都市题材的电视剧等等。这些文化元素对于我们这种内地小县城的人而言是不太可能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确实把这个因素理解成促成广州城市文学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您刚才说到城市文学的观念问题,可以再谈谈到底是什么样的观念吗?
张欣:港台这种城市文化、流行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它不一定是直接的改变,更多时候是慢慢渗透你。有一次我们做一个读书活动,有一个小年轻给我们的留言里写了一句话,我挺感慨的,她说的是:“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因为它会肯定每一个人的努力。”我觉得这种商业社会的逻辑,很早就灌输给了广州的市民。想一想八十年代末香港的电影《富贵逼人》《富贵再逼人》《富贵再三逼人》,三个电影,非常直接,直接就是要富贵要发达。电影不断地强调富贵、发达,它这种直接的对利益、对钱财的看重,很直白。这种文化对于那年代的我们而言,是一种直接的冲击。很长一段时间,我們是“捡了金子也不笑”的,人家那是直接表达、毫无忌讳。在这种新的关于生活关于财富的看法的对比之下,你就会对人性、对我们曾经信仰的价值观会有一种反观。这种东西跟当年王朔那种直接的“反崇高”是完全不一样的。王朔是我们谈文学史时绕不过去的人,他是直接把我们信仰的东西打碎给你看。我们一直以来太喜欢那种崇高化的、歌颂式的、正面的东西,当接受到那种港台过来的世俗文化、商业文化的时候,这是一种直接在日常生活层面就会感受到的价值观颠覆,不同于王朔那种知识分子意义上的解构。
城市这种功利化、商业化的情况,其实也可以是一种很可贵的环境。这种对利益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是都市文学创作的基本处境。商业、功利是都市文学观念的基本面,它承认利益,承认我们爱钱,承认我们有欲望,这是一个基础。如果我们还继续假、继续装,而现实生活又需要钱,那可能就导致了严重的虚伪写作了。所以,我觉得城市文学可贵的一面就是要去面对人的赤裸裸的欲望,要去面对人在欲望面前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性问题。我觉得这才是都市文学的本质,不是什么海鲜、别墅、大沙发、酒吧什么的,这些乡下暴发户也可以有。所以对于都市文学,最重要的还是观念上的突破。以前很多人不觉得有钱意味着什么,老是觉得用钱来解决问题是不好的,是俗的。但是其实用钱买东西、解决问题是最清白的,有钱获得服务也是最正常的。相反,那种通过权力来获得利益才是最奇怪的。我们的文化里,普遍是崇拜权力,权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很多人也从不觉得这种权力逻辑有什么问题。商业社会就是把很多传统的观念给打破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自然要去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包括把包裹在都市身上的那些温柔面纱给揭开,直接去面对都市社会的欲望问题。
唐诗人:确实如此,所谓都市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欲望社会。尤其对于现代城市而言,它就是人的欲望不断膨胀的产物。现代城市就像一个人一样。人的欲望是无法得到彻底满足的,一个欲望会生产另一个欲望。城市也是,有一种不可停滞的发展欲望。现代化、城市化,其实是不间断地发展,不断地从其它地方吸纳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资源进来,满足它的运转。而现代人之所以憧憬城市生活,当然也是个体生活欲望的选择,只不过这些欲望有很多种表现方式而已。所以相对于乡土社会那种追求自给自足、向往超稳定的生活秩序而言,城市是代表着欲望、意味着变化和发展的。如此而言,所谓城市文学,如果回避“欲望”这个根本性问题,还继续以往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宣教式写作,把“欲望”简单化、标签化,那就必然是一种虚伪的写作。“虚伪”是文学创作最忌讳的问题,它从精神根基上就走向了文学的反面。您的小说,可以说都是在直面都市人的欲望,写都市各行各业的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欲望。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之初,都市人的欲望更多也表现为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对于生活欲望,广州这座城市表现出来的状况似乎也有它的独特性,在我们的印象中,广州是务实的。很多人对务实的理解,似乎就是指向物质生活层面的务实,不太谈精神,只求日常生活层面的实在感、愉悦感,您写广州这么多年了,您怎么理解这种“务实”?或者说从文学视角来看,您怎么理解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
张欣:广州这个地方不会因为你是作家就把你看得多崇高,可能还会嘀咕说:“诶……穷人呗。”这不像其它很多地方,把作家看得那么高高在上。当然广州人也不会直接贬损你,也会给你留点面子。这种城市市民的态度,给作家创作提供的语境其实是很正常、甚至很理想的。这就造成了作家必须持续去写,而且不能灌水,让你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跟大家一样的人。这种环境塑造的作家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的视角是很好的,不至于说形成一种俯视他人的视角,不会在生活中对他人随意评判,不会提供各种“应该如何”。广州人这种价值观,其实是一种生活哲学,它可以消解很多东西,包括消解生活中的困难。广州人对于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会觉得很正常,没什么困难和意外是不可接受的。像广州人做生意,广州人做生意的最多了,他们可以把做生意的起伏波动看得很开,觉得投资失败成功都很正常,没什么是必然的、应该的。你怎么能说你做生意成功就必然、就应该的?这不可能的嘛。我就觉得这种处理生活困难的心态特别感动我。包括这种视角问题,每个行业的人看待他人的生活都是平视的,是跟大家一样的,谁也没资格看不起别人,你能看不起一个卖肉的吗?人家戴的金戒指还比你更大更贵呢。我觉得这是广州这座城市让我感到写作会比较轻松的一个理由。我去构思写作的时候,不会去想什么要写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如何解构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小说就是解闷、就是讲故事啊。当然这说起来很不好听,我们也有很多小说是宏大叙事、是写主流事件。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写很多主题、题材,但我们写作的姿态不能端着,不能因为自己写什么就把自己当做什么,不能因为自己写宏大主题就把自己崇高化了。你越把自己当回事往往越写不好,写出来的东西越没有人看。
唐诗人:您谈到这种“消解”的文化和写作的姿态问题,我觉得这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广州人、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特征,当然这是从文学视角来理解的。消解的文化,这其实就是广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为都市人,作为以做生意来维持生活、来完成富贵发达的生活理想的广州人来说,失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失败和发达,在这里是人人都有可能、是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似乎也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广州人的世界观。他不会对某个行业特别地推崇。你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状态。这种文化也是我尤其喜欢广州的原因,就是生活在这里我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我出去办事所遇到的人,多数也是在安分地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但很多人也说,这种太务实的文化对于文学、对于作家而言其实是一种很不理想的氛围,因为文学还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需要读者来支持,需要民众的兴趣和热情。没有这种文化氛围,很多作家就很难写下去。我听过一些作家对广州的评价,就说广州这个城市是扼杀文学的,您好像从不会这么看待广州。您可以说说这个问题吗?
张欣:我没有觉得广州不适合写作。可能很多人不习惯,因为广州确实“文人气”比较淡。我觉得有的文人还是有一种“端着”的状态,就是觉得自己是写作的、搞文学的就跟别的职业不一样。但我前面也说,广州这种城市可以消解那么大的痛苦,可以消解那么多的失败,那它消解一个作家岂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人过这边来,也就那么回事。就像当年广州人看刘晓庆,他们不会觉得看一下这个名人又会怎么样,不会疯了似的去骚扰你。当然也有很多作家来到广州确实没有找到感觉,因为毕竟迁移了,离开了自己的创作根据地。但我还是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作家的身份感,要把自己的架子降下来,要把自己与生活与这个城市的关系处理好,不要有“隔”,有“隔”的话你肯定就写不好。
文学这个东西,它的读者从最终意义上来说不是看作家名气才看的。一个作家名气再大,读者看不下去也不会多看。我为什么对广州这种“务实”的文化很认同,可能有我自己的原因。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我十五岁就当兵了,在第一线工作很多年,都是实实在在地该干嘛就干嘛。汪洋就说“广东人的优点是务实,缺点是太务实”。我就是那种太务实的。我就觉得,我们得对生活有好奇心,对世俗的日常生活有兴趣,这是作家的必备能力。比如说我们要对“吃”有研究,要懂得生活,但我们的作家全都喜欢讲鸡汤或者讲什么人生大道理,或者是拿自己的生活经验不断翻炒,这样的作品肯定是沒人读。作为一个职业的小说家,我平时最感兴趣的就是日常生活。作家对日常生活感兴趣,才会沉入到生活里面去,写出来的作品才不至于浮在生活表面。就比如说写都市生活,要深入到都市的内部去,去了解各种各样的都市人,每个都市人都不一样的。都是富豪,但很多富豪未必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财大气粗,底层人物也不一定是没文化没品位。
唐诗人:不能沉入到真实生活里面去,这确实是当前很多作家无法写好城市的最大问题。我个人以为,很多作家一写乡村就很有感觉,这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经验是乡土世界的,有深刻的记忆和感受。而对于城市,虽然可能也生活在城市很多年了,但内心估计永远都与城市有“隔阂”,总是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是漂泊在城市的。这种“漂”的状态,导致很多人写出来的城市题材作品也是“漂”着的。如今城市文学很火,很多青年作家都热衷于写城市了,我也看过很多,但大多数作品都有您说的这样一种“隔阂感”,就是感觉他们笔下的城市生活,写来写去都是写自己的生活。因为不能深入到城市、不能进入到这个城市的其他人的生活中去,但他们又必须写下去,每个作品也必须有所差异,我们能看到很多作家可能写了很多,但都只是在文字上、在语言感觉和叙述技巧上有所突破,在人物的丰富程度,以及对生活、对城市的理解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我认为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没能深入到自己所要书写的城市生活里面去,没有真正去观察、感知和研究自己要写的“他人的生活”。
城市不像乡村,乡村很多事情是集体完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城市看似有很多人、生活很拥挤,城市也意味着变动不居,但如今科技如此发达,城市人不用接触其他人就可以生活下去。城市提供的便利永远是表面的,便利的生活背后有很多问题往往是特别不容易。这“不容易”的一面就是需要我们作家去挖掘的,但我们的作家很容易就把这些“不容易”对接上西方现代文学所强调的那些孤独症之类的情绪,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看到的青年作家写的城市,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或者广州、深圳,包括香港、澳门什么的,都大同小异。这些问题都是作家偷懒的结果,是作家不愿或不能深入到城市内部、深入到他人内心生活中去导致的。我系统地阅读了您这几十年来的作品之后,我就特别想向一些青年作家推荐您的作品,因为您写很多城市市民的生活,人物形象基本上都不同,但几乎都能把这些人物塑造得很丰满很地道,这一定是下工夫了、有专门的研究之后才能写出来的。
还有一点您一直强调的读者问题,包括前面你谈及八十年代的文學氛围的时候,都很突出读者。我们今天很多作家都不重视读者,都强调是为自己的内心写作,不会把读者能不能理解作为一回事,但从您的作品到您的创作谈之类的文字,包括前面您说的那些,似乎特别在意读者能不能接受,读者在您心目中应该是很重要的,您可以谈读者问题吗?
张欣:我是觉得写作者和读者是很平等的,我从来不觉得作者有什么高人一等。当然今天作家都会说我只为自己的内心写作,不为市场,不为读者,这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答案。但我很多时候其实并不这么认为。我没什么理论,也不会跟什么人辩论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书也好,影视剧也好,打了标价,那首先就是商品,是商品就必须考虑别人能不能、会不会接受。尤其在广州,这不是首都也不是魔都,这是商都,它是最早教会我们市场交换规律的。有很多未婚女性与我聊什么婚姻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说你想要对方拥有什么,那你得拿出一些品质来进行交换啊。文学创作也是,你必须考虑自己的作品好不好看,包括对于读者而言能获得什么。你如果写得特别晦涩,自己都看不下去,还想别人看下去?我一直被别人说成是那种比较通俗的作家,就因为我的作品好读嘛。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通俗的东西就肯定都放不上台面。后来我看到一个作家,好像是余华,他谈创作的时候说他一直不会心理描写,不知道什么是心理描写,但后来发现实际上并没有心理描写这回事。比如说写一个动作细节,并没有刻意进行心理描写,却可以把心理内容表现出来。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你在听我说话的时候,突然被杯子里的水烫了一下,这个动作就可以说明你全部精力都在听我讲话这个心理状况啊。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心理描写”这个词,或者说,不需要这个词也不会影响我们写作。同样的道理,通俗与不通俗也是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通俗”的东西就不好、就不深刻,通俗是什么意思?《金瓶梅》还不通俗吗?你能说人家不深刻吗?我们的作家自己就没想明白自己要干嘛,一会儿别人说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一会儿人家说要那么写就那么写。我写作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我自己是一个读者,好不好看很重要,如果我自己都感动不了我自己,我怎么感动别人?
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比较欣赏的作家、学者,他们会觉得我的写作是比较从容的,写得比较克制。我觉得城市文学就是要克制的,不能老是夸张化。从容和克制是城市文学创作很需要的品质,这种品质目前似乎只存在于那些体制外的作家身上。比如一些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家,很多就有着从容的叙事品质。真正的体制外作家,基本是靠读者真正的购买和阅读才存在着。这些作家会尊重读者,真正把故事讲好,让读者爱看,至于别的,不会考虑那么多。当然,现在的写作,很多很难读下去的作品,不一定是不好,也有可能很好,但是它跟读者难以形成一种粘合度。读者不真正阅读,就肯定跟你有隔阂。读者可能知道一个作家很有名,但若他看不下去,就不会对你有真正的感情,你的作品也不会真正对读者产生影响。作家写作,让读者会读下去是一个基本的品质要求,没有阅读,就没有文学。让读者愿意去看你写了什么这最为重要,别的那些语言、品位之类的,也很重要,但比起读者来说还是次要的。对于读者,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在我写作生涯里,对读者是很尊重的。因为对读者尊重,作家才会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尊重。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人物特别扁平,看上去特别傻,读者肯定会发现的。读者是最不能戏弄的,你的人物很假,读者就肯定能看出来,肯定就不会有什么共鸣。别把读者想得那么简单,他们不是傻子。
唐诗人:不能把读者简单化,这就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剧,总是觉得很多导演把观众傻子化。有些导演不好好讲故事,生怕观众不能明白自己要说什么,总是要在作品中什么都直接告诉你,什么都为你考虑清楚,连这个剧到底要讲什么也要找个地方直接告诉你。这种作品看得想骂人。我觉得小说也是这样,你把读者看成傻子,简单拼凑出一个故事,怎么可能感动人?还有就是你根本不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就一个人在那里做梦一样毫无逻辑地讲述,如此读者肯定不会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创作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出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简单拼凑,一个是胡言乱语。简单化的故事一大堆,毫无逻辑故作高深的也是一大片,这两种写作已经把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给“惹恼”了。今天很多作家抱怨说没有读者,我觉得如果抱怨这个问题的作家自己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写作。我前面写过一个小文章,就谈到现在的小说不考虑读者接受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最早的“说体”文,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接受者听进去,后来的话本什么的,也是要想尽办法把听众吸引住,古代的小说也是,让人读下去是个基本的品质,但是我们今天的小说创作根本就不考虑读者了。现在作家很懂文艺理论,都会说自己写给理想读者,但这几乎都是自我欺骗。很多作家所谓的理想读者,往往就是作者自己。自娱自乐,这是当下纯文学创作最可悲的状态。从这方面来看,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作家来到广州之后难以写下去了,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在这个城市找到自己的读者。很多作家不重视读者,自然就找不到自己的读者。我觉得,这肯定是广州城市文学,或者说广州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所需要直面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您有很多读者,您自己也一直在做一些面向大众的文学阅读分享活动,您可以根据您的读者,包括您做的读书活动所接触到的读者情况,来谈谈广州的读者情况吗?我觉得从大众层面、普通读者层面来看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气息或者文学氛围,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维度。
张欣:我虽然做读书会,但我并不认为读书需要什么“会”。读书就是一个人在家的生活选择,但读书会可以是当代城市人的一个气阀。城市人都比较孤独,很多人需要有一个表达自我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表达一些东西。读书会就可以是一个这样的平台,所以做读书会确实能看到很多普通读者的阅读状况。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觉得真的是经济越发达,人就越需要精神的东西。我们现在有各种机器,洗衣服什么的都不需要自己动手了,那你留下那么多时间干啥呢?有闲暇,才会有精神生活;有太多的閑暇,才会幻灭、会有虚无感,这时候就特别需要文学之类的东西来调剂、来填补。以前是拼命干活,要不然没饭吃,活不下去,当然就没有什么空间来谈精神生活。我记得我们当年在海南岛开会,大家讨论到底是贫穷还是富裕才需要文学。那时候政策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就开玩笑说等着那些人富起来了之后,然后就会彷徨、会虚无,就会觉得人生很无聊,然后我们这些作家就站出来,去拯救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今天看来,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很多家庭好像是发达了,现在的科技也很先进,但那些最基本的问题并没解决。比如人人都会有所思考的人生价值和精神情感问题,包括一些人性问题,这些都属于精神层面的内容。
就读者而言,广州的读者情况其实挺不理想的。我做读书会,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失望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有读者来,不管多少,都很难得。每个来参加读书会的都不容易,他们必须有这份读书的心。在这么忙的生活里、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挤出时间来参加活动,还要学习、要看书,这很不容易。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广州还是有真正的文学读者的,这些读者的文学分辨能力很强。我们做活动读的很多书都是经典,每次的读者都不少,而且他们都是冲着这些经典来的,是真的来学习的,这是一个让我们坚持继续做下去的很重要的理由。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我很想说一说,这不一定跟我们的主题相关。我觉得读书会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搭一个平台给读者交朋友。曾经有一对女孩,给我印象很深刻,她们手拉着手,看上去非常要好。她们中的一个告诉我说她们就是在读书会上认识的,她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能交心的朋友。这种最世俗的收获,往往最让我开心。一个城市有庞大的人群,但我们的读书会可以聚焦一批有共同兴趣的人。来参加读书会的人基本就是有共同兴趣的,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平台上认识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潜在的好朋友。读书会有它的平台功能、服务功能,我们不要忽视这些东西,不要觉得这跟我们做读书会的目的背道而驰。而且,我们找嘉宾来讲书,我是要求嘉宾能讲多深就讲多深。很多时候,我可以感知到那些读者、听众其实是很认真地在听,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文化大餐,是很有价值的“课堂”。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觉得广州还是有很好的文学读者的,尤其广州的年轻读者很值得期待,很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开掘。
唐诗人:确实,我觉得读者肯定是有的,只是我们有没有耐心去发掘和去等待。广州这么多人,喜欢读书的其实非常多,我看这些年的图书销售量排行,广州一直是排在前列的。有人说广州没有文学氛围,做文学分享活动往往没听众。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那么简单,这跟前面我们谈到的广州人不崇拜什么名人有关系,但更大的原因还是我们做活动的方式有问题。我们面对读者的活动,不能高高在上,而要有一种“服务”意识。做读书活动,不要把这个活动的目的想得那么纯粹、单一,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平台、一个契机的价值。这个平台让人可以表达自己,可以让人找到朋友,可以让人获得一些知识。这些很具体的“目的”,可能很不专业、很不上档次,但却是广州读者愿意参与的最有诱惑力的原因。广州做文学活动,不能全讲虚的,还是要有一些“干货”。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而是生活在广州的文化人要去认知、去理解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调整我们的活动方式、活动内容。我们做活动,是在服务,这不是高高在上的“宣教”。
就如何吸引读者来讲,您的作品有通俗化的特征,更明确来讲,是叙事上采用了很多类型叙事的东西,像侦探叙事结构,包括主题上的商战、官场、爱情等等,这些都是很容易俘获读者的元素。就征用类型叙事这层面来说,这些年也特别流行一种科幻类型的叙事,您对现在的科技叙事、科幻写作有什么想法吗?
张欣:侦探叙事、爱情故事这些都是很古老的技艺和主题,我不觉得这跟我们所谓的纯文学有什么不搭的。至于科幻、科技,这确实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实。我们所接触的很多东西都离不开科技,所以科幻写作什么的都很值得去探索。但有时候我又倒过来想,其实文学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寻找差异性问题。文学是一个古老的技艺,它是一个手工业性质的技艺。我一直是比较写实的,对于文学流派什么的,会保持一点距离。就像我们当年流行什么意识流、魔幻现实、黑色幽默之类的,好像写作就是排队一样要排上去。后来我就觉得文学流派都不重要,文学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文学最根本的还是心灵的碰撞。我现在还在看汪曾祺,每次看都觉得特别厉害,那真是好东西。这么多年过去了,作品这么经看,人物跃然纸上。文学这个东西,有一些最古老的技艺、经典的东西是不能扔弃的。今天科技这么发达,但计算机还是没办法解决人的情感问题。所以我认为,不管什么流派,或者什么叙事类型,归根结底还是回归到常识、回归到原始的文本经验。
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今天写作,一个方面是要超越传统的那种老套的、陈腐的叙事方式,比如说那种直白的教育、教化别人的写作。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变成怎么样了,得明白现在年轻人走到哪个地步了,必须用一种现代人愿意接受的方式去书写,这是与时俱进的一面。但反过来,另一方面是我们也需要相信写作的本质还是不会变的,文学要注重人的灵魂,要书写人的心灵和情感问题。我们之所以还会去看几百年前的东西,还会觉得他们写得那么好,这就说明那些作品经过了时代的考验,也说明文学当中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这些也是科技改变不了的。今天的写作,可能科技含量都很高了,但文学终究还是侧重于写那些玩科技的“人”。高科技对文学的影响,我觉得很有限。广州有机器人炒菜、送餐,这些其实都很容易达到,但对于人的情感问题、现代科技人的心灵问题,才是文学要去挖掘的。
唐诗人:文学还是人心的学问,离开人就不会有文学。最后我们聊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也是谈广州城市文学都必然会触及的问题。我们看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北京、上海、香港什么的,他们的城市文学特征还是很明确的,去找这些城市的文学代表作和经典形象都很容易找到。但是对于广州而言,好像总是难以拿出一个形象出来说这是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学典型。甚至我们找广州城市文学代表性作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太明确,不像上海那样一说就可以想到王安忆、金宇澄等等。当然我们很明确,您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但我系统地读完您的小说之后,有一个印象就是,您确实一直在写广州、写广州的市民,人物形象特别丰富,各行各业的广州故事。从总体上来看,您是当之无愧的广州城市文学代表性作家,但就是没办法找到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来说明这是广州这种城市的文学典型。这就导致了外界对广州城市文学的模糊认知。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张欣:塑造代表性形象,其实无非就是写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或者就是小人物身上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城市。我觉得我们对广州的文学形象需要有新的认知。我记得有一次开会,大家说到广州音乐问题,陈小奇就觉得我们不能老是拿出农耕时代的作品来代表广东音乐,需要有一些新的作品、新的标准。我们现在对城市文学的认知,往往也是拿《三家巷》《虾球传》《外来媳妇本地郎》之类作品来作为标准,其实这很表象,现在再这样写,肯定不会有什么反响。包括很多作家也写东山少爷、西关小姐什么的,包括十三行,也无数的人在写,但是写出来都不理想。我就觉得,文学这个东西,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不是想完成就能完成的。我这段时间也在做一些准备,想写一个更广州的作品。但是写广州、广东的东西真的很有难度的。广州的东西,你接触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感觉很有深挖下去的潜力,但是你要深入进去的时候往往就是没有了,你根本没法深入进去。我写广东的时候,往往要参考香港的东西。我就觉得挺难的,上海、北京的作者写城市拥有的参照系是比较多的,但广州好像很难找到一些可参照的资源。那些能够参照着变成文化的、变成文学艺术的东西比较少。我看很多资料,都找不到感觉。我也想写一些有历史感的、有点难度的,因为写当下的对我而言没有难度了。浮光掠影地写广州是容易的,但是要深入进去就特别难。你没有做文学准备的时候,就看不到这种难度。但你进入到那些材料当中,走进过去的那些历史档案里,会发现难度特别大。广州的东西普遍都特别散,而且没有现成的文学资源可以参照。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当然是需要更多的作家去努力完成,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难度什么的。
唐诗人:对,我们不写小说的人,总会觉得广州有那么多的家族故事、歷史变故,应该很好写。但肯定不是那么容易,外行觉得容易的事情,作家们肯定也曾去尝试过。之所以至今没写出来,应该就是您说的这种难度。我很期待张老师您刚说的有在做这种准备,去写一个更广州、更历史的故事,塑造出一个属于广州的独特形象。我们这次讨论就先这样吧,谈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对我有很多启发,也解了我很多疑惑,谢谢张老师!
(栏目责编:朱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