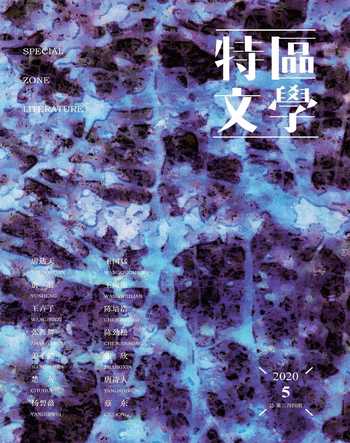广州:中心的边缘与边缘的中心
王威廉 陈培浩
王威廉:广州是一座奇特的城市,也是我迄今为止置身其中最久的一座城市。广州的历史是极为丰厚的,这让很多初来乍到的北方人极为吃惊。北方人经常怀着故乡历史悠久的情结,总觉得南方是荒蛮之地,但来到广州,发现这里的历史文化一点也不短,而且它的特色至今还相当浓郁。广州是中国城市中的异类,是一个完全以商业立足并持续至今的城市。我曾经在广州与北京的城市对话中提出,根据考古学的发掘来说,城市聚落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城市在古代汉语中实际上是两层意思,一个是强调军事政治的“城”,一个强调经济贸易的“市”。在我看来,在中国,“城”的代表是北京,“市”的代表就是广州,北京与广州的对话代表着“城与市”之间的对话。有人一定会提到上海,我觉得先不说上海的历史短暂,上海本身恰好介于北京与广州之间,而且它具备更加强烈的现代性。与之相比,广州的历史漫长,而且几乎从未断绝过和海外的贸易联系,即便是闭关锁国的清代,广州也承担着清帝国与世界之间接触的窗口。
陈培浩:你对“城”和“市”的辨认很有意思。的确,如果让我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广州的话,那恐怕只能是“商业之城”。当然这里的“城”的内涵已经是你上面所说的“市”了。商业其实不仅代表了一种经济形态,商业之城的意思不是说这里除了商业没有其它。而是說在长久的商业贸易氛围中,当地的文化和思维都渗透着某种更强的日常性和实用性。诗人杨克在《天河城广场》一诗中写道:在我的记忆里,“广场”/从来是政治集会的地方/露天的开阔地,万众狂欢/臃肿的集体,满眼标语和旗帜,口号着火/上演喜剧或悲剧,有时变成闹剧/夹在其中的一个人,是盲目的/就像一片叶子,在大风里/跟着整座森林喧哗,激动乃至颤抖//而溽热多雨的广州,经济植被疯长/这个曾经貌似庄严的词/所命名的只不过是一间挺大的商厦。这里颇有意味地道出了广州以其商业性对政治性词汇的转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商业性对政治性的转换是整个中国的趋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广州的城市重要性和影响力才凸显出来。
王威廉:我住的附近,有座森林公园,叫大夫山森林公园。我一直疑惑,为什么要叫“大夫山”呢?后来查了写史料,才发现,那里早年叫大乌岗,后来因纪念西汉初年的大臣陆贾大夫而改此名。这里边的故事特别值得一说。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不想用兵征伐在岭南拥兵自立的赵佗,于是派谋士陆贾南下,说服赵佗归顺汉朝。陆贾凭着他出色的口才,居然真的说服了赵佗,并代表大汉王朝封赵佗为南越王。陆贾因此立大功,被封为上大夫。刘邦死后,吕后临朝,从经济上制裁南越国,赵佗愤而反抗。吕后发兵南下,攻打南越,赵佗抵抗并反攻到湖南一带,一度占领了长沙国边境数县,断然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公元前179年,吕后死,汉文帝刘恒即位,派人重修赵佗先人墓,置守墓人按时祭祀,并给赵佗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物。又经丞相陈平推荐,命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再次说服赵佗归汉。赵佗再次接受了陆贾的劝说,复归大汉。虽然在南越国内,仍然继续用着赵佗的皇帝名号,但一直到汉景帝时,赵佗都向汉朝称臣,每年都会派人到长安朝觐。它是一个复杂的纪念,纪念的是岭南边地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复杂关系。边缘在中央权力变弱之际,便会试图生长出自己的中心性。这一点在广州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广州的历史中一共出现过两个独立的王朝,南越国历经5帝,共93年;南汉国历经4帝,共53年。也就是说,广州历史上总共出过九个皇帝,这是许多人想不到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广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推动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个文化系统里边,受到压抑的异质性的文化元素,往往反而会在大文化系统面临危机的时候,焕发出应对的力量,从而为大文化系统提供更新前行的力量。
陈培浩:边缘也会生长出自身的中心性,这个故事有意思。我来讲讲另一个故事,一个文学中的城市故事。卡尔维诺在他的《看不见的城市》中“城市与名字之二”中讲述了一个叫莱安德拉城的故事。有两种神灵保护着莱安德拉城。两种神灵都非常细小,非肉眼所能看到,他们为数众多,以至无法数清。一种神灵栖身房屋的门口及室内衣架和伞筒处,在搬家时,他们也随着交出钥匙的住户,定居在新住所里;另一种神灵就在厨房里,喜欢藏在炊具下、壁炉罩里,或者在放扫帚的储藏间里。他们属于房屋的一部分,当住户搬迁离去之后,他们仍留下来,与新来的住户做伴。前者被称为“宅神”,后者则称为“守护神”。宅神是跟随主人流动的,守护神则跟随房屋留守。因此,在一所房屋里,总不免发生宅神和守护神之间的交往、共处、辩论和摩擦。他们一起在飞檐和暖气管道上散步,就家政加以评论,他们很容易发生争吵,但也可以和平共处上几年。卡尔维诺写道:“莱安德拉的实质就是他们永远争辩不休的题目。哪怕是去年刚刚来到的宅神,也认为自己是城市的灵魂,并且相信自己离开这里时会把莱安德拉一同带走。守护神则认为宅神是不速之客,是令人厌烦的侵略者;真正的莱安德拉是他们的,是他们使一切内涵具有了形态,是他们在这些暴发户抵达之前就栖息于此,在那些家伙离开之后仍将继续留下来。”莱安德拉不是任何一座具体的城市,而是迁徙与流动成为常态的现代都市那种外来与本土之间冲突的象征化。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在广州,宅神和守护神可能是争吵最少的,广州跟深圳这样的新生移民城市并不相同,它的根性深深地通向历史、文化和方言,可是这并不妨碍它那种如粥沸腾般的温润和涵纳。广州可能是宅神和守护神最和平共处的城市了,可能,每个周末它们正相约在叹早茶。
王威廉:广州,平日低调到尘埃里,却总是在沉默中酝酿着新的事物、新的变化。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从清代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到现代巨型商贸都市的崛起,广州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改革开放后的这四十年,广州更是引领风气之先,在经济上有着鲜明的主动性。换句话说,广州的民间商贸力量是最为活跃的。广州市也一直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文化建设,截至2017年,广州中小企业突破700万家,企业增加值接近4万亿,占GDP的比重超过50%。因此,广州与北京、上海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北京作为首都天然具备了各种资源上的优势;上海和深圳有些相似,都是在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天之骄子”,它们历史不长,刚劲十足。但是广州,建城于公元前214年的秦代,比北京的历史都要久远得多。但包括广州人在内的中国人,似乎都不大重视广州的历史维度。也难怪,从地理上看,广州偏于东南边陲,与北方又有五岭相隔,因此又被称之为“岭南”。外边的人觉得它远,它自己也觉得自己远。它被迫要面对无尽的海洋,寻找新的联系。所幸,在海洋中有别的大陆、别的岛屿,它遭遇了多种文明。因此,唐代起,就在广州首置市舶司,这也是中国首个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从此,广州作为连接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角色,已经注定。它在现代城市的综合指标方面,与香港、深圳相比,肯定各有优劣,但是,它作为岭南区域的地方文化中心,提供的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认同感。
陈培浩:诚然,广州像一座桥梁一样在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之间架设了某种商业文化地带。商业文化的发达,带来对日常性的强调,这意味着对高蹈神话的拒绝,因此玄学家在这里不会太有市场,民众的思维更重实用而非玄虚。人们经常做的对比是,东北人非常讲究体面,穿貂就是这种体面文化的重要体现;但广东人在穿着上却极端低调,路上穿着拖鞋大裤衩的大叔可能就是个亿万富豪。商业文化的发达也体现在服务精神上,80年代最早穿梭于南北做生意或旅行的人对此有非常鲜明的印象,商业文化发达的广州,商场酒店等服务行业从业者的服务态度和意识是北方城市所无法相比的。商业文化也带来更强的契约精神,带来对口腹之乐穷尽可能的追求。因此,生活在广州会非常舒服,一个以商业逻辑来运作的城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冰冷,它事实上充满了热气腾腾的人间性和日常性,它的思维更接近于常识,不会因为价值、立场、性别、区域等等的因素而排斥外来者。
王威廉:广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位置,涌现出了一批经典的革命文学作品。比如欧阳山的《三家巷》、陈残云《香飘四季》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改革开放之后,广州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急先锋,文学被商业大潮所裹挟。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反而不算多。刘斯奋《白门柳》是广东唯一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尽管《白门柳》是写明末,但刘斯奋说,虽然《白门柳》是历史小说,写的也是江南地区的事情,和岭南一地似乎扯不上太大关系,但创作精神和岭南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小说摆脱了多年来历史小说的写法,在题材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以前都是写的农民起义、帝王将相,但从来没有人写过高级知识分子。刘斯奋说,自己写《白门柳》,显示出岭南人不信邪、有胆量,具有独立创造的精神,从这些方面来理解,就是岭南文化的影响。刘斯奋七岁就来到广州,在广州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是地道的广州人。他对于古风的热爱,一方面出自家学渊源,一方面无不受到广州的古典气质的影响。还记得我上大学的第一堂语文课,老教授用广州粤语朗诵李白的诗歌,那诗歌忽然变成了一种婉转的歌唱,令人惊异。广州人对于古代生活方式的热爱与实践,绝对是其他地方的人难以企及的。中草药作为凉茶,是日常的饮品,就连汤里边也会放上很多中药材。
陈培浩:就着你提到的广州作家历史叙事问题再谈一谈。在广州这种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中,人们通常会认为广州的文学叙事必然重日常性而轻形而上,重此在而轻历史。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注重历史叙事,具有历史意识的广州作家也并不少见。欧阳山、刘斯奮之外,比如张培忠所写的《先知与文妖:张竞生传》便通过详细的史料考辨而完成了对一生充满争议的“一代文妖”张竞生的历史还原。陈平原称张竞生为20世纪中国的堂·吉诃德,认为“他超迈千古,特立独行,与自我作战,与风车作战,燃烧着激情,满怀着悲壮”。在历史的烟尘中挽留这样一颗特立独行的灵魂,并使其显影,令其魂魄为世人所见,这也是这类历史叙事的重要价值。此外,像熊育群前两年颇受关注的作品《己卯年雨雪》回到抗日时代,去钩沉一段在民族战争之间的悲情往事,呈现一种超越于民族主义的战争叙事,也是广州作家历史叙事的一种。魏微前些年写的《沿河村纪事》也是对历史的探讨。年轻一代的比如你,比如《绊脚石》《水女人》《鲨在黑暗中》这样的作品,虽然写的是当代人当代事,却有着十分鲜明的历史意识。它关怀和追问的是,当代如何从历史的河流中一路顺流而下的问题。同样,同辈人中的陈崇正的《碧河往事》关注的也是这个历史如何雕刻当代的问题。颇受关注的网络作家阿菩的作品主要也是历史题材,他的《山海经密码》还要筹拍电影。这是历史题材在网络传播和消费主义阅读语境中的新形态,也值得关注。事实上,广州的作家也常像这座城市一样低调。上世纪90年代就以书写都市女性而广为人知的张欣、张梅依然笔健。张欣去年还推出了长篇小说《千万与春住》;从东北移居广州的鲍十,一方面以汪曾祺式的笔致书写东北风情,另一方面又接纳了南方生活经验而有了《岛叙事》;从底层中带着野力成长起来的王十月,也有着不容小觑的倔强和视野,他近年对人文科幻的实践也引起一些关注;由诗歌而步入散文小说,从乡土而写到未来城市的黄金明阅读量惊人,写作也有很强的爆发力;此外,李傻傻、郭爽、林培源、温文锦、陈润庭、巫宏振等小说家也频频引起关注。散文方面,林贤治、筱敏、艾云这几位带着鲜明知识分子特征的作品各个个性鲜明,比他们年轻的杜璞君也以散文受关注。说到广州文学,不能不提及广州的诗歌圈。已经远逝多年的东荡子以高迈的诗歌精神依然被诗歌同道们怀念着。黄礼孩、世宾、郑小琼、凌越、冯娜、杜绿绿、舒丹丹、陈会玲、吴作歆、辛夷等一大批诗人,都用语言经营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以上所及,想到说到,挂一漏万,只是想说,广州的文学力量,其实还是颇为可观。
王威廉:微信塑造了我们,尤其塑造了当下的中国文化、当下的中国人。可是,这个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程序,是在哪里诞生的呢?这个问题似乎少有人追问。人们大多会猜测北京或深圳这两座城市。不过神奇的是,微信的诞生偏偏不在那两个高科技中心。当我得知微信诞生在我所居住的广州时,有过瞬间惊讶,然后是惊喜,仿佛自己作为这座城市的一员也分享了它的荣光。在仔细思量之后,我感到的是理解,是必然。作为国内互联网产业的起点之一,广州从未缺席过互联网的任何一波浪潮,从网易、21CN的门户时代,到如今以微信、UC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低调的广州一直是互联网企业的一片沃土。今天的微信不仅是一款移动互联网的即时通讯软件,更是成了连接一切、沟通一切的端口。张小龙说得好:“这么多年了,我还在做通讯工具,这让我相信一个宿命,每一个不善沟通的孩子都有强大的帮助别人沟通的内在力量。”在广州写作,应该思考微信所蕴含的时代新奥秘。因为有价值的写作不得不跟一个宏大的总体性发生或现或隐的紧密关系,而微信当中有着这个时代向未来跃迁的秘密。个人与他人构成的朋友圈,类似于边缘与中心的彼此建构关系。
陈培浩:关于微信和张小龙,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在腾讯将foxmail和张小龙团队收归麾下之后,马化腾给了张小龙相当的特权,即张小龙团队继续留在广州。张小龙不爱社交,连开会,很多时候都会找借口说自己起不来床,不去。马化腾就让自己的秘书叫他起床。张小龙提出,怕路上太堵,会赶不上会议。马化腾就干脆每星期都派车来接张小龙,接他去开会。显然,张小龙是腾讯中的例外,张小龙不是典型的理工男,他的天才创造力需要无拘无束的土壤才能得以呵护。因此,某个角度上说,是广州这种低调包容的文化催生了微信。腾讯也因为包容了某种大公司文化中的异质性而得到了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