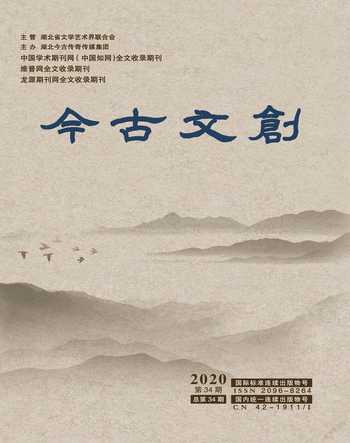关于《摸彩》与《河伯娶妇》中献祭仪式的比较研究
【摘要】 《摸彩》作为雪莉·杰克逊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曾引起世界各地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但始终缺乏比较文学视角的研究。本文旨在分析献祭仪式在《摸彩》中的反映,并将其与源自中国古俗的故事《河伯娶妇》进行比较,从集体无意识、意识形态压迫和狂欢化讽刺的角度解读神圣仪式的世俗化过程。帮助读者在中外文学比较的视角下直面人类历史中的愚昧与荒谬,以更包容的心态和更强大的勇气去接受自身面临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 献祭;《河伯娶妇》;《摸彩》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18-02
一、集体无意识中的共同犯罪
在《摸彩》这篇小说中,“摸彩”在村子里成为一个传统的献祭仪式仅仅因为一句古谚:“六月里摸彩,玉米熟得快”,这本身就体现了集体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盲目与愚昧。在残忍的暴行面前,即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仪式的牺牲品,村民们仍没有质疑或是反抗。他们并不了解献祭仪式,不追溯仪式的起源,不探寻仪式的意义,只是浑浑噩噩地成了荒谬仪式的参与者。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个体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立场,进而退化成另一种道德与智力都很低下的生物。人类本性中隐藏的恶意被不断放大,自私与冷漠使这种病态的影响愈演愈烈。“摸彩”这一仪式是随机的,盲目的,具有煽动性的。在这样的影响下,普通村民的聚集是无意识,漫无目的且无意义的,就像一群羊在祈祷自己不会成为那只替罪羊。当赫群森太太“中彩”后,村民们丢掉仁慈,像刽子手完成任务一样完成了共同犯罪。同时,献祭仪式巩固了村民们的团结统一,这样的共犯模式使每个人都难以逃脱,只能年复一年地重复并拥护这个仪式。
与《摸彩》这个发生在西方近代的故事相比,《河伯娶妇》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战国时期,而这一习俗起源于原始时代,有文献可考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原始农业的收获几乎完全依仗自然天气和雨水,而雨水总是难以满足作物的实际需求,干旱和洪涝都会严重威胁到丰收,因此,原始人类极度渴望适量的雨水。可是在那个生产力极度匮乏的时期,他们对有关降水的科学知识并不了解,认为降水量是受神秘力量支配的,从万物有灵的角度出发,他们把这种神秘力量归于河神所有,人类为河神举办婚礼其实是一种对河神的献祭。河伯是中国古代河神的典型代表,被选作当新媳妇的少女无力反抗,只能坐在草席上飘向河中央,直至沉没才作为祭品完成了献祭仪式。除非出现西门豹这样极度强势的角色,她才可能获救,这反映了内化河神信仰过程中人类群族的集体无意识。在整个婚礼过程中,无论是帮巫祝挑选年轻女孩的人,还是出份子钱观看庆典的人,全都隐秘地促成了共同犯罪。
不管是在《摸彩》还是在《河伯娶妇》中,献祭仪式的开端本来都是神圣且有一定意义的,仪式体现了先民对于世俗与信仰的思考,是远古人性与文化的遗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类对抗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仪式的神圣性和权威性逐渐消退,献祭仪式就这样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变成了荒谬可怖的惨剧。
二、意识形态压迫中的权力展示
在《摸彩》中,村民们虽然不了解献祭仪式的起源与意义,但还是将其奉为习俗与责任。这一仪式其实暗含了权力机关,这个系统从最开始就由几个人领导大部分人,村民们在权力机制建构的对话体系中被管理,被驯服。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人行使它,如“摸彩”的主持人夏莫斯先生,痴迷传统的华纳老人和恶毒伪善的戴拉克罗莱太太:夏莫斯先生受人尊敬,却是这场罪恶仪式的主持人;华纳老人是村子里年龄最大的,不仅没有丝毫反省,还带头呼吁人们拿起石头;戴拉克罗莱太太看似和善,却毫不犹豫地选了一块用两只手才能堪堪捧起的石头砸向赫群森太太。他们暴露出人类最原始的动物本性,在他们虚伪的表象之下,是残忍的暴虐与冷漠的自私。整场仪式通过暴行展现着一种意识形态压迫,如摸彩的中奖者将被石头砸死,如果哪位村民拒绝参与,将被视为异端,招致灾祸。这样的仪式像病毒一样侵入家庭,文化与教育,年复一年,扩散到一代又一代中去。权力的高层通过这一贯穿始终的意识形态压迫下层群众服从他们的规则,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展示权力以获得满足。
这样的权力展示在《河伯娶妇》中也有体现。前人思想中,神的配偶也应该是神圣高贵且品貌端庄的,因此公主往往是最优选。可随着君主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国王不再想牺牲自己的女儿,但又不能违反传统习俗,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式:册封平民女孩为公主,再将她嫁给河伯。在《河伯娶妇》中,女巫师和她的学徒们被人们视为可以与河伯沟通的庄严信使,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装神弄鬼,中饱私囊;乡绅们借着河伯娶亲的名义向平民征收财物,实际上只是以此为托词,名正言顺且肆无忌惮地敛财;富人们心照不宣地交了更多的财物,实际上只是为了交换权力,避免牺牲他们的女儿。他们在仪式中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掌控规则,剥削压迫平民百姓,在举行仪式的过程中同样展示着权力,在维护统治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进行着意识形态压迫。
神圣仪式的世俗化不仅受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还受小部分人对群众进行意识形态统治与壓迫的裹挟,这个过程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为这小部分人往往披着德高望重,名正言顺的伪善外衣。即便如此,《摸彩》和《河伯娶妇》这两个故事的读者还是可以窥得一斑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毕竟特权者的洋洋自得与大众的惶恐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狂欢化讽刺中的喜与悲
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美学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狂欢与反讽的结合。这一特点在《摸彩》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在读者眼中,“摸彩”这一仪式是灭绝人性的荒诞传统,然而在村民眼中“摸彩”是一场狂欢庆典。面对这样可怕的仪式,人们聚集在广场上,非但没有静默,反而高谈阔论,谈笑风生。不管是经营煤矿的资本家还是普通村民都参与进来,每个人都是仪式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被严重异化,从而在群体中感到孤独,极度异化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将献祭仪式变成了一种对抗单调生活的调剂。亲情,友情与爱情在异化中消磨殆尽,剩下的只是人人共有的狂欢,喜中有悲,悲中带喜。在基调沉重的主题下,《摸彩》这篇小说表面上的氛围反而其乐融融,充满欢声笑语。每个人仿佛都有“笑”的理由,而实际上形形色色的“笑”中有平静也有忐忑,有了然也有不安。这样的讽刺同样体现在赫群森一家的表现中,随着仪式的进行,他们一家人经历了喜与悲大起大落的调转。直到故事最后,赫群森太太在人群的围攻中发出一声尖叫,但她终于解脱了,留下的是仍然惶惶不可终日的幸存者们。
在《河伯娶妇》中,献祭仪式以娶亲的形式举行,和“摸彩”一样是整个村子一年一度的大事。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婚礼本身是要大摆宴席,热闹喜庆的,具有狂欢化特质。可这个故事里,新娘却是从未露面的新郎的祭品,在全村人的庆贺声中,新娘一家只能默默咽下伤心的泪水,不知是喜是悲。即使举行了仪式,人们还是担心河伯会不会发怒,担心收成会不会变好,担心哪家的姑娘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在这样的“狂欢”中悲喜交加。而西门豹的出现带来转折,他巧妙地运用了狂欢庆典的体系,看似粗暴且“疯狂”地“表演”着,借巫婆与乡绅的说辞将他们都投进河中,推翻了旧有的统治关系。令所有人震惊的同时,也预示着普通百姓的希望,暗合了狂欢化理论中的“颠覆”精神。
虽然在集体无意识与意识形态压迫的影响下,神圣仪式逐渐走向世俗,但人类本真的情感从未改变,这些情感可以使人自私,也可以使人无私。在《摸彩》中,有赫群森太太这样的人为拉低中彩概率,竟试图拉已经分户出去的女儿女婿下水;但也同样有悄声说话的女孩子,仅仅因为是朋友而不希望小南西成为中彩者,但谁又知道赫群森太太曾经是不是也像那个小女孩一样呢?她在摸彩前的迟到也许是因为似有所感。亚当斯太太对“摸彩”提出的质疑在下一年会有人重提吗?而《河伯娶妇》中,邺城迎来的转折又能持续多久,其他地区又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呢?在喜与悲的混杂中,在这样的震撼与反差中,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即使神圣仪式变成了世俗狂欢,读者仍需品味其中隐含的“颠覆”精神。
四、结语
纵观《河伯娶妇》与《摸彩》两个短篇,虽然一古一今,一中一西,但它们有着相似的文学人类学内核。在现当代人眼中,献祭仪式是残酷愚昧的,但神圣仪式的背后蕴藏着人类原始的生命脉动。即使集体无意识的盲从将其变得疯狂,意识形态压迫控制着平民服务统治者而非仪式本身,在神圣仪式世俗化的过程中,人性与人情始终在那里:善良与邪恶,快乐与悲伤,文明与愚昧,理智与疯狂……总是具有两面性,暗含着颠覆与平等的力量。随着文明的演进,人类应该学会直面历史,直面人性,在自省和反思中带着勇气与包容迎接未来。
参考文献:
[1]黄浩.河伯娶妇故事的原型及其流变[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120-121.
[2]胡喆.集体无意识的狂欢——论《摸彩》中的意识形态压迫[J].名作欣赏,2019,(20):159-160.
[3](美)雪莉·杰克遜.摸彩[M].孙仲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4]杨莉,周楠.从《摸彩》中的“笑”解读小说的恐怖来源之一[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4,(09):45.
[5]张晓旭. 《药》与《摸彩》比较研究[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1):49.
[6]詹鄞鑫.河伯娶妇古俗考[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1):65-67+100.
作者简介:
景秀,女,汉族,山西大同人,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英(美)文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