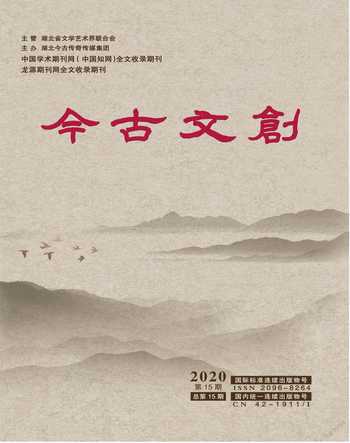文学作品中的“女扮男装”现象研究
【摘要】 “女扮男装”是中外文学作品中一个经典而独特的母题,它是指作品中女性人物乔装成男性的情节,此外,乔装后通常还伴有一系列社会活动。关注这一话题时,除了情节设置外,更需要注意其背后的性别意识。本文以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和明代作家徐渭的剧作进行比较,以此来管窥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两性关系的认知与思考。
【关键词】 女扮男装;性别意识;两性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5-0035-02
一、前言
在文学作品里,女扮男装往往作为一种出其不意的情节而设置,作者常将此描写为女性装扮成男人的模样进行(其本性别会受阻的)活动,“扮男装”被作为达成某种目标的方式。它通过换装打破了“男”与“女”两者间固有的界限,在造成喜剧效果的同时又引人深思,令行文更跌宕,故多见于戏剧创作中。随着性别平权意识的进步,尤其是女性的活跃和发声,文学作品中的这一母题也逐渐为学者重视,并开展分析研究。本文以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以及中国明代剧作家徐渭的《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为例,综合这些作品中的一些形象进行探讨。文章将分为五个部分,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之前加入了性别研究方面的理论,尝试更全面把握这一主题。
二、性别与服装
在女扮男装的情节中,服装作为一类重要的媒介而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后世大众趋向中性化的服饰选择,莎士比亚及徐渭作品的创作年代(16世纪)将服装与性别关联得更加紧密,服饰在这里成为人们对自我性别认知的外化表现,此时它的区分功能格外显著。人们的穿着打扮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活需要,更成了某种象征——例如裤装、长袍等通常被认为是阳刚的,代表着男性气质。正是这样,两性之间的界限被划分得相当明确,服装相当于一种权力场,尤其是对于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而言。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中,提到性别乃至一切身份都具有表演性,“所谓性别表演就是‘我’在扮演或模仿某种性别,通过这种不重复的扮演或模仿,‘我’把自己构建为一个具有这一性别的主体”。这实际上指出人们对于“性别”的连带反映(认为男性坚强,女性柔弱等)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世代积累的主观建构,而后来者为了符合这样的建构,会有意识地将自己打磨成“认定中”的样子,这便形成了一场表演。在出现女扮男装情节的作品中,人物往往是为了求得认证而选择变更服装;而在服装变更之后,她们又会通过模仿来进一步伪装,完成从表面到深层的全方位“改变”,这可以说是一次愚弄。服装为两性认知划出界线,然而也正是因为它们在观念中的绑定关系,才让作品中的“跨越”成为可能。
三、出走与回归
在涉及具体情节描写时,发现“女扮男装”作品的一个共通之处,它们均以“认可——出走——回归”这条脉络进行。这明确展示出部分女性尝试追寻自我,但在最后又返回到从属地位的过程,这是突破之举,亦是无奈之举,以下综合文本详细阐释。
(一)认可:女性身份的接纳
“女扮男装”情节在作品中通常作为一个重大转折点出现,借此营造出一定的戏剧性。转折前,女主人公们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受限的社会权利是很悦纳的。《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纵然有显赫家世与可观财富,但面对择匣而来的丈夫,她仍然先把自己放在低位—— “我只是一个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缺少见识的女子”,《雌木兰替父从军》中花木兰上战场前也暗自思忖“回来俺还要嫁人,却怎生?”木兰父母因她是女儿身而忧愁,她反过来劝慰二老“您尽放心,还你一个闺女儿回来”。
这些女性主人公们确有优越的自身条件:从罗瑟琳、花木兰的勇猛到鲍西娅、黄崇嘏的智慧,可以说是文武兼备。但这些品质展示与否,依旧要以女性身份能否允许作为前提条件,她们自己也认知、并接纳这一点。这一认可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正常想法,不过也为后文女主人公们回归家庭埋下了伏笔。
(二)出走:释放的阀门
莎士比亚与徐渭的两部剧作里,女主人公们都是在紧急情况下而不得不扮作男人的:为亲人解围,或是出于保全生计的需要。此前,她们的才能受到女性身份的压抑,而突如其来的状况却像一个引子,点燃了其展露的愿望。鲍西娅在换装前曾夸口:“我会学着那些爱吹牛的哥们儿的样子,谈论一些击剑比武的玩意儿,再随口编造些巧妙的谎话,这些爱吹牛的娃娃们的鬼花样儿我有一千种在脑袋里,都可以搬出来应用。” 黄崇嘏应考前亦有言:“咳,倒也不是我春桃卖嘴,春桃若肯改装一战,管倩取唾手魁名!”可见她们对自己的实力是相当有自信的。往日囿于限制不得发挥,今时女扮男装,获得了外部认可后,相当于打开了一处阀门,她们借助更为强大的男性身份,得以参与社会事务,充分释放自我。
“女扮男装”,可以说是一种出走,它偏离了传统社会对于两性的划分和认知,在“灰色地带”创造可能。剧作里还描写到女主角变装后对男性的戏弄和考验:如鲍西娅执意要巴萨尼奥的指环作为报酬,还嘱咐尼莉莎“我们回家以后,一定可以听听他们指天誓日,说他们是把指环送给男人的;可是我们要压倒他们,比他们发更厉害的誓”;花木兰在营地哄二军“我花弧有什么真希罕,希罕的还有一件。俺家紧隔壁那庙儿里,泥塑一金刚,忽变做嫦娥面”,让对方惊奇不已。如此安排调侃了男性主导的环境,女性角色从被凝视、被安排的客体转变成了可以表露自我的主体。尽管她们最开始易装是出于被动,但在换装后,反而能够抓住主动权,这种在特殊环境下所表现出的机智正是女扮男装情节最吸引人的地方。
(三)回归:不完全叛逆
易装无疑是富有创新性的巧思,不过它们呈现的仍然是一场不完全叛逆。危机后,剧中女主角的结局依旧是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考虑到当时的普遍观念,这是符合常理的,然而相比她们身着男装大放异彩的场景仍稍有逊色。罗瑟琳在出走前曾道:“现在我们是滿心的欢畅,去寻找自由,而不是流亡!”易装如同一次冒险,通过这一大胆举动,她们得以实现自我价值,这份经历弥足珍贵。以回归作为结局纵然使剧情闭合成圆,但站在女性权利意识的角度上看,不免有一些遗憾。
尽管总体上四部剧作女主人公结局相似,但其中过程各异,最为突出的便是心理层面的不同。在莎剧里,鲍西娅和罗瑟琳的故事围绕爱情展开,其心理状态并未发生太大改变。与此相异,在徐渭的剧作中,主角的心理则更加复杂。花木兰从军时暗道“万般想来都是幻,夸什么吾成算。我杀贼把王擒,是女将男换。这功劳得将来不费星儿汗”;黄崇嘏回诗于丞相:“相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正是由于性别壁垒出现了缺口,花木兰才会发出“都是幻”的感慨,黄崇嘏更是抱有“作男儿”的祈愿,并不满足于安坐闺阁了。亲身感受到男女权利的区别划分,让她们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定反思。在文本里,这样的反思尚处于初步无意识的阶段,并未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不过相较于莎剧,花、黄二人的心理变化更具有进步的色彩。
四、结语
“女扮男装”作为一个经典的文学母题,具有文学和社会双重价值。它是性別易装现象的一部分,又因传统社会环境下两性话语权的巨大差距而带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变得特殊,故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更高。两性关系中,女性常常处于从属地位—— “幼子们在选择配偶方面有最多的自由,女性则很少有这种自由,因为男性家长遗赠给女儿嫁妆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接受父亲遗嘱的执行人为她们聘定的婚姻”。女扮男装情节之所以会有如此广泛的受众,是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男权环境的垄断——过去只有男人能够参与的工作,现在出现了女性的身影,虽然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极个别现象,但也迈出了从无到有的一步。本文所述四部剧作中的主人公也是如此,虽背景各不相同,但都以其地点、工作的特殊来反衬出女性群体之智慧,故更具有代表性。
“女扮男装”这样的举措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可以看作是某种对现有父权中心的反抗,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反抗规则的过程,也是服从规则的过程,只有当女性打扮成男性模样时,才能拿到对擂的入场券,这如同一个悖论。在莎士比亚和徐渭创作的年代,由于大环境没有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仍占上风,因此这个悖论得不到突破口,只能是未解。纵然能够在部分片段中觅得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也会发现它是不完备的。美满团圆的结局背后,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们思想的局限,而作者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
参考文献:
[1](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牛文馨.女性视角下16-18世纪英国两性关系的变革[D].西华师范大学,2017.
[3]杨世明.论中国古代的“色性说”及两性之不平等[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5):20-23.
作者简介:
黄淼儿,女,蒙古族,河南开封人,中央民族大学,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