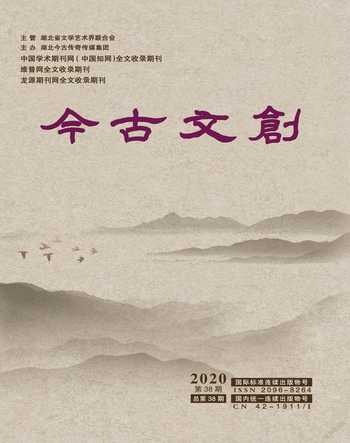孰辨真幻“大人国”
【摘要】田园诗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发源于古希腊、发展于古罗马,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利奥·马克斯在《花园里的机器》一书中将田园理想分为“大众的情感型田园理想”和“想象的复杂型田园理想”两类,后者蕴含着更加丰富的感情色彩与文学理念。17、18世纪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游记中,预见并勾勒了复杂型田园理想的雏形,对文中所建构的“大人国”的田园幻境表达了质疑和讽刺,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理想田园”。
【关键词】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复杂型田园理想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8-0013-04
基金项目:本项目由华中农业大学“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研究成果属于华中农业大学所有。
《格列佛游记》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于18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出版几个世纪以来,该著作已被翻译为几十种语言,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中国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力。作者以里梅尔·格列佛船长的视角,叙述了周游四国的奇幻旅程。通过格列佛在小人国利立浦特、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飞岛国、慧骃国四个国家的所见所闻,斯威夫特深刻剖析了18世纪前半叶英国统治阶级的腐败、贪婪与罪恶。
自《格列佛游记》问世以来,中外学者分别从小说的时代背景、政治批判、性别视角、文学形式及科学讽喻等方面发表了深刻的见解。18世纪英国经济研究学者摩尔(Sean Moore)从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该书的“催化剂”,即“南海泡沫”。斯威夫特官场失意,被放逐到了帝国的边缘,正因如此,他才得以见证了“南海”金融骗局的更深更广的结果,即被压迫者的苦难。正是这个利令智昏、金钱至上的时代,加之“后南海”年代的爱尔兰生活,催生了斯威夫特最著名的讽刺作品《格列佛游记》。森斯(Lewis Soens Jr.)和萨莱诺(Patrick J. Salerno)阐释了该书的政治讽刺意味:“在叙述的伪装下,他讽刺了人性的渺小,尤其是攻击了辉格党。”通过强调“利立浦特人”六英寸的身高,他形象地贬低了政治家的地位;通过“女王房间着火”等一系列故事,他为我们呈现出一系列对辉格党政治的批判。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性别理论学者阿敏特(Deborah Needleman Armintor)则提出《格列佛游记》中的女性缺失。小说中只有寥寥几处提到了格列佛的家庭,在他游历完大人国归家后,谴责妻女令人不安的渺小、身体的可操纵性以及明显缺乏好奇心;在他游历完慧骃国后,更是将妻子看作是“可憎的动物”,彻底地丢失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心和对家人的爱。伍厚恺指出,“《格列佛游记》的嘲讽对象既是现实世界,也包括它所借用的文学形式。”即在表面上采用写实主义与航海日志风格,实际上却对游记体小说乃至18世纪的新闻报道进行了戏谑性的模仿。颜静兰认为这部小说“集中反映了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极其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英国君主制度的腐败和丑恶”,其思想内容深刻,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和精湛的艺术风格,使其在小说形成之初就独树一帜。孙绍先从科学角度出发,深刻指出斯威夫特讽刺的正是那种歪曲科学、滥用科学的行为,“飞岛统治者和科学家的形象则是这种‘科学奴役’的最明显写照。”总的来说,中外学者对《格利佛游记》做出了较为翔实的评论,足见该小说的魅力经久不衰。
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该作品中还蕴含着丰富的田园理想,鲜有中外学者对此进行深入剖析。纵然有些学者意识到“‘布罗卜丁奈格游记’既有童话的特点,又具有乌托邦小说和哲学小说的性质,像同時代法国文学中孟德斯鸠写‘穴居人’、伏尔泰写‘黄金国’一样,重点转向描写作者的社会理想”,但他们并没有追根溯源,寻找小说中田园理想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历程。
本文着重讨论《格列佛游记》布罗卜丁奈格(即“大人国”)游记中的田园理想。“大人国”看似逃离了宫廷的尔虞我诈和尘世的喧嚣,是一种回归田园的近乌托邦社会,但实际上作者却对其田园幻境表达了质疑、讽刺与批判。这不是单纯的渴望回归田园的情感型田园理想,而是一种复杂型的田园理想。
一、田园文学与田园理想
田园文学最初形式为田园诗,也称“牧歌”,往往描写乡村与牧民的生活。作为文类,它是一种诗歌形式;但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它更可能出现在小说、戏剧等其他文类之中,只要是描写和歌颂乡村生活、自然环境的写作都可以称为田园诗。田园诗发源于古希腊。公元前三世纪,希腊诗人特奥克里特(Theocritus)创作出了最早的田园诗《牧歌》(Bucolica),描绘了西西里岛的自然风光,是诗人想象中的理想田园。田园诗在古罗马得到了发展。诗人维吉尔(Virgil)创作出了“后世田园诗的典范”《牧歌》(Eclogues)。诗中建构了位于希腊半岛东部的阿卡迪亚地区(Arcadia),在内容上,阿卡迪亚是一个极尽美妙的理想田园,远离文明的中心;在形式上,《牧歌》第一首沿用了对话体形式,即牧羊人之间的对话和对歌,诗中提氐卢斯(Tityrus)与梅利伯(Meliboeus)便以对话的形式交流。对话体是一种重要形式,这一点在后来的众多田园文学中也有体现。
田园诗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最初,田园文学仅是表达人们珍惜农耕生活、赞颂自然的美好愿望。但其内涵在17、18世纪发生了变化,田园诗的作者和读者往往都居住在都市,对田园的描写逐渐偏离了乡村现实的轨道,变成了一种“诗化的田园”。18世纪,英国田园诗展示出更加明显地对乡村生活进行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倾向。20世纪的文学理论指出,这种歌颂乡村生活的艺术形式显示出了它的文学虚构本质,掩盖了乡村严酷的政治经济现实。《花园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被称作“生态批评的先声”,作者利奥·马克斯(Leo Marx)在本书中将回归自然的田园理想分为两类,即“大众的情感型田园理想”和“想象的复杂型田园理想”。
情感型的田园理想侧重于情感上的表达。它表现在我们的休闲娱乐和由于崇拜旷野而投身的户外活动中,如野营、狩猎等,是一种想要从复杂的城市文明“退避到原始美好或乡村幸福的感伤情趣”。但利奥·马克斯深刻地指出,情感型田园理想实际上是服务于反动的或虚假的意识形态,它很容易掩盖工业文明的真正问题,只是一种心灵上的“乌托邦”。这一现象也引起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兴趣,他在《精神分析引论》(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中提出,这种回归自然的冲动正是典型的“白日做梦”。
复杂型田园理想与情感型田园理想有很大的差异。大多数被称为田园文学的作品最终并不希望我们对宜人的田园风光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作者们往往采取各种方式,描述、质疑或者讽刺绿色牧场的平静与和谐的幻想。这使我们最终弄清了复杂型与情感型的田园理想之间的区别。在西方文学史上,复杂型田园理想广泛隐含于文学作品之中:维吉尔在《牧歌》中虽创造出“阿卡迪亚”这一理想田园,但他通过描写牧羊人之间的对话,间接讲述了农民经历的苦难以及对罗马政治的不满,社会黑暗与美好的阿卡迪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免使读者怀疑阿卡迪亚的真实性;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在小说《福谷传奇》中,基于以布鲁克农庄为原型的福谷乌托邦社团,通过乌托邦、田园牧歌传统以及黄金时代神话之间复杂而隐秘的内在联系,对当时的乌托邦运动展开了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等多方面的思考和批判;而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的第二部分对和谐、美好的“大人国”这一田园幻境表达出了质疑与批判,实际上勾勒出了复杂型田园理想的基本雏形。
二、远离“城”嚣大人国:《格列佛游记》中的田园幻境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的第二部分中建构了一个“阿卡迪亚”式的、远离“城”嚣的田园幻境——布罗卜丁奈格(俗称“大人国”)。大人国的地理环境、社会特征及叙事方式都是田园诗学空间“阿卡迪亚”的延展。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大人国是田园幻境“阿卡迪亚”的变体。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诗中建构了位于希腊半岛东部的阿卡迪亚地区,与希腊大陆的其他部分隔绝。这里的人们与世隔绝、安居乐业,过着牧歌式的生活。它是一个极尽美妙的理想田园,远离文明的中心,是一个逃避烦恼的归隐之地。在《格列佛游记》第二卷中,格列佛游历到了大人国,这个王国同样拥有与世隔绝的特征:它是
一个半岛,东北边界是一条高达三十英里的山脉,山顶是火山,所以完全不能通过。半岛的其他三面都是海洋,全王国没有一个海港;河流入海处的海岸布满了巉岩,海上总是波涛汹涌。因此这儿的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完全隔绝,没有任何往来。但这里物产丰富,因为大河里船只很多,并且盛产十分鲜美的鱼;大陆得天独厚,出产特别大的动植物;人口稠密、百姓安居乐业。
大人国因为地理原因与外界的一切文明隔离,远离尘世的喧嚣,拥有着成为田园幻境的天然条件,因此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大人国是田园诗学空间“阿卡迪亚”的延展。
其次,“大人国”所展现的是一副远离现代欧洲社会、民风淳朴、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初入大人国,格列佛对这个国家巨大的人和物感到十分恐惧。他与其他水手走散,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小山,发现了巨人一般的雇工和雇主,此时他不免感到重重忧虑,“我在这个民族中间就像一个孤零零的利立浦特人在我们中间一样。但我又想到这还不是最不幸的事情。据说人类的身材越高大,性情就越野蛮、残暴。”但是接下来在大人国里遇到的一切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大人国的居民待人友好、民风淳朴。不难发现,田园诗中的农夫有着众多乡村美德,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没有不当的欲望带来的种种烦恼,邻里之间关系简单,整個乡村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正如在大人国中,农民与其雇主之间关系简单、分工明确,格列佛在初入大人国时便观察到“……这些人穿的不如头一个齐整,他们像是那个人的仆人或者雇工,因为他只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到我趴在里面的田里收割起麦子来”,这样简单的管理方式在小国寡民的大人国中是十分有效的;此外,农民生活简单而有规律,“那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仆人送进饭来。那也只有满满的一碟肉”,他们不追求华丽鲜美的食物,单纯的一碟肉便足以果腹。
在格列佛被带到首都“劳不鲁格鲁”后,王后从他主人的手里把他买了下来献给了国王,国王与王后同样待人温和,毫无傲慢之气。王后叫人为格列佛打点好衣食住行,并为他设计精美的衣服、精巧的房间。在王后的悉心照料下,格列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荣幸与温暖,他毫不掩饰地称赞道:“我后陛下是大自然之光、世界的宠儿、万民欢乐的源泉、造物主的凤凰!”在格列佛眼中,王后就是真、善、美的结合体。国王同样具有种种令人尊敬和爱戴的品质:他具有卓越的才能、无穷的智慧、治理国家的雄才,也受到人民的拥戴。他十分博学,研究过数学、哲学等一系列学科,他的知识储备并不亚于该国的任何学者。这位国王喜欢和格列佛谈话,问他一些关于欧洲的风俗、宗教等情形。他头脑清晰、判断也很精确,对格列佛所谈的一切话都发表了很聪明的感想和意见。
“大人国”的治理方式简单却有效,不需要复杂的体系,便可以把整个王国治理的井井有条,使人民安居乐业。在国王看来,治理国家的所需的知识范围很小,不外乎常识和理智,公理和仁慈,从速判决民、刑案件以及一些其他不值一提的简单事项。他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谁要能使本来只出产一串谷穗、一片草叶的土地长出两串谷穗、两片草叶来,谁就比所有的政客更有功于人类,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格列佛对大人国的社会特征做出了精简而又准确的描述:
他们的数学完全用在有益人生的事情上,用在改良农业和一切机械技术上。他们一共有二十二个字母。在他们的法律中,没有一条条文的词数超过他们字母的数目。实际上也只有几条法律有这么长。他们的法律都是用最简单明白的文字写成的……他们的军队由各城市的商民和乡下农民组成的,指挥官由贵族和乡绅来担任。他们不领薪,也不受赏赐。他们操演得非常熟练,纪律也很好。他们没有违反纪律的事情出现。
在这个国家里,不需要庞杂的知识储备、复杂的判决程序、伟大高深的发明创造、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华丽的文采辞藻,不需要一切只有用强大的外力才能控制的事物,一切治理只需要依靠最简单的方式便能取得最有效的结果。同时,这一卷也融入了田园诗学“对话体”的叙事方式。斯威夫特延续了田园文学中常见的对话体的叙事方式,通过描述格列佛在大人国中与农夫、仆人、国王和王后的对话,反映了其社会百态。其中一处典型对话体是格列佛与大人国国王关于英国的激烈讨论。格列佛开门见山,赞颂着祖国的伟大,“我一开始就告诉国王,我国领土包括三大海岛,三大王国统归一位君王治理……接着我又谈到英国议会的组织……我又说到法庭,法官们都是最可敬的贤明而通晓法律的人士……”在多次觐见国王之后,他终于直截了当地对格列佛提出了种种疑问,“他问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培养青年贵族的身心?他们在早年,也就是最可教育的时期,一般做些什么事情?”作者以对话的形式,使激烈的讨论场景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同时也引起了我们的深入思考。
在斯威夫特的描述中,“大人国”的地理环境、社会特征及叙事方式都是田园诗学空间“阿卡迪亚”的延展。它是一个远离尘嚣的理想田园,是一个近似于“乌托邦”社会的存在。
三、田园“幻境”大人国:《格列佛游记》中复杂型田园理想
但是,“大人国”看似逃离了宫廷的尔虞我诈和现代社会的喧嚣,却难免不受现代化洪流的侵染。斯威夫特在文本细节中巧妙地表达了对“大人国”幻想的质疑、讽刺与批判。他最终并不希望我們对宜人的田园风光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而是通过具体的文本,来描述、质疑或者讽刺“大人国”的平静与和谐的幻想,从而戳破这个美丽梦幻的田园理想泡影,使得文本展现出一种成熟、知性的“复杂型田园理想”。
首先,貌似古朴和谐的大人国并未能抵御现代社会之本——金钱——的巨大诱惑。在格列佛入住农夫家后,他的主人觉得他“有利可图”,便决定带他到各大城市去演出、赚钱,最终在他身体极其虚弱时以高价卖到了宫廷。农夫屈服于巨大的金钱诱惑,只有让格列佛表演才能满足他的一己私欲。农夫呈现出的贪婪的本质,与“大人国”之外的欧洲世界的资产者并无差别。斯威夫特生活在17、18世纪的英国,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原始积累时期,整个社会充斥着对金钱财富的无限崇拜和强烈占有的欲望,资产者为了追求更多的金钱而不择手段,出卖良知、腐化灵魂。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大人国中农夫的丑陋嘴脸,以此来批判以金钱为中心、泯灭良知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
其次是格列佛对大人国子民外貌的细节描写,体现出这样一种观点:再美好的东西,凑近了仔细观察,也会发现它实际上丑陋不堪。格列佛在农民家里时,看到保姆给孩子喂奶:
她奶头的颜色和乳房上的黑点、粉刺、雀斑让格列佛作呕,因为他离她很近,所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使他想起英国的太太们皮肤又白又嫩,十分美丽。但格列佛自己也意识到,这只是因为英国的太太们和他身材相等,如果用放大镜来看,就会发现,最光滑、最洁白的皮肤也是粗糙不平、颜色难看。
保姆对格列佛悉心照顾,但是当距离非常近时,还是会令他作呕。在王宫时,侍从女官们常常想趁见见格列佛,甚至想多摸摸他,但让格列佛感到恶心的是,她们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凑近了闻,她们的皮肤会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肉眼可以看到的美好存在,不过是因为距离不够近、观察不够深入。作者想借此引发读者的反思:即使我们看到的“大人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度,表面上一派安宁祥和,但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会发现它没有想象中的安宁与美好,甚至会变得丑陋不堪。
此外,大人国的人民不是完全单纯、毫无邪念的存在。第一,并不是人人都对格列佛友好热情。当格列佛的保姆带他去拜访侍从女官时,最令他不安的是,“她们对他一点儿也不讲礼貌,把他当作一个微不足道的生物。她们在他面前剥得净光,然后再穿上衬衫,但格列佛一点也感觉不到什么诱惑,除了恐怖、厌恶以外,没有别的感情”。格列佛虽然渺小,但是一个有理性的生物,他的文化水平要比这些侍从们高得多,但只是因为身材矮小,她们便没有把格列佛平等对待,甚至漠视了男女之别。第二,并不是人人都具有同情心。格列佛被强拉去看一个罪犯被执行死刑。在行刑时,犯人“从静脉管和动脉管喷出了大量鲜血,血柱喷的很高,就是凡尔赛宫的大喷泉也赶不上它。人头落在断头台的地板上砰的一声,吓了我一跳,尽管我还远在半英里之外。”尽管格列佛还远在半英里之外,但人头落在断头台上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他没办法不听到这个残忍的声音。他们没有给犯人一丝的尊严,他被迫接受当众行刑的惩罚,在一片讥笑与议论中羞愧离世。第三,照顾格列佛的小保姆也是有狡猾的一面的。“虽然葛兰达克利赤格外爱我,但是有时我做了一点呆事,她以为可以讨王后喜欢,就跑去报告王后,显然她这人也是很狡猾的。”在这里,她是一个谄媚小人的嘴脸,就像当时欧洲政客那副嘴脸一样,使人厌恶。因此,“大人国”的人民不是完全单纯、毫无邪念的存在,每个人都有丑恶的一面,只是会在不同的场合下表现出来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大人国”的人民非常清楚自己与动物的区别,他们自认为高其他生物一等。在游记的第一部分“小人国”游历时,格列佛把当地的居民仅仅看作是身形矮小的人;但大人国的民众从未把格列佛当作一个具有灵魂的人来看,只是认为他是一只有灵性的昆虫,他们无意识地堆砌了高人一等的堡垒,将格列佛拒之门外。此外,一只猴子把格列佛错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捏伤了他的腰部,使他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本以为最坏的结果是抓到猴子,然后关起来不让它继续害人,但格列佛听到的消息却是“猴子被杀死了,同时王后还下令,以后宫里不准再饲养这种动物”。猴子本来是抱着母亲的心态,想要抚养格列佛,但最后整个族群都被驱逐出宫。由此可见,在伤害到人类的情况下,大人国的王公贵族们对动物毫无怜悯之心,他们从未将每一个生灵平等对待。所以当我们再重新审视大人国国王与格列佛之间“众生平等”的对话时,就会发现斯威夫特通过文本的这些细微之处巧妙地讽刺了大人国的田园幻境。
四、结语
《格列佛游记》中“大人国”看似逃离了宫廷的尔虞我诈和尘世的喧嚣,是一种回归田园、小国寡民的“近乌托邦”社会,但实际上作者斯威夫特却在细节之中对“大人国”的美好幻想表达了种种质疑、讽刺与批判。他没有一味地鼓励我们去追寻美好的田园世界,而是通过田园幻境显示出来的困境,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理想田园,进而思考如何更深入的改造当今社会。一味地逃离和躲避只能换来片刻的安宁,而协调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才是最终的出路。这不是单纯的回归田园的情感型田园理想,而是一种复杂型的田园理想。
参考文献:
[1]A.Lewis Soens Jr.,PatrickJ.Salerno.Gulliver's Travels-Cliffs Notes[M],2000.
[2]伍厚恺.简论讽喻体小说《格列佛游记》及其文学地位[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5):9-15.
[3]颜静兰.讥讽权贵 嘲弄暴政——江奈生·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游记》[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116-118.
[4]孙绍先.论《格列佛游记》的科学主题[J].外国文学研究,2002(04):99-102+174.
[5]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田园诗[J].外国文学,2017(02):83-92.
[6](美)利奥·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M].马海良,雷月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尚晓进.乌托邦、催眠术与田园剧——析《福谷传奇》中的政治思想[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32(06):79-85.
[9]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M].张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0]JonathanSwift.Gulliver’s Travels[M] OUP Oxford, 2008.
[11]维吉尔.牧歌[M].杨宪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12]廖衡,朱宾忠.远离“城”嚣的乡村赞歌——论亨利·菲尔丁小说中的田园因素[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5(06):157-163.
[13]廖衡.亦真亦幻“黄金乡”——论《一九八四》中的田园主题[J].湖北社会科学,2017(01):129-135.
[14](英)雷蒙·威廉斯.鄉村与城市[M].韩子满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作者简介:
孟阳,女,汉族,山东淄博人,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在读生,研究方向为18世纪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