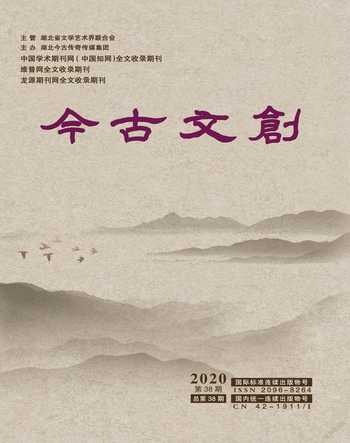“七子”与“三曹”邺下交游及其诗文创作
【摘要】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交游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从内容上来说,他们的诗文创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应制之作;二是以南皮之游、西园之游为代表的寄托幽思、抒发情志的宴游之作;三是在东阁讲堂创作的以小见大的“箴规”之作。其中,寄托幽思、抒发情志的宴游之作在建安文学中价值最高,且在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键词】邺下;交游;诗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8-0004-03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201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建安七子邺下交游探究”(项目编号:2019-ZDJH-689)。
《武纪》:“(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署为丞相副。”裴注引《魏书》:“封植为平原侯,邑五千户。”《魏志·邢颙传》:“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 ①建安十六年曹操假天子之名封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封曹丕为平原侯并为二子“高选官属”,这就为建安时期邺下文人集团开展相关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钟嵘《诗品》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此时,至少曹氏父子与刘桢、王粲等已经在邺下开展文学活动。邺下文人究竟何时开始文学活动,学界对此尚无定论。②但毋庸置疑的是,邺下文人在建安年间文学活动较多,且他们之间交往频繁,而建安十六年曹丕、曹丕封侯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集中活动的契机与舞台。以刘桢、王粲为代表的邺下文人与三曹游处融洽,曹丕兄弟甚至与其“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邺下文人积极参与了诗赋唱和、切磋诗文等交游创作活动,或借物兴叹,或即兴赋诗,或唱和抒怀,或集体创作,亦形成了建安文学创作的一个高潮。本文拟通过考察邺下文人的文学创作,归纳其文学创作的内容,探讨其与当时政治生态的关系。
一、铜雀台赋与政治命题
三曹七子作为特殊时期的文人集团,其政治性是不可避免的,其文学创作也必然要为政治需要服务。在曹操的倡导下,以《铜雀台》赋为代表的政治命题作文蔚然成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曹操南征孙刘,曹丕、陈琳、阮瑀、徐干应瑒等人随行,初期战争进展顺利,但他们都对赤壁之役投以关注,他们创作了《述征赋》(曹丕)、《纪征赋》(阮瑀)、《序征赋》(徐干)等诗赋并预知曹军赤壁之败。如徐干的《序征赋》:
“余因兹以从迈兮,聊畅目乎所经。观庶士之缪殊,察风流之浊清。浴江浦以左转,涉云梦之无陂。从青冥以极望,上连薄乎天维。刊梗林以广涂,填沮洳以高蹊。揽循环其万般,亘千里之长湄。行兼时而易节,迄玄气之消微。道苍神之受谢,逼鹑鸟之将栖。虑前事之既终,亦何为乎久稽。乃振旅以复踪,泝朔风而北归。及中区以释勤,超栖迟而无依。” ③
从“行兼时而易节”至结尾是描写南征大军北归时的情景与心境,这一层总体上概括而不确指具体败事,从而就会避免曹氏政权对这次败绩的不愉快的回忆,接着赋中写秋冬战事与未来的春夏相接,又暗示将来会带来统一天下大业的转机,未来将是美好的。在这里,徐干虽讳言败事,但也绝不是其无聊的心境的表达,而是这一代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反映。
最有名的同题创作是曹氏父子的《铜雀台赋》。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发布《让县自明志令》,同年冬却下令修建铜雀台,以微妙方式宣示自己代汉自立的政治意图。许慎《五经异义》载:“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 三台本是天子属物,曹操却于封魏公前后分批在邺城建造了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合称“铜雀三台”,隐有王霸之意。铜雀台修成后,曹丕兄弟与七子陪同曹操登台作赋。《三国志·曹植传》记载:“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④尤其曹植的《登台赋》:
从明后之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功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呈。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虽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权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尊贵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⑤
《登台赋》由写景状物自然转换到抒情颂德,将“圣德”“仁化”“桓文”“圣明”等颂德词汇化用于赋,处处颂扬曹操,最后用“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权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 ⑥的最高分贝把修建铜雀台的政治功用,与歌颂曹操的功业统一起来,才思敏捷,思虑甚周。
总之,建安时期的这些同题之作,不仅继承了东汉中后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关注社会现实的特点,还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密切相关的特性。具体来讲,建安七子是曹氏父子最为亲密的文学侍从,他们虽然有抒发个人感情,展现其理想抱负的文学作品,但是他们的人生命运与曹氏父子紧密相连,所以他们关注现实、同时也对政治投以热切的关心,与正始文学形成鲜明对比。
二、南皮之游与西园游宴
令曹丕和后来者念念不忘的是南皮之游。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说道:“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沈约距离南皮之游不远,感慨“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宋人苏颂《公说再和并前十五篇辄复六章用足前篇之阙》其四云:“追寻燕友南皮会,谁继曹刘七子诗。”南皮之游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
俞绍初考证说南皮在漳河下游的渤海之滨,在邺城的西边,距邺城约有五百里路程。“南皮之游”发生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五月,时曹丕被封为五官中郎、副相,带领不少文人学士游至南皮,与友朋诗酒赋会,愉悦欢洽。这一时期,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社会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曹丕游猎南皮是驰骋畋猎、情致飞扬之行,充满了昂扬的色彩。建安二十年曹丕的《与吴质书》写道:“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⑦这不是普通贵族子弟的游冶嘻乐,而是既有琴棋六博之欢愉,更有清泉寒水之情操、六經百氏之远思,其风趣自是不同。他们相处的如此融洽,“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 ⑧,简直融洽无间,形影不离;他们意兴飞扬,“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⑨,这种壮思揽月、浑然忘物的状态,令古今多少文人向往不已!
遗憾的是,南皮之游留下来的诗文多散佚,我们只能从曹丕以及他人的描述中想见当时的盛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必然留下不少佳作,并深有影响。正如俞绍初先生所言:“及至建安十六年,因有南皮之游,遂将邺下文人集团群体性的诗赋创作推向了极致,呈现出高潮。” ⑩曹道衡和沈玉成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也赞道:“曹丕与诸僚属文士大会于南皮,高谈畅论,弹棋博奕,遂开以后邺下游宴论文之风”。⑪从相关论述可知,南皮之游构成了建安文学关注社会现实之外的又一面相,即通过文人间的交流沟通,高扬个人理想,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典型代表。
据俞绍初先生考证,西园宴游发生在南皮之游一个月之后,也即建安十六年六月曹丕等一行人從南皮归来之后。西园宴游将南皮之游的余兴引向了高峰,文人们除了游兴之作外,在人生思考、精神境界上也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将漳河引入邺城解决了城内居民的用水问题, 也为营建园林做了准备,铜雀台建成后,即在文昌殿西侧,依台建园。铜雀园位于邺北城(邺因洹水分南北二城),故称北园,因其在北城的西北角,又被称为西园。铜雀园清水长流,景色秀丽,园中有铜雀台、芙蓉池等等景观,三曹曾多次率众人游于西园,诗酒唱和,“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曹丕、曹植、王粲、刘桢等均有诗作描述昼夜欢饮、夜游西园。
这一时期留下的名篇主要有曹丕的《芙蓉池作》、曹植、应旸、刘桢、阮瑀的《公宴诗》等。如曹丕《芙蓉池作》诗云: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拂轮毅,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详细描述了西园的内部环境,同时用用开阔的视野观照西园的外部环境,将情思引到丹霞明月间,最后感慨人生短暂,当珍惜眼前美景。曹植《公宴诗》诗云: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飚接丹毂,轻晕随风移。飘摇放志意,千秋长若斯。⑫
其思路与曹丕基本是一致的,皆是由近及远,进而生发人生慨叹,只是其情思更显飘逸,意境更为深邃。时代的动荡,让人普遍有一种刻到骨子里的无常感,不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况,总不自觉生发出些许感慨。应旸、刘桢、阮瑀等人的公宴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如应旸《公宴诗》:
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⑬
应旸展现的是西园之会其乐融融、觥筹交错的公宴之景象,在宴席之上,大家通过辩论来化解心中的郁结,并把这些诉诸于文章。邺下集会虽然是曹氏集团吸引文士的有效手段,但是客观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与演化,这也就使得西园之公宴诗无论是在深度与广度的上都与后世宴饮诗不同。
文人间的觥筹交错固然使人感到酣畅淋漓,但酒醒之后就会往往使人感到惆怅,西园之会正是表现这种盛景之下的幽思,当时文人们对时代、对社会的思考,将自己短暂的人生与离乱的时代相比,感慨人生的短暂与世事无常,使得西园之趣别具一格,成为建安时期的代表性文化象征之一,并为后世文人所向往。
曹丕《与吴质书》回忆起曾与徐干、应瑒、陈琳、阮瑀、刘桢等人一同游宴,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南皮之游与西园宴游一同将建安文学推向了高峰,成为文学史上令后人念念不忘的佳话。
三、讲堂唱和与文以载道
除了政治命题、宴饮交游之外,邺下文人集团还有一个重要的集会是讲堂唱和。讲堂(一作讲坛)指东阁讲坛。顾炎武《历代宅京记》说东阁、西阁都是邺城宫寝便殿之名。《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集》曰:“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 ⑭。曹氏父子在邺下延揽文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这些文士参与政治,为曹氏出谋划策。东阁讲坛是作为太子的曹丕修习为君之道、治国之道的重要场所,因此是谈论多是事关政治的主题。如曹丕在东阁讲堂作《戒盈赋》,其序云“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乃作斯赋”,阐明了讲堂作赋的原由。其赋云:“何今日之延宾,君子纷其集庭。信临高而增惧,独处满而怀愁。愿群士之箴规,博纳我以良谋。” ⑮曹丕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取“箴规”,纳“良谋”。在建安七子的作品中,表现他们 “箴规”“良谋”并不多,刘桢《清虑赋》便是一篇,《清虑赋》全秩已不可见,俞绍初先生辑校部分曰:“结果阿之扶桑,接西雷乎烛龙。入镣碧之间,出水精之都。上青臒之山,蹈琳珉之途。玉树习叶,上楼金乌。错华玉以茨屋,骈雄黄以为墀。纷以瑶蕊,糅以玉夷……” ⑯由此可见,该赋词语华丽,风格铺张扬厉,应具“劝百讽一”汉赋之风。他们还有同题拟作,他们共同拟宋玉《好色赋》,曹植作《静思赋》,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玚作《正情赋》和之。⑰刘桢《清虑赋》题意也与讲堂赋诗相近,亦应为同作。
此外,李善注引《文选·颜特进侍宴》说曹丕于讲堂还作有《东阁诗》,惜仅存“高山吐庆云”一句。曹丕另有《善哉行》(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一诗,《初学记》卷十四引题作《于讲堂作诗》。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说王粲《公宴诗》、陈琳《宴会诗》、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和《公宴诗》、曹植《侍太子坐》等诗篇均作于东阁讲堂。” ⑱讲堂唱和也成为邺下文学盛会中的重要内容。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天降疫病,民有凋伤”,“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噎,或覆族而丧”,王粲、刘桢、陈琳、应玚、徐干等人也因瘟疫相继去世,创作的主力军烟消云散,又因曹操选定继承人立曹丕为魏王太子,二曹夺嫡多年,邺下文人集团创作交流的环境不复存在,二祖陈王与七子持续六年多创作高潮走向了衰落。
综言之,邺下文人的交游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在交游中他们通过同题拟作或“命题作文”,使诗文创作主题趋同。尽管邺下文人集团具有明显的政治取向,但是他们的创作还是体现了时代性的特征,如南皮、西园之游而产生的寄托幽思、抒发情志的宴游之作,这些作品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现实主义因素,体现了邺下文人以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进而思考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因此,这些作品充实了建安文学的内涵,使之具有“风骨”。
注释:
①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附《曹植年谱》,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26页。
②其中陆侃如先生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古文学系年》认为邺下文人文学活动始于建安元年(196年)。
③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3页。
④(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7页。
⑤⑥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6-67页。
⑦⑧⑨周建江辑校:《三国两晋十六国诗文纪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
⑩俞绍初:《“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读<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文学遗产》2007年05期。
⑪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2页。
⑫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72-73页。
⑬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2-173页。
⑭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頁。
⑮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7页。
⑯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4-205页。
⑰(宋)王楙著、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9页。
⑱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 第439页。
作者简介:
谢其泉,男,汉族,河南信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