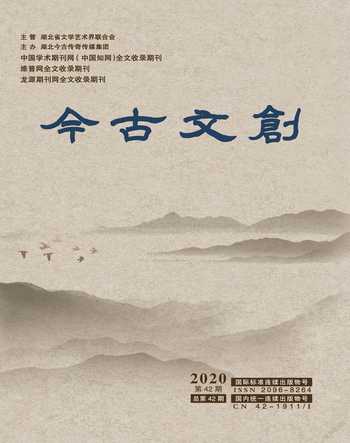谎言遮蔽下的澳大利亚民族创伤
【摘要】从立国之初的“自由定居者殖民地”到纪念一战加里波利登陆的“澳新军团日”,及至二战中死亡铁路集中营“邓洛普千人团”的神话,澳大利亚主流话语擅长编织谎言来规避民族创伤,获得某种暂时的安慰。当今澳大利亚文学界,“白澳神话”下的流放和殖民的创伤已经得到了一部分作家的关注,但是战争的创伤尤其是二战的创伤依然书写者寥寥。由此可见,澳大利亚的民族创伤从抑郁走向悲悼及至最终康复依旧长路漫漫。
【关键词】澳大利亚;创伤;谎言;战争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2-0023-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澳大利亚作家群二战创伤书写研究”(18WWD003)的阶段性成果。
澳大利亚对本国的历史有着一种奇怪的认知。1988年全国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纪念1788年英国运囚船队首次登陆悉尼。这就是澳洲国庆日的由来,其时间节点不是1901年澳大利亚正式建国,而是纪念英帝国对澳洲的入侵。一战加里波利一役中,数万澳洲年轻人在英国将领的愚蠢指挥下,在土耳其盲目登陆,白白送命。这竟是后来澳洲的全国節日“澳新军团日”(Anzac Day)的由来。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2014年7月,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国会向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致辞:日本是国际一等公民……即使澳大利亚不认同日本二战期间的行为,也对日本人的战争技能和使命必达的荣誉感十分钦佩。此时离日本在二战中轰炸达尔文港只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究竟用什么可以解释这种比小说更魔幻的现实?施琪嘉在经典创伤文论《创伤与复原》中译本前言中认为:群体在创伤的处理上,一方面会极度自恋,对异己和其他族群极具排他性和侵略性,另一方面会极度自卑,妄自菲薄,对他国盲目崇拜,类似于鲁迅先生笔下阿Q的形象。(赫尔曼,2019:V)一部澳大利亚近代史就是一部创伤史,国家和个体都用谎言来规避创伤、自我神化以获得某种身份认同,面对弱势群体极度自恋,面对当年的加害者又极度自卑。这一点在澳大利亚作家的笔下可见一斑。
一、“自由定居者殖民地”的谎言
关于澳大利亚殖民(流放)时期的历史,马克·吐温曾不无夸张地说:“它读来不像历史,而像编造得最美丽的谎言。”(黄源深,2014:5)在“白澳政策”影响下的民族身份叙事中,白人的到来揭开了澳洲殖民史的第一页,也揭开了澳大利亚向欧洲启蒙思想开化的第一步。在随后的两百多年中,澳大利亚人依靠坚韧勤劳、乐观向上的“丛林友谊”,将这一块蛮荒落后的大陆开辟成人间天堂,使澳大利亚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实验成功的乌托邦。这个美丽的故事至今或隐或现地体现在澳大利亚主流话语中。
“自由定居者殖民地”的谎言主要表现在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从宗主国的视角看待澳大利亚,将殖民地的丛林、牧场、冒险等元素融合进小说,以供19世纪伦敦上流阶层茶余饭后的消遣。
较有代表性的有亨利·金斯利(Henry Kingsley)的《杰弗利·哈姆林的回忆》(The Recollections of Geoffry Hamlyn,1859)、马库斯·克拉克(Marcus Clarke)的《无期徒刑》(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1874)和罗尔夫·博尔特沃德(Rolf Boldrewood)的《武装行劫》(Robbery Under Arms,1888)。
这片土地上真正的苦难没有得到真实的体现。被迫来到澳大利亚的流放犯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戴着脚镣从事最繁重的无偿劳动,苦难深重的他们无力也无权为自己发声。土著在英帝国的殖民话语中被排除出人类的范畴,看作是与动物类似的野蛮人,他们更无从为自己发声。
这种境况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一部分作家意识到殖民和流放的创伤,并开始描绘这段历史才有所改善。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彼得·凯里(Peter Carey )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帕特里克·怀特《树叶圈》(The Fringe of Leaves, 1976)的女主人公埃伦·罗克斯伯格在沦为土著人的奴隶后,被一名叫杰克·钱斯的流放犯所救,并与之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基尼利的小说《招来云雀和英雄》(Bring Larks and Heroes, 1967)描写了在澳大利亚早期的殖民社会,主人公哈洛伦下士因不满流放制度对流放犯的压迫,最终加入了流放犯起义行列,后因被告密事发而被处以死刑。彼得·凯里逆写了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1860-1861),以其中的流放犯马格威奇为主人公创作了《杰克·迈格斯》 (Jack Maggs,1997),与另一部小说《“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2000)一起为流放犯翻案。作家弗拉纳根的小说《欲》(Wanting,2008)刻画了土著女孩玛蒂娜在被白人殖民者收养以后走向沉沦和毁灭的痛苦故事,隐喻着土著文明被白人殖民者屠杀和毁灭的历史创伤。
“1988年为庆祝反英两百周年而出版了一大批历史小说,有鼓励人们回顾历史、探究民族身份之意,尤其是鼓励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估对待女人、流放犯和土著人的历史,而这些内容都折射在文学作品中。”(彭青龙,2013:59)但与此同时,鼓吹“自由定居者殖民地”神话的话语从未消失,土著和流放犯创伤的言说和最终走向康复依旧是未竟的事业。
二、战争英雄主义叙述的谎言
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澳大利亚都积极地参与了。一战的“澳新军团日”二战“邓洛普千人团”战俘营的神话至今仍是澳大利亚民族心理创伤的安慰剂。
一战是澳大利亚追随母国英帝国去世界各地作战,希冀将带着历史原罪的流放犯的血液净化成为母国尽忠的英雄的血液。结果是加里波利登陆的惨败,数万澳大利亚年轻的生命并不被英帝国的指挥官所珍惜。
二戰则更为惨烈,澳大利亚被母国抛弃后直接面临着亚洲地理上的邻国日本的入侵。随着二战中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推进,日军飞机直接轰炸澳大利亚港口。最终二战的结束并不是由于澳大利亚本土的顽强抵抗,而是因为外界的支援,澳大利亚民族心理层面上对日本的谦卑依然存在。因此,澳前总理阿博特匪夷所思的言辞就可以理解。
与此相对照的是,澳大利亚自19世纪中期便不断掀起反华浪潮,用“白澳政策”排斥有色人种,排斥土著文化。华人劳工建设澳大利亚的贡献,二战中中国在正面的战场牵制了大部分日军南下的兵力的抗战,一同在澳大利亚主流话语中被抹杀了。
这两次大战在文学作品、理论专著上都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征。澳大利亚主流话语更愿意对此视而不见,用谎言来做安慰,建构一种战争英雄主义叙述,歌颂军人为国捐躯的重大意义,自我神化,即使面对最难以启齿的二战死亡铁路集中营,也塑造出了“邓洛普千人团”的神话。
伦纳德·曼(Leonard Mann)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创作了《穿盔甲的人》(Flesh in Armour,1932),将其中的人物吉姆·布朗特描写成了理想主义的英雄人物。退伍士兵汤姆·汉格福德(Tom Hungerford)二战后创作的《山脊与河流》(The Ridge and the River,1952)描写澳大利亚士兵在热带丛林中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最终成为平凡的英雄。泽维尔·赫伯特(Xavier Herbert)的迈尔斯·富兰克林奖获奖小说《可怜虫,我的国家》(Poor Fellow,My Country, 1975)第三部分以日军轰炸为描写对象,着力刻画了爱国主义。这种过于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描写有时还夹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不如此的话,似乎便无以告慰亡魂。卡莉·塔尔(Kali Tal)认为受害者面对无法接受的创伤会发展出三种策略:疾病化(medicalization)、消失(disappearance)和神话化(mythologization)。(Tal,1996:6)面对摧毁主体自我认知的创伤,受害者用一种英雄主义的叙述策略建构起高大全的神话形象,在谎言中聊以安慰,使主体免于崩溃。
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在试着戳破“英雄”“国家”“民族”等谎言的肥皂泡。基尼利的《惧怕》(The Fear,1965)中,主人公并没有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对日本的战机十分惧怕,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澳国内对涉及日本侵略的《惧怕》研究远逊于基尼利的著名小说《辛德勒的方舟》 (Schindler’s Ark,1982)。大卫·玛洛夫(David Malouf)创作的小说《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中,集中营的日本兵日复一日的摧残下,两名澳士兵俘虏通过彼此的友谊而存活。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参与编剧的电影《澳大利亚》真实再现了面对日军的轰炸,普通澳大利亚人四散奔逃,大农场主之间互相倾轧,发战争财。弗拉纳根的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2013)解构了“邓洛普千人团”战俘营的神话,集中营没有英雄,只有挣扎着活下来的可怜人。支撑着死亡铁路集中营战俘们的不是国家民族等“比肚子还要空”的观点,而是彼此之间的友谊。对二战中日本的入侵除了在一些小说和电影中有所涉及外,在主流话语中的表述不多,这表明了澳对战争创伤依然处于抑郁状态,离公开发声的哀悼为时尚早。
三、结语
虽然澳大利亚文学对立国之初的流放殖民之痛已有所触及,其主流依然是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笔下的丛林开拓者,是充满男性阳刚气息的“伙伴情谊”,这些是澳大利亚主流话语建构民族身份时所能接受的,历史创伤污点是主流社会急于抹去的。与其清醒地面对摧毁自我认知的创伤,国家和民族都倾向于谎言中规避创伤,从此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在怀特的代表作《沃斯》(Voss,1957)中,流放犯贾德是探险的唯一幸存者,他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和遭罪的时间足够长, 你不可能完全离开它。你的精神依然在那儿。”(White,1957:443)这暗含了怀特对澳辛辣评论,也可以看出近百年的民族创伤是澳大利亚无法否认的现实,它如毒瘤般潜伏在民族意识的深处,隐隐作痛。
澳大利亚主流意识形态对入侵国家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崇拜,而对难民、土著和其他亚洲邻国等异己族群表现出排他性和侵略性,尽管这些族群从未损害澳大利亚的利益,有的还对澳大利亚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种民族精神分裂症状可以用创伤理论来合理解释。自英帝国入侵后,澳大利亚2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创伤史,出于对民族身份正统性的焦虑,澳大利亚民族心理极度的自卑又极度的自大,他们面对给予自己创伤的加害者,无力进行反抗,因此下意识产生了一种“文化自卑”(cultural cringe);面对土著等较为弱小的群体时,又展示了内心深处的白人中心主义,认为自己是高等种族。谎言是以证伪的方式证明了创伤的存在,澳大利亚去殖民化、去创伤化的历程,远未结束。
参考文献:
[1]Patrick White. Voss [M].London: Penguin Books, 1957.
[2]Kali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3]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4]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5]彭青龙.澳大利亚现代文学与批评——与伊莉莎白·韦伯的访谈[J].当代外语研究,2013(02):57-60.
作者简介:
施云波,女,汉族,江苏常州人,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当代澳大利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