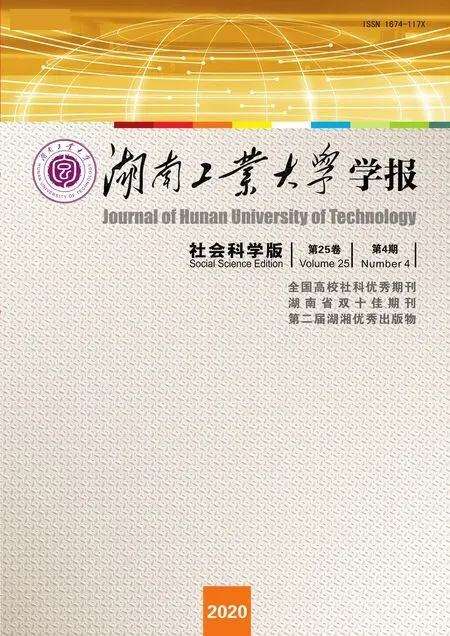社会实践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新视角
刘红华,刘毓容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一 研究背景
社会翻译学,又称翻译社会学,是指借用社会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翻译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一门学科,是翻译学的子学科。社会翻译学的概念最早是由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提出来的,并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迈克尔·卡龙(Michel Callon)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及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Theory of Social Systems)等社会学理论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主要有三个分支,即“行动者社会学”(sociology of agents)、“翻译过程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process)和“文化产品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cultural product)。
国内外译界学者对社会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学者仅借鉴一个社会学理论(如社会实践理论)对翻译进行研究,从而导致译者行为研究的片面性。如采用“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在分析译者行为时,可能将不属于译者的行为结果作为评价译者的参数,从而导致研究出现偏差。也有学者尝试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相结合来研究翻译现象,如2005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伊莲娜·布泽林(Hélène Buzelin)就已经提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翻译研究中的“意外盟友”(unexpected allies),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弥补社会实践理论的不足,并阐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社会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合理性。其后,国内外相关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证实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相结合,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更全面与客观的视角。但在结合这两个理论进行的翻译研究中,研究者或仅提出拉图尔和布迪厄结合的合理性,或仅借用两者的关键概念如“场域”“网络”“惯习”等来分析翻译现象,而鲜少有人深入剖析两者异同,也未见有人建构相关理论框架。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关注中观层面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关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社会实践理论相结合,寻求两者在翻译研究中的契合点,以拓展社会翻译学视角,同时构建这一新视角下的译者翻译行为研究框架,以期为更科学系统地研究译者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 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社会翻译学之局限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颇受译学界欢迎,其“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等核心概念经常被用以阐释翻译活动中的社会本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抛弃了近年来占据理论讨论中心舞台的另外两个二元对立,一个是结构与能动作用(structure and agency)的对立,另一个则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1]3。布迪厄将结构内化到个体之中,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彼此关联并相互强化。其核心概念“惯习”是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体现,其理论将对客观结构的分析扩展到了对主观性情的分析[1]13-14。
在具体的翻译研究中,场域用以解释惯习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资本用以分析译者在场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惯习用以解释译者行为的主客观合理性。译者拥有资本的多少决定译者在场域中地位的高低,进而决定其在翻译活动中自身惯习发挥作用的程度大小,在场域中形成的译者的惯习则主导着译者的翻译行为。布迪厄使用场域概念来界定塑造行为的各种因素,因此,对于研究影响行动者决策与行为的社会历史因素,场域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价值。
以往的翻译理论尤其是多元系统理论很少考虑翻译活动的个体因素,其呈现一种“去个体化”(depersonalized)的特征[2]。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则可以克服这一“去个体化”的缺陷,如通过分析翻译场域中行动者的地位和作用,将翻译中的行动者这一在多元系统理论中缺乏的元素纳入分析中来[3]203;通过考察译者的人生轨迹与译者个体的心智结构,即译者惯习[4-5],突破多元系统理论重语境而轻认知的局限。
基于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研究虽然克服了以往翻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基于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研究更关注译者在社会以及在翻译这一行业中的地位与作用,却很少涉及实际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参与者[3]214,以致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决定论”(deterministic)倾向,译者“永远被困在社会建构的自我当中”[5]261。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场域”概念界限模糊,令人难以把握和界定,给具体问题的分析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布迪厄并未给各种场域划定清晰的边界,他声称“文学或艺术场的主要争夺焦点之一就是对场域的边界的界定”[6]174。因此,学者们在借用这一概念时通常不知道如何划定每个场域的界限。比如说教育场域,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公司的培训、社区的公众教育、媒体节目上的知识学习等,这些能否归为教育场域之中?翻译活动是在文学场域还是在翻译场域内进行?翻译场域是否存在?如果翻译场域真的存在,它真的能够包含翻译活动中所参与行动者的关系空间吗?这些问题,在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社会翻译学中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
其二,“惯习”概念具有“决定论”倾向。布迪厄的“惯习”概念过于强调集体性对行为结果的决定性。正如他自己承认的,结构永久化的倾向已经被植入其社会化行为模式中,习性倾向于再生产那些与生产习性条件相一致的行为[6]95;社会行动者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正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1]222。由此可见,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结构决定行动者惯习,惯习又决定实践的行为方式,这就最终又落入了他自己所批判的“决定论”的俗套。于翻译而言,也就是又回到了翻译规范决定译者行为的原点,这样,译者个人的心智结果所作出的选择就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
其三,“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无法有效阐释非译者行为产生的结果。这一分析框架不能包含实际翻译过程中每位行动者具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如译者是否与他人合译,最后的译作是否由编辑修改定稿等,这些过程无法用“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来解释。
上述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局限,主要源于其对中观层面的忽视。译作生产场不仅包含宏观层面的翻译行业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更包含中观层面的翻译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而其场域无法涵盖后者,才导致翻译场域无法被清晰界定。“惯习”概念被认为具有决定性,也恰恰因为其关注了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心智结构,却未关注实际场景这一中观层面上惯习是如何对行为发生作用的。正是由于对翻译过程这一中观层面的忽视,“场域-资本-惯习”无法解释非译者行为产生的结果。
三 布迪厄与拉图尔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新视角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视角,其同时关注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可以为社会翻译学提供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及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关注个体的人生轨迹及其社会地位,认为个体的惯习是个体内化社会结构的结果,能预测个体的潜在行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并非拉图尔所提出,但其对该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学界也常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称行动者网络理论)则更倾向于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认为行动者的能动性是行动者与参与同一个活动中的其他行动者互动的结果,注重产品生产的过程。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惯习”这一概念可用以预测行动者的具体行为,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认为行动者的心理构造、行为目的都是无法预测的[7],只能在实际行动中去考察。布迪厄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心智结构,而拉图尔更关注这些结构在中观层面的具体行动中是如何对行为起作用的。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可以合理地解释译者行为背后的因素,即译者的惯习以及这种惯习形成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可通过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清晰呈现译者在其中的能动性,从而将译者并未参与的行为结果排除在评价译者能力与素养的证据之外,保证了译者评价的公允性。此外,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通过描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动性的程度大小,来探究社会、文化、历史、译者心理以及其他参与到翻译过程中的行动者对译者行为以及译作的具体影响程度。因此,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相结合,能同时关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一)中观“翻译网络”与宏观“翻译场域”相互补充
学界虽然对翻译场域和翻译网络进行了界定,却过于抽象与模糊。翻译场域是指各个国家的译者形成的关系空间,包括不同领域的译者群体(如文学译者、字幕译者、口译者等)、翻译社区以及翻译派别,是每个译者带着惯习与各种资本在权力争斗中逐渐形成的[8-9];翻译网络是指译作生产过程中行动者的关系空间[10-11]。如何准确理解“翻译场域”与“翻译网络”这两个概念,并在翻译研究中恰当运用,这是目前社会翻译学研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由于“场域”与“网络”两个概念界限模糊,笔者将在阐述“场域”与“网络”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之后,再对“翻译场域”与“翻译网络”这两个概念进行详细分析与再界定。
1.“场域”与“网络”
“场域”与“网络”这两个概念既有重叠之处,又相互补充。场域是行动者为了某种利益而角逐的场所,强调竞争关系;网络则是共同完成一个任务的行动者的关系总和,强调合作关系。这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如下:
(1)场域与网络都指涉一个特定的虚拟空间,但两者分别指向两个不同维度的关系空间。
场域是生产同一类产品的个人或机构之间竞争的空间,如各位作者或出版机构在文学场域中生成文学作品,各个大学在大学场域中培养大学生或出版学术作品。文学场域还可以划分为小说或戏剧等子场域[1]142,即创作小说或戏剧的作者或出版社之间构成的客观关系空间;知识分子场域用以指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空间;艺术场域是指艺术家之间的关系空间;哲学场域是指哲学家之间的关系空间[1]145。由此类推,翻译场域当然应该指译者(包括翻译机构)之间的关系空间,而非译者与作者、编辑等之间的关系空间。
网络的构建包括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引起兴趣(interestement)、招募成员或成员注册(enrolment)和动员(mobilization)等四个步骤,其指涉为完成同一个任务将不同能力的人和物集中在一起的一个关系空间,如一次物理实验所涉及的实验员、实验器具、记录员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由此类推,翻译网络则是指为完成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原文、作者、译者、编辑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翻译网络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微观的翻译网络是指完成一次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行动者的关系空间,如一部作品翻译所涉及的译者、编辑、赞助人等组成的关系空间;宏观的翻译网络是指完成翻译这项活动所涉及的行动者的关系空间,如一个翻译机构的编辑、译者等组成的关系空间。用拉图尔的话说,网络就是“行动的空间”,即一次或一种行动所涉及的行动者共同组成的空间。网络既包含在场域之中,是场域中的一次行动始末所涉及的行动者关系的总和,相当于场域中个人或机构工作的关系场所,又延伸到场域之外与其他场域产生互动。
(2)场域与网络都关注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但两者关注的是不同维度下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
场域关注的是行动者在整个领域中(如文学、经济等领域)而非某一次具体行动中的角色与地位,网络则注重行动者在某一次具体行动中的角色与地位。以下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角色与地位为例,来说明行动者在场域与网络中的角色与地位差异。在翻译场域中,杨宪益、戴乃迭是资深翻译家,在翻译这一行业享有盛誉,拥有较高的象征资本;在翻译网络中,他们的角色与地位则依靠实际行动者的数量以及占主导行动者的性质而定,如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就是杨宪益为主,而戴乃迭负责润色。
对场域中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进行分析,有助于推测行动者的行为倾向;对网络中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进行分析,则可以确定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做过什么,没有做什么,能更客观地分析其行为及结果。场域分析的行动者的地位与作用虽能合理解释译者行为,但在无法确定哪些是译者行为的情况下,其解释有些缺乏依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哪些阶段没有发挥能动性,哪些阶段发挥了能动性以及发挥了多大的能动性,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对翻译网络中的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进行分析。例如,译学界大都认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的书名All Men are Brothers 是译者本人所为,但有证据显示,这一英文书名的敲定是出版社所为[12]。若赛珍珠《水浒传》英译书名是出版社所为这一事实确认无误,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一书名来评价赛珍珠的翻译行为。
(3)场域与网络都注重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但场域关注竞争关系,而网络更注重合作关系。
场域中的行动者带着各自的资本与其他行动者竞争以获得更高的地位,而网络中的行动者会为了完成同一个任务而共同合作,可能在行动过程中也会意见相左,但最后会协调解决,向共同的目标迈进。
2.“翻译场域”与“翻译网络”
“场域”与“网络”这两个概念指代翻译这一领域的两种关系空间,它们的相互补充解决了译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布迪厄场域概念下的翻译场域是否存在的问题。对此,译界大部分学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即认为不存在或很难界定翻译场域。其理由是:翻译活动跨越不同的场域[13];翻译场域内嵌在或者从属于文学场域中[8]10;翻译活动具有多变性,行动者以及行动者所追求的利益都可能随着翻译活动的变更而发生变化[14]111;翻译这一职业并未完全规范化,从事翻译活动的人不管其翻译水平高低,都可以称自己为译者,而且大部分人只把翻译当成自己的第二职业[14]112。
翻译活动既跨越不同场域,又具有多变性,这一特征具体表现在每次翻译活动过程当中。这实际上也是“场域”理论无法分析的问题,因为“场域”只关注宏观的某一行业的个体或机构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问题可以用拉图尔的“网络”概念进行合理的解释。“网络”的存在就是为了分析每个参与到具体活动中的行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沃尔夫等人所述的翻译场域其实可以翻译网络代之。网络中的行动者更多的是一种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相互关联。仅仅关注翻译的每个具体活动却无法确定译者在整个翻译行业中的地位,这显然不能全面分析译者的翻译惯习。这时就需要借助于布迪厄的“场域”这一概念。由此可见,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的翻译场域确实还是存在的,只是无法包含具体翻译活动中的行动者的关系。
综上,翻译场域是指译者(此处的译者并非仅指译者个人,还包括出版社、代理人等与译者组成的团体)之间的关系空间。它主要是指同一类产品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用于分析某次具体的翻译活动,却能在宏观上分析译者在整个翻译这一行业中的角色与地位。翻译场域中的行动者与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如译者与译者之间在译作的质量与传播效果上进行竞争,译作质量高、传播效果佳的译者可以获得更好的象征资本。翻译网络是指具体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译者、编辑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它不能在宏观上预测译者在整个翻译行业中的地位与作用,却能确定译者在具体翻译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翻译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为完成同一部译作而相互合作与妥协。翻译场域呈现整个翻译行业的规律,翻译网络则展现具体翻译活动中的实际情况。翻译场域的存在是为了分析译者行为的倾向性及其成因,翻译网络的存在则是为了分析译者行为的差异性及其成因。翻译网络的出现验证了翻译场域存在的可能。
(二)“译者的能动性”弥补“译者的惯习”之“决定论”局限
与布迪厄相似,拉图尔也强调行动者,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行动者”概念范围大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行动者”概念,其包括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拉图尔强调“跟随行动者”,记录其在每个活动中的具体表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实地描述翻译过程中各个行动者(译者、翻译机构、委托人等)的地位与角色,更清晰地界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其使得通过出版的译作评价译者的能力与态度更具公平性。如葛浩文《天堂蒜薹之歌》英译中增加结尾的情况,如果研究者不去追踪这一具体翻译过程,显然会认为葛浩文不顾原作,随意添加结尾,不忠实于原作;但实际上,译文中这一结尾的添加却是三个行动者共同参与的结果,而且译者葛浩文并非起主导作用的行动者。葛浩文在一次采访中揭示了这一结尾添加的前因后果:出版社不喜欢《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于是葛浩文联系作者莫言说明此意,莫言应出版社要求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结尾,葛浩文负责将这个新的结尾翻译出来[15]。除此之外,翻译活动中的译材选择行为也有可能并非译者所为。这些不确定性都需要通过对翻译过程进行追踪,确定译者的能动性之后才能得知,追踪的结果决定了能否通过翻译选材、最终出版的译作等评价译者的行为。由此可见,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翻译研究中借鉴“惯习”概念所致的“决定论”缺陷。
(三)趋向“行动者-翻译过程”研究模式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各有千秋,相互补充,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翻译,确如布泽林所述,能够克服多元系统理论中存在的局限。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结合,能够使翻译研究迈向面向行动者与过程的研究模式[3]195。译者的惯习为其在翻译活动中的各种行为提供合理的依据,这些依据包括译者的个体意识、内化于译者自身的社会性、译者翻译活动发生之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等。译者在翻译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译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则为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动性的发挥程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为探究影响各种因素对译者翻译惯习的具体影响提供了事实依据。如果说布迪厄的“惯习”这一概念涉及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与社会性,那么拉图尔的“网络”与“行动者”这两个概念则考虑到了具体翻译过程中各种因素对译者行为的作用程度,两者的结合能更具体、更全面、更系统地阐释译者行为。
布迪厄的“行动者”(agent)只包含人类,而拉图尔将“行动者”(actant)扩大到了人类和非人类,认为在行动中“起作用”的人和物都具有能动性[16]。通过借用包含了人类与非人类的拉图尔的“行动者”概念,可以将译者、作者、读者、赞助人等人类因素与翻译规范、意识形态等非人类因素都包含在分析当中。因此,翻译网络中的行动者就可以指对最终译作“起作用”的所有人和物。
由于“惯习”这一概念的加入,“行动者”概念又不同于拉图尔所述的“行动者”概念,本研究中的“行动者”是指独立于每个行动者之外的人和物,还包含每个行动者本身的个人惯习,即这些行动者的社会化的主观性。为方便分析,可以将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行动者作一个细微的区分:将主流意识形态、主导诗学、主流翻译规范等称为宏观行动者;将直接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来的行动者称为中观行动者,如中文编辑、译者、定稿人等;将译者这一中观行动者本身所具有的个人惯习(包括身体化资本)称为微观行动者。宏观行动者通过中观行动者间接影响译者的行为,微观行动者直接影响译者的行为,中观行动者则进一步加强宏观行动者对译者行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情况下,除译者之外的中观行动者不通过译者对最终译作产生直接作用。
四 译者翻译行为研究理论框架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笔者结合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译者翻译行为研究理论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译者翻译行为研究理论框架
图1 呈现了对译者翻译行为进行分析的两个主要步骤:
首先,通过分析微观行动者、宏观行动者与中观行动者在翻译网络中对译者的影响,来确定译者的具体能动性。由于中观行动者可以直接对译作产生影响,因此,在通过最终译作分析译者的行为之前,需剔除中观行动者对译作的行为结果。在分析微观行动者时,要注意其本身的变化,即每个网络中译者的个人惯习具有一定的差异。前一个网络中的译者的翻译惯习与译者的初始个人惯习又共同形成译者的个人惯习,作为微观行动者对后一个网络中译者的翻译惯习产生影响。
然后,通过译作中译者的行为结果(非译者的行为结果已经在第一步中被排除)来分析译者的翻译惯习,包括恒定性翻译惯习与差异性翻译惯习。恒定性翻译惯习是指译者在整个翻译生涯中所表现出的性情倾向的一致性,主要由译者个人初始惯习的影响所致;差异性翻译惯习是指译者在翻译生涯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性情倾向的差异性,主要由不同行动者对译者不同程度的影响所致。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的具体研究思路如下:
(1)将译者的翻译活动划分为不同的翻译网络。翻译网络的划分视译者在具体翻译活动中的能动性而定。通过查询记述译者翻译活动的相关史料,来追溯译者在每个翻译网络中的具体角色与地位,并最终确定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包括翻译选材、翻译、定稿等)中的能动性。在分析过程中,应将译者并未发挥能动性而产生的翻译结果排除在分析译者翻译行为的证据之外。此外,在确定参与每个翻译网络中微观行动者、宏观行动者以及中观行动者的地位与作用,在考察行动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的影响程度的同时,确定每个翻译网络中的主导行动者,并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
(2)探究译者的翻译行为及其成因。通过译者译作中所显示的译者的行为结果,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进行深入探究。总结出译者在每个翻译网络中所表现出的恒定性翻译行为,并探究译者在不同翻译网络中所表现出的翻译行为的差异性。结合第一步的分析结果,探究译者的恒定性翻译行为与差异性翻译行为的深层成因,为译者翻译行为的合理性提供解释。概括而言,译者的翻译行为是译者的惯习以及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其他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行动者都无法对译者的行为起决定性作用,行动者对译者行为的具体影响程度要通过将他们置于特定的翻译场景中加以考察才能得知。
本文论述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在翻译研究中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以寻求社会翻译学新视角,并基于这一新视角,构建译者翻译行为研究理论框架,其对译者研究具有如下启示:
其一,将译作中的非译者行为结果排除在评价译者的行为之外,以给予译者更公允的评价。比如在译者手稿难觅的情况下,学者们可以“跟随行动者”,追踪整个具体的翻译过程,尽量厘清各个行动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其对最后的翻译产品(译作)的作用程度。重点确定译者在翻译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能动性,将其他行动者对译作的直接影响排除在外。
其二,在分析译者行为时,应将译者置于某个具体的翻译网络中,综合考察这一翻译网络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译者、编辑、原文本、作者等各个行动者对译者行为的共同影响,全面探究影响译者行为的各种因素。具体而言,由于译者个人、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等任何单一因素都无法对译者行为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对译者行为的成因进行考察时,应综合考虑历史因素、个体认知因素、翻译活动发生时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直接参与到翻译过程中的人与物等多种因素对译者行为的共同影响,以更客观更全面地解释译者行为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