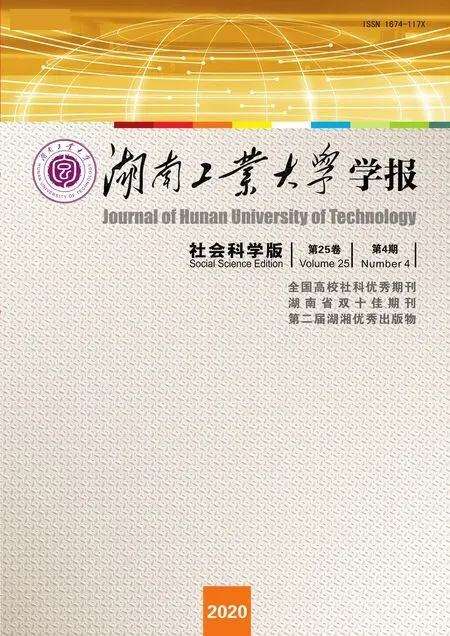声音符号与时代命运、个体情感的共振
——电影《八月》声音叙事探析
徐广飞,胡 琴
(1.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2.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文本质量提升明显,一些电影在声音叙事方面的探索引人瞩目。2016年,影片《八月》作为一匹艺术电影黑马,以其独特的声音符号体系(人声、音响、音乐)引起了学界对于电影声音叙事美学的再聚焦。我们深入考察电影《八月》的声音系统,不难发现,该片不仅对声音符号进行了系统化的“输出”,成功编码了国企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秩序,还给观影者设置了沉浸式的听觉体验,引发了受众关于1990 年代文化记忆的共鸣。
弗朗索瓦·若斯特(Francois Jost) 在《什么是电影叙事学》(Narration and monstration in the cinema)中指出,非视觉手段更能完整地映射出电影叙事的可能性,而影像外加的声音能决定视觉聚焦的价值。据此,我们得以窥见声音叙事之于影像文本的重要作用。“根据具体的情境,声音对于人物和观众都有特定的涵义,当声音超出机械感觉和信号功能之外,搅动我们情绪和思想时,会被当做一种符号。在这类声音时间的作用下,一种意义或回声在心灵的更深处响起,声音符号从我们的环境背景当中发展成为文化的、具体的声音。”[1]168-173此种文化的、具体的声音恰恰与《八月》中的声音体系的功能相契合。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以《八月》为代表的电影声音叙事所呈现出的新面貌,打破了大众对音乐、音响单纯地作为环境背景音的刻板印象,深化了声音作为影像内推力、文化传递者的符号塑造。因而,由“声音叙事”维度切入电影《八月》,以“听点”即“影视声音创作所预设的倾听角色”为核心,解码声音符号在个体情感渲染与时代情感认同中的隐喻效果,能够成为我们管窥新世纪以来电影声音叙事理论体系发展的一个有效端口。
一 音响色调与文化记忆的缀合
《八月》中影像声音叙事体系的音响色调包括了以片中人物为听点的影片环境音及影像中的影像——复调影像,其整体基调是温婉、从容的。或许,导演意在寻求以积极的方式,让时代之下的社会群体从时代转型后的文化创伤中解脱出来,并重塑他们的文化身份与精神价值。
(一)影像环境音变化:文化转轨的指涉
“所有的文化秩序都是特定的和相对的,新旧文化秩序之间常面临阵痛的转轨。张大磊以其《八月》呈现了一个反例,他以回忆的方式去再现1990 年代并致敬父辈,实际上是以一种柔和的姿态帮助旧文化秩序进行转轨。”[2]28-32影片《八月》对1990 年代音响的挪用与还原,使得社会文化秩序转轨的影像表达有趣而和谐。相异于同类型影片在追溯时代记忆时所着力强调的苍凉感,《八月》不再是一首悲戚的时代挽歌。其舒缓平和的音响色调使缀合于影像中的文化记忆变得明朗、开阔,而常规的“暴烈式”变革——文化秩序转轨在平静的“生活协奏曲”下也变得悠扬婉转。影片中涵盖自然环境音响和社会环境音响的背景声,不仅充斥着画内,还延伸至画外,对社会文化秩序的转轨构成了无意识聚焦。
影片中支配观众注意力的方式分为几个层级,这几个层级的划分建立在格式塔原理之上,属层层递进式。其中,最高层级是指“我们不会注意到,但是组成所创造的电影世界并能够影响我们潜意识的背景声音”[3]。片中,小雷生活的大院内阳光明媚,蝉鸣鸟叫,风吹树叶沙沙作响,间或有几声慵懒的猫叫,电视机里的雪花噪声、卧室闹钟滴答声与厨房水龙头漏水声、小孩的打闹声、邻居间的窃窃私语、大叔清脆响亮的练歌声、院落小道上的磨刀声,等等,交织在一起。这些“我们不会注意到”、极易被忽视但却又真切存在的有声源环境音浸润着浓厚的烟火气息,描绘了一个充满着人情味的世界。这是生活,也是国企改革前最后的“狂欢”。然而,自从小雷在姥姥家树下低声浅唱《祝你平安》后,大院相继发生了各种变故。暴风骤雨天气影像所萌生的纯粹的有源环境音响充斥着画内画外,院子由此陷入了“沉寂”。这里,自然环境音响的变化预示着时代秩序更迭的逼近,国企改革前小城里自然环境音的“躁郁不安”与父辈们失业后的愤懑遥相呼应。
如果说自然环境音响是文化记忆的承载体与见证者,那么,电影文本中的社会环境音响则无情地还原了1990 年代文化秩序裂变的发生。影片序幕,声音先行的画外环境音“你是警官,我还是罗马教皇呢”,将观众拉入时代情境的延展和想象中。这句源自1990 年代动画《大盗贼》中的台词,既是对小雷“小升初”后悠闲暑假与个体蒙昧的真实写照,又是对导演欢乐明媚的童年时代的复归与重述,同时也是对社会变革前小院温存时光的追忆与缅怀。随后,当小商贩“夏天最后一茬了,卖瓜啦”的吆喝声敲响夏天将逝的警钟并开启时代变更的前奏后,离别的苦味与未知的恐慌便渐次代置了小院里温存的欢乐与和谐。电视机中首次以“国家现在对于中小型的企业就是采取抓大放小的政策……”的环境音响正式宣告了国企改革的开始,其意味着计划与市场的分轨、个人与集体的告离。对于电视机传递的这一信息,影片设置为由小雷同姥爷“一老一小”来接收。虽然镜头停留的时间十分短暂,但其极为巧妙地淡化了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可以说,多元化环境音响的声音技巧,营造出了泛生活化的社会小环境,让一场社会变革被多维度、多方面地刻绘与呈现出来。在此,影片既没有直白的时代更迭话语表述,也没有生硬的旁白介入,但“变”这一元素却始终浸透于音响色调与影像生活展演的一点一滴中。
(二)复调影像环境音更迭:社会变革的喻示
影片《八月》挪用了部分1990 年代国内外的影视资料,如《篱笆·女人和狗》《爷俩开歌厅》《遭遇激情》等,构成了“影像中的影像”即复调影像。《八月》对此种复调影像的模仿/征用形成了一种互文效果,“一方面充实了影片文本的声音体系、扩大了电影的叙事容量,另一方面,其镜像形式及内容的变化同片中的社会变革以及父辈们失业下岗的变故关涉,又使电影文本具备了多种阐释的可能。”[4]
影片序幕,小雷一家三口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的《篱笆·女人和狗》是1990 年代初的一部情感悲剧。由“复调影像”本身及其延伸的枣花的隐隐哭声,小雷父母对剧中主人公枣花悲苦命运的感叹,小雷对吃苦菜的抱怨,母亲对小雷吃苦菜的劝诫,皆潜藏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于是,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之下,社会变革初见端倪,家庭生活的变故也尾随而来。
《爷俩开歌厅》是影片中出现的第二部影视作品,“这是1992 年陈佩斯自导自演的‘二子’系列电影的一部,而陈佩斯正是中国最早吃螃蟹的‘电影个体户’,砸碎了旧电影厂的体制,这与《八月》的内蒙电影制片厂改制巧妙地联系在一起。”[2]30此时的社会变革尚处于酝酿阶段,小雷进出电影院毫无阻碍,电影院影片放映时的同步环境音,也使其产生了一种置身于安全“堡垒”中的假象。但自从小雷与伙伴们在电影院遭遇三哥等人的“驱逐”而被迫“出境”后,其主体位置迅速转变,小雷的眼泪成为了这“山雨欲来风满楼”改革趋势的隐喻,只不过此处声画分离的影像处理柔和了“变革”的暴力性。小雷的身份转变照应着其父亲的地位变化,变革的绝对话语权在人物的失语中被渐次放大。
《遭遇激情》是小雷和父亲能够通过“走后门”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影片讲述的是男主用自然真诚的情感温暖了一个濒死少女的故事。其中,女主“我觉得闷得慌,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想和你聊聊天……”的独白与小雷父亲内心的悲荒、无奈、迷茫互成指涉。而就在这“最后一次”观影的过程中,小雷父亲“凭本事吃饭”与“绝不低下高贵的头颅”的自我警语和生活态度,在影院的镜像中得以复现。父亲默默地擦拭着眼泪,在暗室中将压抑许久的情绪进行自我消解。导演将父亲无法言说的心酸寄予《遭遇激情》的镜像世界,意在阐明:社会变革是必然趋势,其将导致小雷、母亲与父亲的别离。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变革即将到来的时刻,他们一家更需要学会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语境,必须接受“离散即将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的这一事实。
此外,《出租车司机》《亡命天涯》这两部外国电影文本,对影片内涵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出租车司机》在影片中共出现三次,与作为剪辑师的小雷父亲有着深刻的渊源。影片中以频繁出现的画外台词“你小子想跟我作对?”为引子,一方面触发了父辈心中对体制的愤懑不平与无声的反抗;另一方面则搁置了“集体”与“个体”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和睦相安”,进一步凸显了二者不可规避的抗衡。这里,新时代艺术创作的主流理念——“唯金钱至上”(以韩胖子为例)发起了对“为艺术而艺术”(以小雷父亲为例)主张的深入挑战。当《出租车司机》的录像带被暴力摧毁,也正暗示着社会的革变无情地推移了小雷父亲“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的主体位置标注,而《亡命天涯》影像资料则将“旧体制被打破”这一消息赤裸裸地公之于众。影片放映前的宣传环境音——“进口大片……火爆刺激,改革年代,激烈论争,电影市场,风险上映……”无疑是给仍旧固守“集体信仰”父辈们的“善意”忠告。作为第一部以分账方式在中国上映的好莱坞影片,《亡命天涯》的意义不仅在于从此将小雷和父亲无情地隔绝在电影院外,更是代表着在这一标志性的时代节点过后,社会变革所裹挟的商业大潮在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怦然而至。
二 无声源音乐与个体情绪的互引
“当我们与周围事物的震动和波动有共鸣的反应时,我们的生理功能可能会受到声音冲击的影响,包括我们体内的消化活动、肺的呼吸、心脏跳动,以及大脑中神经元的快速反应”[1]85,这种现象被称为声音的互引。声音的互引不仅作用于生理,还会造成心理侵扰,构成神经互引效应。在影像创作的过程中,剧中人物、观众及创作者的情绪反馈则是这一现象的外显形式。《八月》中声音元素的互引效应主要体现在无声源音乐符号的叙事描白及抒情修饰技巧上,叙事的现实感知同抒情的虚幻臆想牵引着个体情感。
弗朗索瓦·若斯特在《什么是电影叙事学》中,对应三种视觉聚焦,总结出了三种听觉聚焦类型,其基于叙事学的听点与听觉聚焦的对应关系如表1[5]154所示。

表1 听觉聚焦与听点的对应关系
无声源音乐符号大多以标题性音乐形式存在,属于“画外音”,此音乐类型对于影片中人物角色来说处于缺席状态。因此,基于弗朗索瓦·若斯特的电影叙事学观点,笔者对影片中语言、无声源音乐符号与个体情感的互引的探讨将以零听觉聚焦、原生内听觉聚焦为主线,尝试从客观、指向两种形态对影片中具有代表性的无声源音乐的隐喻、注释等功能进行剖析。
(一)零听觉聚焦:观众的情感认同
“零听觉聚焦是一种‘全知听点’,听觉信息经过滤被观众接受,即以观众为核心,主要以达到观众情感认同为目的。”[6]或需赘言的是,观众作为负载“全知听点”的对象,虽然在观看影片时能以上帝视角摄取所有的声音信息,但本文选取的只是专门针对观众而设计的无声源音乐。《八月》中围绕主线人物小雷的无声源音乐是拉威尔(Maurice Ravel)的《引子与快板弦乐四重奏》(Introduction et Allegro)和德彪西(Achille-Claude Debussy)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Fille aue cheveux de lin)。这些“印象风格”的音乐不论是对观众还是剧中人物的角色身体、精神以及情感设定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感情、梦幻影像、白日梦”[1]50三个方面。由这两首无声源音乐所塑造的影像世界——《八月》也相应地呈现出“印象风格”的审美效果。
拉威尔的《引子与快板弦乐四重奏》这一标题性音乐围绕小雷视点共出现了三次。这三处集中采用了竖琴段落最密集的部分,并通过节奏、语言、情绪内容速度的渐进变化,与观众达成稳定的互引效应,实现他者的情绪感知由梦中虚幻的“此在”向炎炎夏日真实的“存在”跳转。(1)在小雷的梦中,音乐引领观者穿过一片荒芜,而后转至小河边同一群大人围观杀羊。此时,音乐由拉威尔转向德彪西,梦中无意识的承接动作匹合了纯朴、温柔、朦胧在幻境之中的“亚麻色头发少女”的浪漫意象,而这一美好少女正是催生小雷懵懂性意识生发的邻家姐姐。当“懵懂的性”徘徊、游荡在印象音乐中,《引子与快板弦乐四重奏》以“短呼吸式”接过梦幻的镜像,并在真实/现实的床帏边让小雷/观者“恍然惊醒”。(2)在午后的院子里,小雷仰望母亲水浇昙花,惬意交谈的老人三俩成群,葡萄树下投落的影子在摇椅上游动,饱满欲坠的葡萄连同夏日百无聊赖的躁动皆被《引子与快板弦乐四重奏》穿起、曝晒在亦真亦幻的生活中。(3)雨夜,三哥在雷声与警笛声交织的巷子里奔逃、反抗,直至被抓。在略显荒诞与扭曲的音乐中,小雷孩提时代依附暴力的幻想、崇拜被一笔勾销。
影片中的黑白色调加上印象派音乐使现实如梦似幻,这是小雷作为旁观者的记忆碎片,也是导演张大磊通过音乐向观众传达的情感体验。梦境与梦幻般存在的现实交织并行,同视觉形象紧密结合。“单簧管演奏的主旋律,竖琴的琶音在长笛和弦乐四重奏的映衬下形成斑驳梦幻的色彩。”[7]朦胧梦幻的曲风着实让人“费解”与迷惑,但正是由于印象派音乐的特质才使得电影文本携带大量回望现实但又置身梦境的幻觉。因此,当“迷离扑朔”的音乐将影片视点聚焦于孩童世界,观影者同样暂别了成人/成长繁杂与忧愁,并被影像文本直接带回到1990 年代。可以说,此种由无声源音乐牵引的影像逻辑和情感体验,恰到好处地完成了“零听觉”现实与梦境的交叉式对接。
如果说印象派音乐让影片过于先锋,那么,选自音乐家凯特·毕卓斯坦(Ketil Bjornstad)的作品Pianology7 则实现了电影文本情绪逻辑的常规倒置,即由“虚空”到“现实”的回落。Pianology7 是小雷大舅母向姥姥道歉时出现的音乐,属于北欧爵士乐,钢琴独奏,细腻多情,蕴含着神秘而难以琢磨的庞大能量。小雷的大舅妈与姥姥有着多年未解的情感隔阂,但经时光的打磨,两人最终和解。全家人在影片即将落幕时照了一张“集体照”,但小雷父亲的缺席让观众感受到了定格照片中人物角色微笑后的些许失落。曲子一直持续到出现小雷推着自行车上学时的背影,其同之前坐在父亲自行车上的场景形成对比。这个八月就这么带着几分落寞过去了,而导演张大磊的童年回忆也终于落地。
(二)原生内听觉聚焦:创作者的情感克制
“原生内听觉聚焦是指不拥有主动倾听的标志,不易被观众知道是否经过某人物耳朵过滤的特殊处理,但能将不可见的叙事机制表达出来。”[8]《八月》导演张大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部影片倾注了较多的私人体验,但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有意抑制了自己的情感。因此,在描绘1990 年代社会的美好状貌时,创作者的声音设计主动规避和筛除了时代转型模式里的社会危机,以及因人际情感闭塞和社会动荡造成的戾气。换言之,以原生内听觉聚焦为核心的无声源音乐选取,暗合了创作者/导演克制的情感空间铺展以及厂区文化的投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影片尾声主动介入了灵动的转引音乐《青青的野葡萄》——引自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并串联起由消色转彩色的过渡影像。音乐逻辑的凸显和创作者自身情感的喷涌,在逼近结局的影像序列中被潜抑和柔化。因此,“虽然电影中的角色有苦闷有无奈有不甘,但创作者本身的受害者意识消失了,一种功利化的情绪诉求也就消失了。没有了或歌颂或反叛或其他压力下所表现出的刻意,我们终于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5]153。影片借着“青青的野葡萄,蛋黄的小月亮……在那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温暖、灵气的歌词传递,先在地重述了创作者记忆中青春和生命的时光样貌,表达了对父辈们能够转岗成功的深切祝福。至此,我们也得以见证,影片以原生内听觉聚焦为核心的无声源音乐与创作者的情感克制等值对位、呼应。
三 有声源音乐、人声与时代情感的指涉
有声源音乐是指“音乐的原始声源出现在画面所表现的事件内容之中,使得观众在听到音乐声的同时也能看到声源的存在”[9],“它不仅支持银幕上真实的画面,还让我们感受到看不见的和听不到的、所表现人物的精神过程和情感过程”[10]。《八月》以1990 年代初为时代背景,有声源音乐的选取集中于1990 年至1995 年之间,其情感指涉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美国小提琴演奏大师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曾表示:“音乐从混乱中创造秩序,因为节奏可以使分歧变为一致,旋律可以使断裂变为连续,和声可以使不和谐变为和谐。”[1]88我们不仅会对作品所揭示、持续不变的、深层关系的美好情感做出反应,同时也会对我们感知音乐的事实本身进行反省。《八月》中有声源音乐的处理,让处于断裂的年代凝聚了更深的时代情感,其关涉的不仅仅是个人情感,更携带着共性的集体情感。
(一)以“母亲”与“故土”意象为主的有声源音乐:无奈与迷茫
影片中的无奈与迷茫是专属于父辈们的集体情感,同时也是导演着重表达的时代情感。影片中部分有声源音乐的引用是对因国企裁员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以及从熟悉的土地抽离出来而身份迷失的父辈群像的情感渲染。影片通过有源音乐的共享,勾勒出了1990 年代独有的怀旧想象与记忆。其中,有声源音乐的引用尤以“母亲”和“故土”意象为重点。比如,游泳馆播放的《白发亲娘》,“情感表现较为婉转、含蓄,有一种娓娓道来之感,歌词描绘的栩栩如生,让观众听到歌曲眼前就浮现了母亲等候儿女的孤独的背影的画面。”[11]音乐响起时,生活的往常规律与小雷父亲“铁饭碗”的在岗意识逐渐告离,淡淡的悲情意识弥合了音乐声响中传达的个体遭遇集体的身份弃置,即“母亲”意象的叙述语调与风格,成为父辈的身份抽离直至迷失的警示和先兆。
以“母亲”意象为主的有声源音乐第二次出现,是小雷父亲和朋友们在家中吃散伙饭的时刻。这是一首离别序曲。恼于变故,《母亲》诱发了他们依恋故土不愿离开的愁苦心情。这首低沉有力的歌曲出自以草原、母亲和故乡为永恒创作主题的腾格尔之手,男声的遒劲与柔情磨合共生,对故土有多迷狂,即将别离的心就有多焦虑与沉重。电影文本借重歌曲情感与厂区文化历史表述的差异性,间或放逐了父辈对故乡母亲留恋之情的功能化固置。此外,创作者还检视文化空间中父辈的“流氓性”。朱大可于1994 年发表了《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他以‘精神分析’的方式梳理了‘流氓’的历史谱系:第一代是丧地者, 第二代是丧国者, 第三代是丧本者。”[12]父辈在改革年代很快就要沦落为时代的“流氓”。厂区/土地面临消失,集体主义幻想即将破灭,这是“丧地者”携带无奈与悲伤的历史条件。但是,面对国企改革,即使沦落为“流氓”的父辈们也能保持理性,这里,他们将脆弱的情绪适当收敛,携着几丝颓丧的希望继续前行。
而关于“故土”的意象则更多地被统合在《海港之夜》《你在他乡还好吗》这两首歌曲的情绪“展陈”上。厂区解体/改制后,离别之夜的苦恼代置了不舍的衷肠述说。柔和、安静、忧伤的《海港之夜》作为牵留父辈的“故土”意象,放逐了父辈内心的无奈与迷茫。歌曲中“一副宁静又深情的画卷展开在人们眼前,白天战争……而在第二天清晨战士们却又要奔赴新的疆场……歌曲满载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3],同父辈们无奈从故土中抽离,即将奔赴他乡/“战场”并向可爱城市挥手告离的精神面貌相十分匹合。当小雷目送载着父亲的大巴远去,父辈们对故土的不舍与眷恋被《你在他乡还好吗》猛地抽出,并在离乡的影像中再度加重了迷茫与无奈的情绪。大巴车上,小雷父亲梦中回望故土的惊讶、诧异和不知所措,成为一种失落情绪的心理视觉透视。正是这种透视使得作为负载故土/时代情结的意象,在影片中首次以音量齐平的方式出现。当镜头被梦境(回忆)拉回到厂区员工集体聚餐的场景,歌曲的声音覆盖了嘈杂的环境音响与人物对话,一汪肆意流淌的迷茫锁在父辈的愁眉上,并被歌曲串联在不同的时空深处弥散。
(二)集体主义交响曲与正谕话语:怀旧与迷恋
在无奈与迷茫的背后,充斥于集体内心的是无限的怀旧与迷恋,而正谕话语的发声对此作了意义指涉。“正谕话语是伴随权威主义的,他要求语义单一、严密、崇高和不容置疑,它不再关注具体某个个人的感受。”[14]本文正谕话语的结构是建立在人物语言台词基础之上的话语共享与逻辑延伸,关涉有声源音乐,具有拓展性。此外,正谕话语在影片中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即“入侵—游离—解体”,而这一情感的承担主要又与大院里的歌唱者大叔对位。歌者作为一个因国企改革失去工作的时代“弃儿”,在1990 年代正谕话语的逻辑机制中,体认了对集体的话语迷恋,进而成为了“装在套子里的人”的时代缩影。当歌唱者站在阳台上赋唱集体主义交响曲《江河万古流》,歌曲作为自我附注的生命慰藉与精神依托的标签,指称了个体精神世界和集体坍塌空间的怀旧撞击与迷恋冲动。该歌曲在影片中共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小雷和玩伴蹲在门前玩耍时,导演运用有声源音乐转场,镜头衔接歌唱者阳台练声的场景。这是在改革时代背景之下正谕话语的首次入侵,其试图掌控话语权,却遭遇流氓“话语”的反击与解构——三哥团伙“打劫之声”的挑战。第二次是小雷和父亲从田野里抓蛐蛐回家的路上,同样是对音乐转场的借重,正谕话语的权利指向被潜抑/压制——代表改革势力的胖子扬言要辞掉违背他意愿的员工。在厂区大院里,从喇叭里挣脱出《花在欢笑》的曲子与歌者“磨炼的是,非凡的毅力,较量的是,充沛的体力……”的助威诗的影像序列,共同体认了“大院”作为集体空间负载时代情感的必然性、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强刺激”“强推进”改革的另一层面,正谕话语的权利空间间或被遮蔽和隐藏,使缺席的“逼退下岗”的现实与“琴棋诗酒”的理想离轨,从而痛击了在生活中沉浮的每一位“在场者”。当“歌声”与“诗话”中断,歌者所引导的“离轨语境”与时代工人的“话语权”在“争夺”中跌落。此时,“喇叭”也不再是发声机制的器物;因此,具有仪式感的比赛也便草草收场。而影片尾声,歌者与昙花合影缓慢/呆滞的举动,不仅是缅怀旧时光同找寻失落正谕话语权的等值对位,更是在孤独与落寞的图解下正谕话语走向解体的真实写照。
从感觉到知觉,听觉是被动的,而听音则是主动的,我们的双耳使我们可以感受到立体的声音,帮助我们感知距离、空间关系以及我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八月》中的声音体系向观众传达的更多是记忆的感知而非存在的实体。这种记忆感知不再局限于个体而是上升至整个时代,盘结着整个时代的命运脉搏,引领观众用“耳朵”回到过往的特殊年代,帮助观众或感受年代更迭的魅力,或追寻自身的时代印记,或回望已逝的文化记忆。不论是追寻还是回望,我们不难看到,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声音叙事系统在逐渐完善。其一方面能够为未来的中国电影的创作与实践指引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电影声音叙事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理论参照。